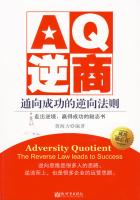为首的那人手里掣着一把宝剑,走起路来直直挺挺,大步向前,颇有一般威风。
旁边也有一个人引人注目,其人长得身材高大,壮如一只大水牛,手里拿着一把大刀,走起路来就像一座大山在你面前蹦来蹦去,陆方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他定是个性急如火,心急如牛之人。
这些人之中虽然也都带着一股腾腾的杀气,但杀气之中却又隐隐然显出一种阳刚正气。陆方看得明白,心中想:“我只不过一介小民,不管来者何人,都不可轻易招惹他们,玉佩的事,暂且不能泄露出半点。”见那伙子人上来,陆方停住脚步,正想站在一旁,让出一条路来。不料那大水牛却急冲冲地奔上前,把陆方吓了一大跳,心想:“事又来了!”大水牛跳到跟前,二话不说,就把陆方扯了过去。陆方被大水牛这么一扯,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脱着走了,陆方想挣扎,奈何力量实在是太悬殊了,又怕自己一动,藏在衣服中的锦囊香袋就被抖落下来,只能大叫:“做什么!”大水牛边拖着边说:“我不做甚么,就问你几句话。”陆方说:“问什么?”大水牛将陆方拖到带剑者的面前,才将他放开,说:“我问你,这山上可有女。。”女字刚说了一半,那带剑者的眼睛一瞪,大水牛就不敢把这个女字说下去,嚷道:“山上有什么人?”陆方说:“山上没人!”带剑者上前一步,问:“真没人乎?”陆方想了一下,在心里算计好,就说:“未曾见过,刚才也有一伙子人问我山上可有人否,我说不曾见着,他们带头的不信,就都往山上找去了。”带剑者一听,惊问:“那伙子人有几个?”陆方说:“约摸五六个,没去详数。”带剑者又问:“几时上的山?”陆方回答:“走了不多一时。”带剑者把剑柄握紧,眼神里又多了几分的杀气,对身后人喝道:“走!”身后人应声而走,急匆匆地跟随他往山上赶。大水牛把陆方一推,也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陆方被他这么一推,不住地往后退了好几步,栽了个大跟头,在地上“哎呦”了一声,心里暗暗地骂了大水牛一句:“贼他娘!”大水牛自然是不知,只顾着往前追赶那个带剑的。
陆方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将那捆摔落的柴捨起来,背好,撒腿就跑。跑在路上,不管见着人没见着人,都不停下脚步,生怕再遇出些什么事来。一直奔到村口,心里想着终于是到了,一个不经意,迎面走来了一个人,陆方也没有看到,双脚只管向前,那人也没注意要躲着陆方,结果两个人头碰着头,面碰着面撞在了一块,“嘭”的一声,两人额前一阵昏黑,双眼冒出了金星。
那人倒退了一步,捂着额头,骂道:“哪个走路不长眼的!”陆方也捂着额头,睁眼一看,那人也是细长的身材,略微发胖,肚子滚圆圆直挺出外面来,俨然一副怀孕十月的光景。脸上小眼小鼻小嘴巴,着灰色长衫,穿一双草鞋,腰间别着砍刀,头上扎着一条旧布头巾,浑浑噩噩的。此人名为刑虫,家里排行老大,本来村里皆称呼他为虫大,后来几个好玩的,干脆叫他大虫,渐渐地人人就都称他为大虫。大虫家里只有一个弟弟,人称小虫。两人虽是同胞兄弟,弟弟却生得骨瘦嶙峋,有如干柴,性格就类若他大哥。大虫小虫皆算是陆方小时候的玩伴,只不过他们和陆方的关系就不如谷三和陆方走的那样的近。这两兄弟和谷三不一样,谷三好耍诈,他们好耍滑,只要哪里有好处有小便宜,他们就往哪里钻。
陆方捂着额头,说:“哎呦,撞上了一只大虫。”大虫说:“陆瘦子,你着着急急的作甚,赶着去死呢。”陆方一听,心中有些不悦,说:“我背柴回家去,与你何关,休得来管我的闲事。”大虫哼了一声,说:“你的闲事我却不愿意管,白让你撞了我一回,我上山伐我的柴去!”说完就要离开,陆方斜了一眼,看村口并没有其他的人,就将他叫住,说:“先且不要走。”大虫立住脚步,问:“还有什么的事?”陆方说:“我来问你,近来附近可有妇女上山?”
大虫听了,扑哧一声,继而哈哈大笑,道:“陆瘦子,你打的什么歪主意,莫不是想女人想到昏了头脑么,罢了罢了,你还是叫你家老头儿尽早与你将亲事做了罢。”陆方被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更加疑惑了,问:“这话是怎么说?”大虫微微地一怔,说:“你当真是昏了头脑么,枉你在燧石村活了这么长,不知道我们这里方圆地界,村落人户,女子是从不上山的。山上又没有宝,尽是石头与大树,去它的作甚?”
陆方微微点头,说:“我知了,你去罢。”大虫就问:“你刚从山上下来,莫非见到山上有妇人?”陆方说:“不曾见到,下山时有人向我打听,我来问个明白罢了。”大虫大笑,说:“那定是个痴的,要是山上能有女子,我下世不为人。”陆方在心头暗笑:“你就真去当条虫。”嘴上也不回答,大虫转身就走。
陆方进了村口,走了没多久,来到了王谷家的门前,走到他们家门的对面就停了下来,在心里琢磨:“这谷三刚从都城回来,不定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向他打听打听,也许还能套出点什么消息来。”计划已定,就走到门前,在那里张头张脑,看谷三有没有在家。
可巧篱笆围起来的院子里就只有谷二一个人,见门外有人在探头探脑,心里奇怪:“不会是贼?白天里来踩盘子,晚上要来盗我家东西。上次就把三的当成了贼,这回可别看错,有了,我拿家伙到门那边看看去,若是不认得的,必是个贼,打他一顿,再让他走,贼人就不敢来了。”王家三兄弟中,这第二的平日里既爱睡觉,也喜欢疑神疑鬼,总怕有人来偷东西,也不知道他到底私下里藏了些什么宝贝。谷二随手拿了扁担,不想太多,就直奔门那边去了。
到了门边,一看是陆方,原来是认得的,就把扁担放下,问:“陆家小子,到我家门前何为?”陆方说:“我找你们家老三。”谷二就说:“我想着你到这里来也不能有别的事,我们三的在家呢,上次在山上淋雨,你一病不起,我寻思着你该到天上去了,未曾想你又活了过来,都说命大的福气也大,你将来这福气定是不小呀。”陆方点了一点头,说了声:“承你的好话。”谷二笑了一笑,说:“嘿,用不着客套,到时有了福气,就是别忘了村里邻人。”陆方说:“岂敢。”谷二说:“进来坐坐?”陆方说:“不多时还要往家里赶,只管叫谷三出来。”谷二就“咯吱”一声,将门合上,走了没几步就大嚷:“三的,陆家小子找你呢,快快出来。”
谷三在内屋里听见,答应了一声,以为是土地公已经托梦给了陆方,自己大财将至,急冲冲地从屋里冲出来,跑到门前。看得谷二心里犯纳闷,要不是谷三是他自家兄弟,他就要偷偷地跟过去,听一听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好事,碍于与谷三兄弟的情面,要是他当哥哥的,去偷听弟弟和别人讲话,万一要是被发现了,自己面子上可就过不去,于是谷二纳闷归纳闷,也不去管那么多,在院子晃荡了一会,径自回屋内去了。
谷三一见到陆方,就将他拉到一旁,瞅一瞅四周有没有人。一看四处没人,就问:“怎么样?”陆方说:“不怎样。”谷三就不高兴了,说:“那你来找我作甚?”陆方说:“我来向你打听打听。”王谷问:“你要打听什么?”陆方说:“最近可有见到什么青衣女子?”谷三眉头一皱,说:“你问这个作甚,我们附近地界,着青衣的女子几乎没有,都城里头倒有的是。”陆方就说:“我也是一时的好奇,有路人来问我,我就来问你了。都城里都是什么人着的青衣?”谷三回答:“都是寻常的百姓,奴仆侍婢之人。”陆方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面还是弄不清楚山上的青衣女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想那青衣女子外貌神态,绝不是寻常之人,必也是乔装打扮上的山,自己也就问不出什么来了,又想了一下说:“你到都城,可有见到什么有趣之事?”谷三又回答:“都城照旧,一切如常,并没有什么有趣之事,只是偶尔听市井之人说,西边秦国人可是厉害。”陆方马上就问:“怎么个厉害法?”谷三就说:“我上都城办事,焉能打听得这么多。”陆方就不问了,准备要走。谷三一把将他拉住,不让他走,问:”土地公何时才来托梦?”陆方说:“咱哪管得了他老人家何时来,他老人家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咱可不能着急,万一他老人家一不高兴,把宝物收回去,到时怎地?”王谷急出了一身冷汗,用手往额头上擦了一擦,连忙说:“不急,不急,你回去等,我在家里等,土地公爷爷一托梦,你就来告诉我,咱们就去挖。”陆方点头说:“焉能急得来,咱只管平心而待,定不能有半点桀错。”
谷三也点头,不敢再阻拦。陆方将柴背至家中,扔在院子里头,将刀放好,跟陆老爹敷衍了几句。回到自己屋内,将门栓栓上,把门反锁起来,在衣服袖子里将锦囊香袋拿出来,一看香袋依旧完好,玉佩也还在里面,暗暗地庆幸。偷偷拿了一个铁家伙,把床移开,在床脚处挖了一个窄窄深深的小洞,将玉佩放在一个小陶碗内,再用一个相同大小的陶碗反方向扣上,将锦囊香袋封存好,放入洞内,把土盖好,在上方放一个小石子做记号,将床移回原位,才把门栓拉开。陆方心想,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绝对不会被人偷走,觉得也没什么别的事,一个倒身,就躺在床上歇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