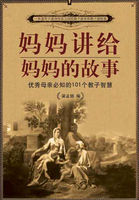朱允炆惊讶地回过头去,凝望着发声之人,只见黄子澄满头大汗,跌跌冲冲地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道:“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啊!”
朱允炆被搞糊涂了,什么人都有可能为朱棣求情,但就是眼前这个黄子澄是绝无此可能的,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他的撤藩立场最为坚决,为何今日却会出此奇怪之语。
朱允炆皱眉道:“黄卿,你在干什么!燕王朱棣意图不轨,竟然想要行刺朕,实在是罪该万死,为何朕杀他不得!”
黄子澄跑到了朱允炆的跟前,小心地低声奏道:“皇上,此处不是谈话之地,请速速回宫,从长计议。”
“什么从长计议!”朱允炆怒道:“朱棣弑君谋反,证据确凿,还要计议什么!”
“皇上!”黄子澄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哀声奏道:“微臣服侍皇上多年,对皇上忠心耿耿,绝不会做出损害皇上的事情,就请皇上相信我这一次,回宫吧!”
朱允炆默然凝视了黄子澄良久,又再度看了看昏死的朱棣,最终狠了狠心说道:“朕相信你,回宫!”说着,朱允炆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了。
黄子澄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了地,欣喜之余更加感到无比的感动,朱允炆在此时的这一句“相信你”,里面包含了多少信任和宠爱,这种无尚的荣耀险些使得这个饱经风雨的臣子当场流下眼泪来了。
不过此地绝不是他表现感动的地方,迅速收拾起了自己心情的黄子澄很快站了起来,追随着朱允炆扬长而去了。
当这两人都走了以后,王府诸将才勉强回过神来,而在他们之中,姚广孝更是第一个反应了过来,疯了似地放声狂吼道:“快!快去看看王爷怎么样啦!”
一个时辰之后,在燕王府的厢房之内,几乎已经浑无生气的朱棣瘫坐在床上,赵飞云坐在其身后,双掌紧紧地印在朱棣的背门之上,浑厚无匹的九阳真气透体而入,通经活穴,驱阻化淤,为朱棣疗伤保命。
在他们二人的面前,姚广孝和冷彪卓然而立,站在床前护法,他们神情忧虑地看着朱棣那苍白的脸色,心中真是又惊又怕。
良久,赵飞云猛地一下催劲,朱棣浑身一颤,张口吐出了一口淤血,淤血成紫黑之色,可见沉积之深,而当朱棣吐出了这口淤血之后,原本煞白的脸色也再现红晕,渐渐地转醒了过来。
姚广孝和冷彪看到朱棣转醒,都不由得欣喜万分,正待冲上来探问,但是赵飞云扬手一拦,慢慢扶着朱棣躺下,沉声问道:“王爷,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朱棣长叹了一声,缓缓地点了点头道:“多亏了贤侄的‘九阳神功’为我疗伤,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听到朱棣还感谢赵飞云,冷彪可憋不住了,悲愤地吼道:“王爷你不用谢他,要不是他出的这个鬼主意叫王爷去袭击朱允炆,王爷根本就不会受伤的!”
赵飞云根本不理激动的冷彪,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颗银丹,沉声对朱棣说道:“王爷,我已经用内力将你体内的皇极功劲稳固住了,现在你服下这颗‘玄阳银丹’,我要用金针刺穴之法为你进一步活穴化淤,你要准备好啊。”
“嗯。”朱棣张口服下银丹,笑着点头道:“有劳贤侄了。”
赵飞云解开朱棣的上衣,露出了朱棣已经被打得惨不忍睹的胸口,而众多淤痕之中,又以两个深深的拳印最为惊心动魄,赵飞云一边缓缓地拿出随身的金针插在朱棣的身上,一边叹息着笑道:“所幸王爷数十年的功力修为的确是深厚无比,朱允炆的这一拳虽然将王爷重创,却没有将心脉完全损毁,王爷性命无忧,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姚广孝看着朱棣那满身的伤痕,忧心地问道:“那王爷什么时候才能康复呢?”
“急不得!”赵飞云道:“王爷受创极重,本来一两个月也难以痊愈,此时就算有我的调理也至少要七天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若是急躁冒进,王爷很可能会留下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甚至还有废功的危险。”
冷彪再也忍不住了,破口大骂道:“姓赵的,你这个王八蛋出的什么鬼主意,竟然叫王爷去弑君,你是不是想害死王爷啊,狗娘养的!”
“啪啪”两声,冷彪的话音刚落,赵飞云便闪电般地回手扇了冷彪两个耳光,强猛的劲道扇得冷彪连退数步,一下子瘫倒在了椅子上。这两个耳光事前毫无预兆,在场诸人也不乏高手,但是竟无一人看得清楚赵飞云究竟是如何出手的。
而转头再一看,只见赵飞云依然在给朱棣施针刺穴,竟像根本没有移动过一样,两边面颊被抽得高高肿起的冷彪猛然间听见了赵飞云森然地说道:“我警告你,你的嘴臭我可以原谅,但是如果你再敢辱及我的家人,我立刻就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赵飞云看似悠闲地替朱棣扎针,但是他那言语间弥漫的杀气却让人不寒而栗,冷彪原本也是冷血凶悍的江湖大盗,但是被赵飞云这么一吓,竟真的不敢再口吐脏话了。
但是心中有不服,冷彪还是硬着脖子嚷道:“我说错了吗,难道你的主意不是想要害死王爷?”
“王爷死了吗?”赵飞云头也不回,冷冷地说道。
“那个……”冷彪刚想反驳,突然觉得这的确是非常奇怪,反问道:“哎,对呀,那个黄子澄为何要替王爷求情啊,他不是最想王爷死的吗?”
赵飞云懒得理他,根本不答话。
姚广孝知道厉害,先深深地打了一揖,恭声问道:“敢问赵兄弟,那个黄子澄为何要为王爷求情,难道赵兄弟早就知道了?”
赵飞云转头一看,只见朱棣也露出了询问的神色,唯有摇头叹道:“朱允炆之所以抓到了王爷而不杀他,就是因为刚刚登基而朝局不稳,而王爷又是德高望重,若是现在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杀了王爷,那朱允炆随时都可能得不偿失,所以黄子澄才要替王爷求情。”
“啊?”姚广孝奇怪道:“但是此时王爷已经做出了弑君谋反的举动,如何算没有真凭实据呢?”
“什么真凭实据?谁知道啊?”赵飞云没好气地反问道。
“啊?”姚广孝被赵飞云反过来这一问,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而冷彪却不解地道:“谁说没人知道,朱允炆和黄子澄不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什么叫没人知道啊?”
“哎,不是什么人说的话都可以作为证据的。”赵飞云长叹了一声道:“朱允炆虽然是皇帝,但是他的话也不过是一面之词,根本不能作为证据,而那个黄子澄和皇帝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一力主张撤藩,仇视天下藩王此事天下尽知,他的话和皇帝的话一样无法作为证据;而至于我们,难道我们还会指证王爷弑君吗?”
“对啊!我明白了!”姚广孝突然兴奋地大叫,把冷彪给吓了一跳,只见他再度深深地对着赵飞云做了一揖,恭声说道:“赵兄弟真是神机妙算,在下佩服佩服!”
冷彪莫名其妙,问道:“姚先生你佩服什么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姚广孝微微一笑道:“其实道理很简单,冷兄弟,如果有人告诉你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你信不信。”
“神经病!”冷彪道:“我见鬼了才信。”
“没错。”姚广孝兴奋地道:“那如果有人对你说他看见一只兔子追着一只老虎满山跑你又信不信。”
“姚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冷彪不耐烦地道:“这些荒谬之极的东西谁会信啊!”
“这就对了!”姚广孝笑道:“既然当事人的话都不能作为证据,那只有看谁的话更让人相信了,如果你要对人说,一向都是英明睿智的燕王会蠢的在自己的府第里做出弑君的举动,你说谁会相信!”
“对啊,根本没人信的!”冷彪恍然大悟道:“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是啊!求生才是为人的本能,求死本就是大违人性的举动,尤其是聪明人就更不会这样做。赵兄弟这一招反其道而行,攻击人性的弱点,以达到死中求活的目的,让朱允炆和黄子澄无可奈何地吃了一个闷亏。”姚广孝叹息道:“可是这种方法实在是太过危险了,若是没有超人的胆识和见识,是没有人敢用这种计策的,因为在兵法上,这种计策就叫做……”
“置之死地而后生!”平躺在床上的朱棣也微微露出了兴奋的神色,微笑着道。
“以方才的情形而论,除非是一些天下闻名的刚正人物,还必须是在立场上亲近王爷的人物亲眼目睹到刚才的场面,否则任凭朱允炆怎么说也是没人信他的,所以他就不能杀王爷。因为如果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杀掉王爷的话,他早就已经动手了,而我正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才敢兵行险招,赌上了这一把。”赵飞云连施两针,头也不回地淡淡地道。
姚广孝疑惑地道:“但是赵兄弟为何要王爷去袭击朱允炆呢?激怒他对我们可并无好处啊。万一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而不顾一切了,那王爷岂不是在自掘坟墓?”
“年轻气盛的朱允炆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而想不到,但是老奸巨滑的黄子澄应该不会想不到其中的利害。”赵飞云淡淡地道:“再说我的真实目的也不是想要激怒他,而是要误导他。
“历史上,有很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基本上他们取胜的秘诀都是——遇强则屈,骄敌之心。令敌人骄傲轻敌,在寻觅他们的破绽加以击破。
“王爷此时身在敌人的地盘里,可谓弱势之极,完全没有对抗敌人的资本,而我们的敌人也实在太过强大,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完全没有任何破绽可供我们利用,如果硬拼的话只会是死路一条,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给他制造出一个破绽来供我们利用。
“而要制造出破绽,就先必须让他轻敌才行,我要王爷去袭击朱允炆,正是要让他亲身感受一下王爷和他的巨大差距,让他看不起王爷,认为他自己什么都比王爷强,从而产生轻敌之心,这就是骄敌的第一步了。”
“难道这样朱允炆就会放了王爷?”姚广孝疑惑地道。
“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赵飞云道:“朱允炆和一班力主削藩的臣子铲除王爷的心情实在是太坚决了,光是让朱允炆认为自己更强是没有用的,除非能让他认为王爷对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威胁的时候,我们才能有一线生机。”
“彻底地失去威胁?”姚广孝摇头叹道:“除非是王爷死了。”
“不。”赵飞云同样也摇头道:“除了死,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让人完全失去戒备之心,而在古时候就有人曾经以这个方法成功逃离了险境。”
“这个古人是谁?”姚广孝和冷彪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问道。
看到连朱棣也露出了期盼之色,赵飞云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孙膑。”
“什么!”姚广孝惊道:“赵兄弟的意思是要王爷——装疯!”
“没错。”赵飞云点了点头道:“这才是我真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