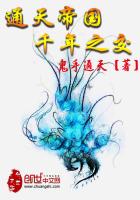1898年7月,一位法国作家被法庭以诽谤罪,判处徒刑。就在宣判的当天,他跨海逃亡,在英伦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这位作家,就是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作家被弄到对簿公堂,左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抚今追昔,不胜唏嘘。
但左拉这个名字,在今天的先锋文学圈子里,已经少有人谈起。其实他逝世,距今不足百年,读他那些曾经辉煌一时作品者,已寥若晨星。这现象给我们后人的一个启示,便是在还健在的时候,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不要动不动的就把不朽啊,传世啊,杰作啊,经典啊这一顶顶桂冠抛洒出去。因为这些褒词不是和街头卖烤白薯一样,随意就从炉子里拎出来那样简便的。想到时下文坛上一些作家,认为自己已经被下个世纪的读者认定;或一些捧家,认为某些作品已经是本世纪的经典,都是不怕大风扇了舌头的过甚之词。
文学是否为经典,是由坐在书斋里的几个人,交头接耳就能决定的吗?2097年的读者喜欢读什么文学作品,能以眼下这些明公的不太高明的脾胃为标准吗?我们到饭店请客的最起码的礼貌,总是要把菜单递给客人,请他点菜吧?如果一个主观的主人按他的好恶决定了几道菜式,也不管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诺曼地那种臭不可闻的奶酪,非强迫你吃的话,你会欣欣地坐在那里吗?
左拉一生的目标是追赶巴尔扎克,直到他最后死于煤气泄漏,由二十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他的类似《人间喜剧》式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现在,不仅左拉的这套大部头作品,还没有完全译成中文,甚至差不多出齐的巴尔扎克近三十卷的文集,又有多少读者潜心其中呢?
这位长篇小说领域中进行过写作实验的大师,时下,持现代派观点和只不过标榜新潮的作者或读者,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的文学混混之流,都不大提起。有的人甚至不知左拉为何物,即或知道他是谁,他曾写过些什么,现在忽然提到了他,和从箱子底下翻出来的四个吊兜的涤卡中山服,国防绿的洗得退色的军便服一样,至少有种老古董感觉,背时的感觉,这大概是不会说错的。
文学是个市场,和服装一样,流行什么,滞销什么,是个使神经脆弱的作家,像没头的苍蝇东碰西撞,足以忙得五内俱焚的问题。有的作家,财源滚滚,炒作成瘾;有的作家,枯守寒窑,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这种不平衡,大概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随便举个例,同是外国作家,同是在名字中间有个“拉”字的,那境遇也是黄泉碧落,上下迥异。譬如那位杜拉,譬如那位昆德拉,其吃香走红的程度,可就大大地让左拉感到惭愧。杜拉因为和张爱玲一样,由于在前不久香消玉殒的缘故,突然走俏。不但她的书好销起来,连由香港演员饰演男主角的《情人》VCD,也卖得不错。至于昆德拉,那更是一直被敬若神明,受到众人顶礼膜拜的。甚至拉美文学,只不过沾一个“拉”字的光,也在文学市场上被看好。因为流行和时尚,有一股裹胁愚盲的力量,会诱使那些轻信者、追随者,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老赶”之辈,会不由自主地趋之若鹜。其实,拉美作家中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相当“柴”的。最近召开的国际西班牙语大会,巴尔加斯·略萨不就指责一些作家在使用垃圾语言吗?语言都散播垃圾的恶臭,整个作品大概也不会香味扑鼻了。因此,杜拉也好,昆德拉也好,狂捧嗜痂者,固大有人在,持相异评价者,也大有人在的。中国人之容易被蛊惑,被煽动,和中国人之喜欢看热闹,喜欢一窝蜂,喜欢大呼隆,喜欢起哄架秧子有关。
清末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一夜之间,京城津门,神坛遍地,磕头烧香,扶清灭洋。那些信徒坚信大师兄所言,念了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哪怕后来在武清县、在垡头镇的交火中,证明了敌不过洋枪洋炮,一排一排地被洋鬼子击毙,倒地不起,还不承认符咒不灵,声言系死者不够心诚所致。所以,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则统计数字,说中国每天有六千万人在如火如荼的大练气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其实是缩小的说法,包括我认识的几位神神道道的作家,几位走火入魔的编辑,说现在神州大地上流行着当代义和团癔病综合症,不算过分。于是,我想,拉美文学,乃至死去的杜拉和活着的昆德拉的崇拜者,有的是托,有的是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只不过“矮人看戏何曾见,却是随人说短长”,众人说东,不敢说西的从众心理的惯势罢了。
所以,此“拉”敌不过彼“拉”,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并不等于其文学价值也打了折扣。再过几年,杜拉、昆德拉,和左拉一样,又被新的什么拉替代,也不是不可能。文学市场就像清代人赵翼所说:“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前些日子,有一家文学刊物,搞了一个新体验专号,为已没有什么故事的文坛,掀起几丝漪涟,增加些许热闹。有人去当小贩,有人到太平间,大家觉得很新鲜,其实并不新鲜,不过老戏新唱,旧调重弹。溯本推源,这种新体验小说的老祖宗,就是左拉。他在上世纪末的巴黎文学圈子里,就推行他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当时,赞同他这种文学实验的,还有写《羊脂球》的莫泊桑,写《最后一课》的都德,他们共同结集出版的《荷塘夜话》,便是他们最初创作实践的结果,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据说,左拉为了写他《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九部的《娜娜》,也是这部系列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曾经专门去拜访过巴黎的名交际花,到三等妓院去深入过,甚至在一个老鸨家里作客长谈,还待在后台的女演员化妆室里观察她们的生活,在那里过了好几个夜晚,尽量熟悉舞台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在当时一新耳目的写作方式,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页,然而,时过境迁,甚至不足百年,就落一个“至今已觉不新鲜”的结果了。
这家刊物标明“新体验”以区别于前人和他人,而不说天下惟一,世上无双,这就是聪明之处了。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看透,文学和历史一样,所有的花样和把戏,招数和功夫,名堂和噱头,方法和点子,几乎都被前人玩过。后来人的全部努力,包括作家在那里苦思冥索,皱断枯肠,顶多也不过是在前人玩过的基础上,稍稍加以演化,赋予自己的和那个时代的特色罢了。
文学就是一条这样不停变来变去的河,仅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