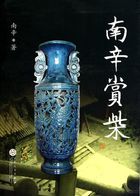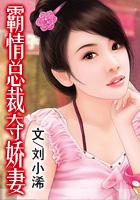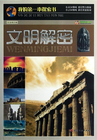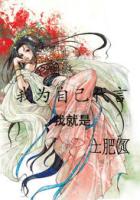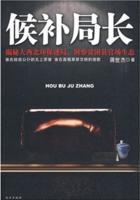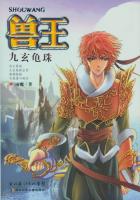“五四精神”的“引领期”,至“国防电影”后结束。经过“孤岛”时期的沉滞,到1945年后,进入它的“沉淀期”。之所以用“沉淀”一词指称这时的“五四精神”的流转,主要是因为,尽管这一时期仍存在一定的“引领”,但经过多年的战争与革命,国人对于“五四精神”的理解显然已更进一步。在脱离了直接的或较为线性的思想主题表达之后,直到1949年建国前的这一时期,“五四精神”在三个面向上得到了延伸和拓展。第一个面向是继续沿着左翼电影运动的方向继续发展,以昆仑影业公司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为代表,但不同于左翼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五四精神”不仅大大降低了“激进”的程度,还在人物的塑造、人性的开掘、群像的刻画、悲剧命运的揭示以及现实生活的深度书写诸方面,都较以往更为圆熟。第二个面向是将“五四精神”深入到市民阶层,在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中,通过对情感和伦理等外衣的剥离,深刻表达一种“五四精神”所指涉的“现代性”的理解。它以文华公司出品的《太太万岁》、《假凤虚凰》等为代表。在这些影片中,虽然“五四精神”所强调的“反帝/爱国、反封建/革命”等都已基本消失不见,但“五四精神”所昭示的对于“现代性”的呼唤与思考,却被这些影片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另一方面,反衬着“五四精神”的平民化进程。第三个面向则是将现代西方的一些人权、民主等思想直接转换为一套叙事情节,并按既定的思想发展逻辑来组织叙事进程,是一种“五四精神”的理论化呈现,它以《摩登女性》等影片为例。这类影片无意表达“爱国”、“革命”等主题,也无意详尽展示或披露市民的阶级本性,而是自我满足于一种对于现代西方思想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建构。尽管这与“引领期”的“五四精神”的体现有些距离,但对于西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又何尝不是“五四精神”的基本内容呢?
从“自发期”到“引领期”,再到“沉淀期”,“五四精神”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总体上说,虽有反复,却从未缺席,就算是在上海沦陷后的“孤岛”时期,再次出现的“古装片”等风潮,从某种意义上似乎与我们所理解的“五四精神”无关,但戴锦华教授却认为,如果说,古装稗史、神怪武侠片原本是对前现代民间故事的重述,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拍,便事实上成为重述的重述。这一独特的电影文化现象,间或作为平滑、同一的历史叙述的一处裂隙,为一个迄今已愈百岁的幽灵赋形。这幽灵正诞生于老中华帝国颓然崩裂,少年中国艰难莅临的当口,为通常被简单地命名为反帝/反封建、救亡/启蒙、现代/传统的逻辑悖反命题所建构并召唤。戴锦华:《“五四”洪流中的一泾:中国电影的初创》,选自《“五四”记忆中的精神与电影》,《电影艺术》2009年第3期。如此说法,并非表明这一时期的所有中国电影都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普照,而是旨在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从“五四精神”诞生的那一刻起,都以此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参照,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叙事体系。不过,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一精神便被另外一个系统取代了,这便是“延安传统”。
二“延安传统”及其影响探析
“延安传统”显然来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么,何谓“延安传统”呢?周星教授认为,《讲话》精神包含五个方面的要素:即强化注重现实精神的要求;对艺术文化借鉴创新的强调;对注重鲜活的生活气息的强调;关于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的辩证认识;对艺术文化工作者必须有高尚的人格和贴近大众的心理亲近的提示。周星:《新时代电影文化精神认知的借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启示》,《2012电影创意研究》,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页25—30。陈旭光教授则认为,《讲话》精神在中国电影中的呈现,实际上是一个“主流化”或“大众文化化”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大众化”及“化大众”的革命文化理论与实践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陈旭光:《大众、大众文化与电影的“大众文化化”——试论〈讲话〉精神的当下性与电影生态的大众文化视角审视》,《2012电影创意研究》,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页34。陆绍阳教授则指出,“延安传统”的精神内核有两点:第一,“延安传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精神指引的,《讲话》中“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不但是作为文艺政策写入文件,而且深入人心,成为所有文艺工作者的行动纲领;第二,“延安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品格成为新中国电影的首要创作方法。尽管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也受到了其他文艺思潮、流派的影响,但那些思潮、流派并不是主流,影响时间也比较短,而真正成为中国电影精神内核的是现实主义精神。陆绍阳:《〈讲话〉的当代价值与中国电影的精神内核》,《2012电影创意研究》,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页57、59。
然而,本文却认为,“延安传统”是完全逆“五四精神”方向的另一种文化运动。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延安传统”与“五四精神”本身并无高低之分,只是代表两种不同的文艺方向而已。本文也无意于对任何一方做出倾向性批判,而是就本人的理解,对此进行一番较为客观的评述罢了。因此,当我们回到原点,我们就会发现,《讲话》所确立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实际上是将“五四”以来的文化美学整个掉了个头,从总体上来说,是将“自上而下的重塑重造”改为了“由下而上的仰视景仰”;从美学上来说,则是将“以批判揭露为主的雷电文艺”变为了“以歌颂赞美为主的阳春文艺”。而综观建国后至新时期这段时间的电影创作,可以看到,“延安传统”在电影创作上的基本规律。1.由于视角的变化,叙事人称开始渐渐由全知型或第三人称叙事向第一人称叙事转变,有时采取杂糅的方式,布道者的角色仍然存在,但已被具体化为“党”。2.对现实采取二分法,一种是美好的歌颂,一种是苦难的展示,但展示苦难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是意在一种新旧对比;虽然革命现实主义是创作的基础,但因为视角的变化,革命浪漫主义反具有更直接的亲缘性。3.为了达到歌颂的目的,与“五四精神”的传播一样,也会选择一些传统的故事题材,但好人好事、悲情加励志是此种的首选。此外,思想加图解大于叙事的现象也仍有存在。4.人物的类型化与固定化开始愈来愈明显,坚定的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人、有缺点的好人、成长的人成为基本的人物谱系。5.人物的生死转变以及新人物、新典型的树立,多是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是“流沙型”人物。6.由于意识形态已同化为故事,所以反复讲述已成为一种策略或习惯。
根据这些规律,我们发现,在新时期之前,“延安传统”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大致经历了“确立期”、“震荡期”和“畸变期”三个时期。“确立期”是指建国后至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开始进行批判直到结束的这段时间。之所以称这段时间为“确立期”,原因有二:一是这一时期全国电影工业已基本完成公私合营,电影制片厂国有化的道路已基本确定;二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批判。通过这次批判,它起码完成了如下任务:(1)在思想认识上,统一了全国所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是《讲话》的一次现实演示。归结到电影方面,它最突出的地方是完成了对上海电影创作队伍的改造和重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上海传统”的颠覆性再造。(2)通过这次批判,在文艺美学和创作方法上,真正确立了《讲话》精神中所昭示的基本创作方向。本文认为,毛泽东对《武训传》展开批判的主要原因为:1)主人公的选择存在严重问题,因为乞丐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属于真正的农民,这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有所偏差;2)所采用的视角“明仰实俯”,也就是说,对于行乞办学的武训,创作者表面上是歌颂与赞扬,但实则却是批判的,因为武训办学的目的是好的,方式却存有很大问题;3)本片所宣扬的“阶级调和”和“改良思想”,实属“五四精神”多侧面中的一个,但这却与毛泽东所强调的“阶级对立”以及“农民革命是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严重抵牾;4)缺少“党”这一布道者角色,主人公武训也并非是一个“接受党的领导和召唤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人”。这些批判,实际上正暗合了本文在前面所归纳的“延安传统”在电影创作中的基本规律,是一次全方位的“大纠偏”。
当然,在实践方面,这一时期来自解放区的创作队伍其实在长期的领会中早已身践力行。《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女司机》、《民主青年进行曲》等故事片,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以影片《白毛女》为例,这个故事经一系列改造之后,已由一个普通的藏于深山中的白毛女的旧故事,上升到了在党的感召下,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新故事,由于视角的变化,对于白毛女的勇气和敢于反抗的精神,影片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而这个悲情的故事,也没有停留在“阶级调和”上,而是在势不两立的“阶级对立”中,表达了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美好愿望,白毛女直接成为意识形态机器中“被重塑的人”,成为意识形态反复讲述的一种策略和一个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