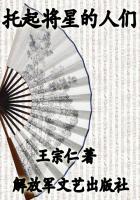我曾经计划去青海、甘肃、西安、黄土高原、秦岭,黄河,这是我旅行的终点。那滔滔河水从巴彦克拉山麓奔流到人类的脚下,黄河谷地风景壮阔,直到关中渭水流域,八百里秦川。我像一个过客,曾经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只身亲临北方的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的边缘,希望能从日落的水面看到尘世的影子。也许河流本身就是我们这样渺小生命的一个永不停息的永无尽头的仪式,弯曲的流向,像欲望一样蔓延在野草的世界,寻求一种火来作为它的终结。火光中,你能在时光的废墟里找到那河流的眼泪,那是对人类的爱,那是负重的几近干涸的情感,那层叠淤积的泥沙,而我们不过是过客。河流映照着剑胆琴心,那是知音的歌谣,是放浪在苦水河畔天然的乐律与生存的法则。生存,艰难地生存下来,寻找机会。在戒律中寻求生存的希望,这就是高中书本上的历史。当木柴、盐巴、木屋、火镰、陶罐、人力耕作成为历史,我会摊开地图,顺着自己的感觉寻找那西北繁华的王朝。那是荷尔德林所说的故乡吗?大地上的群雕、宫殿楼台、池阁亭轩,生寄死归,家乡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只能在对这古城和陶俑、古迹的猜测中借以安慰自己。看吧,这是与大地紧密联系着的另一个谱系,河流的谱系,泥沙掩盖着这个世界,我只能看到滔滔的时间与河水,看到浊黄的颜色握着一把鲜艳的颜色润饰这憔悴的土地。我需要在这片土地上发觉事物的真相,需要将我的抒情文字中那些缥缈的宏大的叙事清除,回到平静的气氛中去。
西安是我最熟悉的一个西北城市,骊山北麓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的陕西临潼县,在秦始皇兵马俑,我看到了那半截身体还埋在黄土里的秦俑,那一瞬间的感觉是不可磨灭的。那些用泥土、木、铜制作的俑身上显现着泥土质的光泽,阔大的黄土坑里排列得整整齐齐,保留着庄严的阵势和仪态。有奴仆、舞乐、士兵、仪仗,有的附有鞍马、牛车、庖厨用具和家畜等模型,还有镇墓的神物。我站在巨大寝陵内部的黄土坑旁,换了无数个角度,甚至我双手粘满了尘埃,浓郁的气息,厚重的土层,庄严的表情集中起来,我目视那些青灰,枯黄色的陶俑,荣与耻的感觉就像那随时可能涌上来的黄土一样,淹没我的手、脚、耳目、头颅。我欲凭借残断的瓷片来窥测秦俑孤独的方阵其中的构造奥妙。那是几欲燃烧起来的黄土坑,但是我感到地气湿寒,空气凝重,骨节甚至有点酸痛,感到体乏,脾胃里开始生虚火,僵直了脖子探到土坑里去看。击瓮扣缶,弹筝搏髀,这是秦地音乐的诱惑,我看着那些浸了黄河水的瓦当、砖石、土方、梁木这些沾染了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的器物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心力。我见过皇陵展出的那些瓦当,细心地看过几册隶书碑帖,还有那些玻璃罩内标明度量衡的物什。坐在车上,在窗外的树林边也可以看到那些仿制的陶俑,我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时间观,在那些青色墨灰一样空气流动的昏暗墓室、碑林和塔寺里像失去魂魄的人一样游荡。阳光照在那些兵马俑的脸上,它生黑锈的兵器上,衣服的褶皱上,我已经迷失在这个阵势里,我汗津津地握紧了弓箭,读着陌生的符号,辨识他们的微笑和被宰割的痛苦。那褐色的方砖组合在一起,铁架建筑的顶棚空隙里光线散开,土墙晃荡浮动的样子。我的血液在巨大的火坑里异常的冰冷,陶陶罐罐,叮咚的声响如水滴顺着我的感觉神经下滑。打击乐从旱野的黄土层涌出水面,马结实的肌体,陶塑在我的相机镜头里飘移,我的感觉已经迫近了极限。耳目失聪,那些兵马俑已经在黄土中苏醒,战袍外罩着黑色铠甲,遗风尤在。渭水秦川,黄土高原的世界就是这样的。骊山陵墓庄重地矗立在黄土之上,茂密的树木掩映着山体,建立在奴役基础上的辉煌消散了。不见遗骨,只有浑浊的水花。我把破旧的相机丢进旅行包里,我觉得我此时和那些辉煌的景象仅仅隔着空气、一层泥土而已。我看到了众多的假象,不可穷尽,随心而生,缈无涯际,心与物的界限被弃置。我已经没有正视美的能力,依赖隐语和微笑掩饰我的不安。但是我的心已经空虚。
那流水带来的泥沙就是万物的本源,大地本质是赤贫的。我们追求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我在这些兵马俑的陶塑中拍摄我内心的影像,我甚至拿起铅笔耐心而惊慌地临摹造物主的设计品,扭捏的线条更像是一种伪装。
你知道土地的终极意义吗?那黄土、风沙,还有无边的风雨。当你的视线被遮盖,你知道心痛吗?
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西起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南靠秦岭,北抵阴山,从地理上讲它甚至是辽阔的。也许用辽阔来形容高原地域并不恰当,但是当我望见这地形破碎、坡陡沟深、土质疏松、植被稀少的陕北高原漠漠的黄土,我宁愿相信这个无比沉重的形容词。霍去病墓、法门寺和周原遗址我已经缺乏兴趣,缺乏对抽象的寄托,对银器、琉璃器、石雕、珐琅器、石刻丝织品的辨伪能力。我根本不相信这是家的概念的全部意义。它是那么的冷漠、浮华、不近人情。在这些琉璃器中,传说一件盘口细颈淡黄色琉璃是从东罗马帝国传入中国来的。另几件花纹琉璃盘也是来自拜占庭帝国。这些是资料,但我仍认为它缺乏根据,根据或许根本就没有。它们不属于当下的黄土高原了,离开土地它们就丧失了神秘的美,而我越发没有虔诚的必要。就那一点稀释的审美知识,那一点寒碜的词语妄图来发现或引导别人,简直是痴心妄想。我断然认定人在历史和美的面前是虚假的存在,是幻象,人的能力十分有限。
黄河,我还是那样不嫌土气地称呼为母亲河,我觉得这样很亲切。在我奔赴西安所遇见的黄土高原,流水侵蚀分溅蚀、面蚀、细沟侵蚀、切沟侵蚀、冲沟侵蚀。这是具有科学定义和指称的精确的单位名词,每一个名词都证明了一个严峻的与抒情无关的事实。至少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带着家园的那种亲切感来寻找、查证、呼喊。知识、理性、情感都破碎了,只有不死的尘灰在散播时间和另一个世界的拯救的福音。
苍莽大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古歌四起,衣襟飘飘,马不并辔、车不方轨。有它的理想也有它的艰险,虚幻,是梦,是废墟,是古人的形而上的童话,是我们的家园。你应该了解它的内心的痛楚,不是凭空的誓言,而是日渐衰老的骨骼,毁弃腐朽的栅栏。荒山秃岭,函谷关关楼已经很脆弱,它地处长安古道,因在峡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它也见证了闹剧一样的黄河漂流的传媒神话。关于函谷关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从各个角度去描写它,只要你有心,并且愿意去写。你也可以去阅读老子几千年前写下的那部《道德经》,去翻看历史看看日本人当年怎样轰炸黄河渡口、堤岸。那没有湖光山色、翠峰潭影,只有生存者的挣扎与呼号。
我信任理性,但是我同样对启蒙和我们的语言抱有怀疑。父亲的劳动经验和人生经验让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这个新的视角。如果你站在高处遥望黄河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炊烟从洪荒的谷地飘升,它沟通了人与这块土地的情感,通晓人的疾苦历史。你尽可以高歌,可以在这黄河边看着潮水怎样生成,沙砾怎样着魔似地裹住了人。浩大的水声水势把人卷入苍凉的大地的裂缝里一样,我处在失神状态,泥浆咆哮着愤怒地击起滔天的水花。那一刻,人真的蓦然就衰老了。那浑浊的水花像火苗一样烧荒了土地,吐着火舌,在你的心里跳跃。你的歌声已经战栗了,顺着火势在漫野的树木与水声中灼痛难忍。那些青铜色的夔凤纹、流云花纹已经被这浊浪淘尽,你在下沉,并且不能重现浮生。唯有你的歌声留在这焦土废墟之上,点破残忍的谜底。这针对人的刑罚,无须文墨刀笔,就能置人于死地。
矫饰的美竟然是如此严厉的惩罚,这是我断难察觉到的。
站在咆哮的黄河边,风沙吹来,我百般寂寞,仰望浮云。这可能是一个极端想象化的图景,然而我还是进入了抒情状态。我不肯悔改,不肯回头。我被这河水和声响所禁锢,从身体到思考。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古歌飘摇在我的世界,汹涌的水花卷着黄土一起流向远方,韶华易逝,浮生文字,我写得无怨无悔。我在这歌声中看到了那苦难的家园,被虚拟化的家园,她贫瘠、疮痍,在水花中苦苦浸熬失色的容颜。那是已经惨遭虫蠹的甲骨文的原始,石斧猛烈地劈开麻木的河道,我恣意地享受一种痛苦带来的战栗。我的知识和思考都在这战栗中暴露了我对自然的恐惧。
哦,黄河!她开始在大地上沉沦,中心摇摇,岌岌可危。黄河水一泻千里,倔强地将最后的力量用尽,嘶喊着奔腾不息,但是已经十分沉重。
我的表达开始变得艰难,往往词不达意。我一言不发。在健康的自然面前,我是弱者、病人、语言的奴隶。我了解自然的力量,我的语言骨子里是虚软的。它的缺陷是致命的,但我没有回避。明哲保身,这是粗人士人的哲学。
黄河!
黄河在我的信仰中是这个世界的开始,她是善与美的观念的起始。她有正义的性格,但同时这也是一次惨痛的轮回。她是超脱人身滞重的尘土、启蒙、血缘关系和感情的。你见过黄河流域的文明遗迹吗?是黄河揭示了人的愚妄和浅薄,傲慢,暴露了历史的秘密和底色。她有一种非常诱人的节律和异端纯美的音色,有着黄铜一样光泽的水面,有着剑一样的闪光,明媚和晦涩,有着形式的旋涡和虚妄的深渊。皈依一条河流,就等于膜拜了哺育生灵的大地,参悟了诡谲的典籍。那些素面朝天的秦俑,那铿锵的号子,牢牢地扎下了根。
是的,与在大地上劳作一样,人要面对虚无的袭击,面对劳役和疾病,面对这怒吼的水声。
黄河火燎一样的河道,给人的感觉是焦躁。
人在事实面前疲于奔命。
父亲说歌谣和流水在我们的匆忙的劳动、远行、哭泣里有着永恒的相同的本意。这不仅仅是父亲的经验之谈。我未必能了解劳动、远行的本质意义,我只是看到了表象。来自远古和痴情的流浪人内心悲天悯人的曲子,长时间蜿蜒驻留在与我们生命有关的虚无升腾的村落和河流平静幽蓝的水面上。一条河流就与我们的生活结成朴素的联盟,幽雅的古意飘悠的水面上,曾经留下多少阳光的残照和冰雪的灵魂。建立这样天然般的感情,需要共同的理解,需要首先奠基一种相同的生死观念和不屈的积极态度,和面临毁灭的果断。像这样的河水,这样的曲子来自渡口肌肤黝黑的船工和面庞憨厚的水车,以及脆弱而迷人的芦苇和黑色冷酷的斧凿,简单的协作关系。尘土覆盖的村庄,昭示着河流与人。那些悠然的曲风和感性的词,就是水面上往来人间和俗世的悲伤的过客。多么美的歌谣,可是人是在认真地聆听吗?宫、商、角、徵、羽,这是心灵之器所奏的歌谣,劳动的节奏。水边诞生了群落,群落是我们这些愚昧的身心的人祖先的诞生地,我们聆听这些上善若水的音乐,物质与精神交融,四野玄黄,黯然神伤。
这是在干旱的大陆,农具、罂粟花、导航图、罗盘针只是人手中的万物,人们可以随意改造它。罗盘针本身不能确定时光的走向,不能确定流浪者的目的地。只有神圣的河流,你可以看到它的容颜,它的倒影,它的血液,它的骨骼和精神,它的愤怒与情感,它的褶皱与皱纹,它的衰老与渊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你们的语言是传习了古人对大地、劳动、劳动号子的崇拜,你们通过经验,通过不朽的经验获得缘分。金石、朽木、水井、火塘、土地,这是与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联系密切的器物、工具、材料。酸、甜、苦、辣、咸都在其中,这是五味,人间烟火。我们的耳、鼻、舌在这样的浸泡和濡染中变得麻木不仁。我们跌入迷宫,凭嗅觉寻找光亮。四面都是森林,磷火在空气中燃烧,那些瘪瘦的字词已经丢掉了神气的色彩。
然而真正的旅行无须任何地图,指南针。那些数字符号不能指导人前进的路线,不能作为参考的依据。大地本来无所谓方向,只有一个永恒的中心,人类根据需要依靠风水地理知识相对划出方位,确立了最早的行程。历史正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心,被迫与大地割裂。那是一个秘密的方向,那是河流的源头。我们祖先的歌谣预言了我们的路线与方向,他们说无始无终,这是旅行的心要。人不能掌握自己的方向,人只能顺着自然的事物的轨迹前进,逢山就征服山,遇水就征服水,顺其自然地继续自己在大地上的流浪,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最终都必归于大地归于尘土和故乡。古老的司南也好,故乡的风车也好,黄土高原千沟万壑,不允许轻浮的经验论断。钟鼓馔玉,玉壶美酒过眼烟云。苍茫云海,水花化作浪漫主义的语词,黄土高原,这是我膜拜的世界,我膜拜的青春!在这样的春天,走向荒芜的村落的过程中,我熟悉的悠然清亮的调子,烂漫的文字,还有烧伤的身体,发出尖锐喊声的野草,还有身后的陈年旧事都成为一种剥离了青春那种天真的伤感。失去了语言和判断的经验,所有的神话、传说、语言的古谶瞬间解体。干瘪的谜底,泛滥的私语将人的思考逼入绝地。陶俑和铜车马嘶啸的声响混荡在污浊的空气里。那河水浑浊不能照见人的容颜。
远望北方草原,我想起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只担心我配不上我经受的苦难。在北方,早些时候听一个蒙古族歌手蒙语版的《蒙古人》,他就是腾格尔,我觉得从他的歌声中我对北方的感觉逐渐突显了出来。我收藏了他的很多歌词。和西北民谣在我心中的地位一样,苍凉独特忧郁的嗓音曾经留给我许多无穷无尽的浪漫遐想。我记得腾格尔还有一首歌是《父亲和我》,随着年龄的陡增,那种感动有幸早已沉积成了人生经验的一部分。草原,那是音乐的天然摇篮;高原,那是涵养浩然气度的地域。草原歌曲的辽远、浑厚、沉郁开始影响并慢慢渗透到我的文字里去。似乎就是一种血液,一种心气的荡漾。难以诉说其中的快乐、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