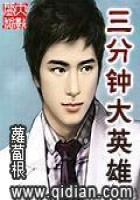“嗯……”女孩很认真地点点头。
温度越来越低,我将一个抱枕抱在怀里,女孩两手抱膝,好像并没有怕冷的意思,她望着我,反倒使我有些局促,稍稍别了一下头,女孩觉察到了。
“对不起,失礼了。”
“没什么,你在想什么?”我问。
“我在想……可不可以做一回我的模特,明天,找个地方坐下来,想着你的心思,大概用上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没问题,只要你愿意。”
“谢谢你。”她向我伸出手。
我握住她的手,感觉那手温暖得很。
女孩回去后,我继续坐在炕席上,直到冷得实在呆不下去的时候便回到房间里,外面很多游客仍在开怀畅饮,一个孕妇正忙忙乱乱地给客人倒茶,间或不忘用手摸摸自己的肚子。
次日一早,我仍在睡梦中,身体如同散了架,两只胳膊像要掉下来似的,刚刚翻身准备再睡,就听见“咚咚”的敲门声,我以为是母亲,便披上被子打开门,原来是昨天和我说话的那个女孩子。
“这么早就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我已经吃过早饭了,莫老师说你可能要多睡一会儿,没有叫醒你。”
“这就起床,对了,是昨晚说的那个事情吧?”
“嗯,还记得?”
“好像没忘,稍等,马上就来。”
女孩下去后,我连忙起床洗漱,在食堂随意吃了一点东西,很快便来到他们工作的地方。
“这地方离旅馆不上一千米,可以看见栅栏里饲养的奶牛,几个农牧民正蹲在地上往瓶里挤奶,不远处是个小学校,虽然是假期,但国旗仍然飘在夏日的天空中。
“在这边……”女孩子老远就招呼道。
经过母亲身边的时候,她正埋头做画,阳光下的母亲显得沉静而秀气,俨然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
“吃过早饭了吗?妈妈来不及照顾你,自己用点心吧,我儿子也不是小孩子了。”母亲停下手中的工作,一只眼睛眨了一下说道。
我向母亲点点头,凑近看了一眼她的作品,然后小跑着到了那个女孩子的面前,她支起画板,调配好颜料,四顾一眼茫茫草地,指着正北方让我坐下来。
“北面只是草地,背景最好,寂寥而有生命的气息,你随意坐着就好,但有一点,要想着你的心思,这样不算是窥视你的隐私吧?”她笑着问道。
“就算是吧。”
坐下后,我无论如何也摆不好姿势,虽然她一直嘱咐我随意就好,可越是这样,越不能找到感觉。
“和照相的时候一样?”我问。
“差不多,就是那么个意思,不过照相只捕捉一个瞬间的镜头,‘咔嚓’一下就OK了,绘画是一个过程,相互必须默契配合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行,明白了,那就开始吧。”
“也可以随意地和我聊天,总之放松就行。”
我点点头,从我自身的角度看着画板,女孩盘腿席地而坐,半张脸时而会移到画板一边看着我,可以说从始至终我都没有看见她的整个面部,就是这半张脸,使我蓦地以为这就是封面上牡蛎将侧脸转给我的那楚楚动人的脸,只是这个想法一瞬间就消失无存。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女孩从地上站起身,向我伸出两个手指,我明白是画完了,便也站起身,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似乎刚从梦中醒来一般。
“我入小学就开始学画画,已经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感觉,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创作,可别不信我的话。”
“没有不信的理由。”我在原地活动一下身体,浑身酸痛,肝区也有明显的刺痛感。
“过来看看,画得不好,别笑话我呀!”
“哪儿敢。”我说着便站起来走到画板前,画面上的人与我本人并不相似,但感觉是没有差别的,这或许就是她说的创作吧,只是眼睛忧郁过度,这忧郁也在感染着我本身。
“能帮忙签上你的大名吗?”她说着便将一支细细的毛笔递给我。
“只签我的名字是吧?”我问。
“先写上‘心思’两个字,然后再写上你的名字,时间就写在今天。”
“没问题,只是我的字拿不出手。”
“只要是你写的就行,想来一个作家的字是不会差到哪儿的吧。”她说着便咯咯笑了。
“要不要再按上手印?”按照她的要求写完后我又问道。
“倒提醒了我。”她说着,将印泥盒揭开来递到我面前,我伸出食指按了一下,然后选准自己的名字按下去。
“真是太感谢了,回去后有个画展,这副作品可以展出吗?”
“只要你乐意,怎么都行,我个人是没意见的,如果展出成功,说不定还能沾你的光呢。”
“只要作品能被人理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也算没有白让你辛苦一回。”她说着,对我嫣然一笑。
“祝你成功。”
“谢谢,可以把你的小说送我一本吗?”
“可以,那得等回去以后。”
“一定?”
“一定。”我说。
一星期以后。我们坐上火车往回赶,火车经过高原隧道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女孩从车厢里的餐厅给我买来盒饭,还买了两瓶啤酒,说是算感谢我,我客气地接受了。
母亲困倦地躺在自己的座位上,与我们对面的那个男学生从兜里掏出香烟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
“我不吸烟的,谢谢。”我向他摆摆手。
“那我吸一支可以吗?解解乏,把玻璃窗拉起来,吸完后就关上。”他有点抱歉地说道。
“没什么,请便。”
男孩子吸着烟,一副老练的样子,他是江南人,老家是中国针黹业的发源地。
夜里,身旁的女孩子将头枕在我的肩膀上酣然入梦,临明的时候,女孩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向我点点头,好像在说有扰了。
“做梦了?”我问。
“嗯……梦见草原上突然有一片森林,我一个人在里面走来走去,找不到方向,突然看见一条小径,前面一只小狗紧张地望着我,我还没有踏上那可以走出来的小径就醒了。”
“哦,是不是感到很害怕啊?”
“是啊,偌大的森林就我一个人,好孤单的,又感到很安适,或许是枕着你的肩膀的缘故。”
“你先是枕在我的肩膀上,后来就躺在我怀里了。”我笑着对她说。
“啊,那真是让你受累了,为什么不叫醒我啊?”
“看你睡得那么香,就没忍心叫醒你。”
“真是不好意思。”女孩说着,脸微微一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森林,有的人走出来,有的人迷失在里面。
我心里想着一个日本作家的话。
火车钻出隧道,地域下倾,我知道已经到了平原地带,古城在望。
我感到从一个长长的睡梦中醒来一般,平原十几天我几乎没有做梦,就在女孩以我为模特的时候,我坐在那片草地上,心里想着的多是甜蜜蜜,可是她已不在人间,她的死我的确应该承担责任,但法律没有没有理由让我身陷囹圄。
火车行进在熟悉的平原上,宛如游在湖面上的蛇一样,女孩去了躺卫生间,发梢湿湿的,像是刚刚理过妆。
“回家了。”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嗯,感觉还好。”
“第一次和莫老师出外写生,下学期去北极村,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女孩对此充满憧憬。
“将雪涂在画板上。”
“就是那样,只有身临其境才有收获,比如,将面粉撒在地上,想象着那就是雪,可能一整天都下不了笔。”
“搞艺术或许就是在苦恼中获得快乐。”许久以后,我这样说道。
“苦中作乐。”女孩笑道。
“一次愉快的草原之旅,谢谢你。”她又说道。
“我也一样。”
“记得送书给我啊。”
“一定。”我说。
肝区开始作痛的时候,火车已经进了站,由于他们行李多,加上画板本身的不方便,用了很长时间才下了车,母亲依旧一副困倦的样子将一条胳膊搭在我的肩上,告别的时候,他们回学校,我拦住一辆出租车,那女孩又走到窗前,向我挥挥手。
“再见。”我说。
“早点回去,别在外面贪玩。”母亲叮嘱道。
一觉睡到下午,母亲起来后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吃完饭后,电话铃响了。
“你好,是莫老师家吗?”
“是的。”我说。
“是我啊,还记得吗?休息好了没有?”
“哦,知道了,已经吃过饭了,你呢?”
“和你一样,晚上方便吗?带上你的书。”
“好,在哪儿见面?”
“学校附近有家咖啡屋,一起坐坐好吗?”
“可以,我现在就出来?”
“要是方便的话。”
挂断电话,母亲问是谁打来的。
“你的一个学生。”
“是苏宛如那丫头吧?”
“嗯,大概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说。
“都一块相处快十天了,连名字都不知道就和人家约会?”母亲笑道。
“她要我送她一本书,谈不上什么约会,我可没什么想法。”
“可千万不能心猿意马,你个人的事情我没法多过问,问多了你嫌烦,人家杨五一的父母可是和我谈过话的。”
“知道了。”我不耐烦地点点头。
师大附近的这家咖啡屋外观古旧,但里面还是相当时尚的,我以前没来过,四年里只有最后一年多才和杨五一交往,况且这是低年级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
苏宛如坐在窗户一角,不停地摆弄着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在她对面坐下后,她似乎很吃了一惊。
“这么快啊,我还以为你还得十分钟呢。”
“你离得近,怕你等不及,就打车过来。”
“很是感谢。”她接过书,翻到扉页上看了一下签名对我说。
“签名很重要是吗?”我问。
“当然,至少证明见过作者本人嘛。”她又随意翻了几页,放进自己的挎包里。
“其它的都废了,只保留了那一张。”她说。
“你是指在草原上的作品吗?”我问。
“对,我要最好的,所以……”
“唯美主义?”
“艺术总是追求最高境界,就像佛教里那些僧侣一样,有自己的目标。”
“真看不出,你小小年纪,就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都是从莫老师那儿学来的,在你眼里她只是母亲的身份,可在我眼里,无论作品还是自身,都很有魅力。”
“或许是吧,在我眼里她的确只是母亲的角色,其它的被我忽略了。”
“过几天就办画展,我拿这副作品参展,相信莫老师也会同意的,古城很重要的一次画展,有很多商家积极赞助,入围作品还将被推荐参加全国性的大展,但有一点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带有一点点功利目的。”她说到这里,突然变得认真起来。
“我不会有任何介意,这已经对你讲过,只要你乐意。”
侍应端上咖啡,她问我要不要加点糖。
“还是加一点吧,我不太喜欢那苦味道。”
她将一块冰糖放进我的杯子,也给自己加上一块。
“这里的咖啡很廉价的,不过环境还好,离学校又近。”
“让你破费了。”呷了一口之后我对她说。
“哪儿能谈得上破费,能和作家在一起喝咖啡我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客气了,再这么说我可坐不住了。”
“展出过几天举行,莫老师会去的,到时候我通知你。”
“可以。”我说。
晚上九点,苏宛如回去后,我在附近给牡蛎宿舍挂电话,她说自己刚回来。
“去了趟草原,刚回来。”
“是吗?玩得可好?”
“还好,就是有些疲倦,有时间一块出去玩吧。”我说。
“五一姐姐快回来了吧?”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有意转换话题。
“大概快了,再几天。”
“走时想带我一块去,可是不方便,其实她对我够关照的了,我又何苦白花她那些钱。”
“出去走走也好,或许对你的病情有帮助。”
“以后方便一定会出去的,但现在不行,现在只有尽量把书念好,保持视力的稳定状态。”
“总之要有信心,平时不要考虑太多的烦恼事,这样对你可能会好些。”
“哦,谢谢。”她说。
“早点休息吧。”我说。
“好,再见。”
“再见。”
挂断电话,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辆自行车,一口气骑到那片草地上,将车子扔到一旁,几乎带着哭腔跑到草地上,草地上什么都没有,连我自己都成了不速之客,我为自己唐突来到这里感到不安和内疚,由于体力透支,蹲下来吐了一回,什么都没有吐出来。
我久久地躺在草地上,全然不知道远处公路上呼啸而过的车辆,身边没有了甜蜜蜜,没有甜蜜蜜在身边的这个时候,我像在梦境中游走一般,伸出双手,这双手白净而富有男人气息,但已是血迹斑斑,那个细高个男人将手伸向甜蜜蜜的脖劲,目的是要与她同归于尽,而我的双手伸出去要做什么呢?我不不知道,不知道,我扯着嗓子用力喊着这句话。
人生若有一次告别,那意味着死,若没有告别,那意味着生。我想着甜蜜蜜六月二十号晚上在这里对我说的这句话,她的话竟然如此具有现实意义,那晚她也说过和我告别的话,谁知竟然遭遇到突如其来的死亡,她被那个细高个男人掐住脖劲的时候,是否想到自己真的会死呢?
甜蜜蜜终究已不在人世,但我一直感到她并没有死,终究有一天还会与她不期而遇,就像我们认识的时候,还有她腹中的小生命,甜蜜蜜成就了一切,惟独没有想到那个要她回答是或者否的男人会将双手伸向她的脖劲。
甜蜜蜜的回答是否定的,否则那个男人不会与她同归于尽,又或许是肯定的,但那个男人容不得她与我交往而断然将手伸向她的脖劲,并且还要将它当成一桩悬疑案欣赏一番之后又挺身而出,让我还没回过神的时候已经将我淘汰出局。
逝者已去,这草地上的草仍在茁壮地生长,它们枯萎以后回归泥土,甜蜜蜜会是这样的吗?
自然的周而复始总让人视而不见又充满好奇,肝区开始作痛的时候,我便骑上自行车,很买力地回到学校。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去一家小门诊请教大夫,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男大夫扶扶鼻梁上的眼镜,用听诊器在我的上身扫除一番。
“有喝酒的历史吗?”他问。
“五六年了吧,但也不多喝,几乎没醉过。”
“没醉过只能说明你的酒量好,以前有过疼的感觉吗?”
“就是最近,时断时续,有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
“这多半是喝酒过度、频繁所致,看你的气色不像经常喝酒的人,先吃几天护肝药,不行的话就去医院检查一下。”
他说着,为我拿出一瓶护肝药。
“真的没什么?”我问。
“少喝酒,最好不喝酒。”
“全是酒的原因?”
“也不全是,但不沾酒对你有好处,加上你受了些刺激,病由心生的道理你懂吧?”
“嗯,知道了,谢谢!”说着我便走出门诊部。
晚上回到家,按说明吃了几片,可能是心理的原因,感觉疼痛多少缓解了一些。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接起电话,是杨五一打来的。
“还好,前些天去草原了,刚回来。”我说。
“怪不得电话打不通,去草原也不知会我一声?”
“你还好吧?”
“还好,刚开始感觉还新鲜,可早就呆不住了,想回来,但人多不方便,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回来后给你讲讲我的见闻。”
“好,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礼拜之内,对了,去看牡蛎了吗?”
“去了,但没有见着人。”我照实回答。
“也罢,回来时候带牡蛎一块来机场接我,记住,一块来,如果就你一个人,我是不会见你的。”
“记住了,一路平安。”
“很想你,晚上会梦见你的。”电话另一端的杨五一娇滴滴地说。
九
几日后,画展如期举行,虽然我已于前一天从母亲那里得到消息,但晚上,苏宛如还是打来电话。
“明天可一定要来啊。”她叮嘱道。
“一定,放心吧,我记着呢。”
“我给你准备了墨镜,如果怕被别人认出来的话。”
“你是说当我站在你的作品前的时候?”
“是的,不算多此一举吧?”
“想得很周到。”
画展是在交通大学的礼堂举行的,我看见了自己,确切的说是我看见了一个陌生而亲切的自己,在这个名流会聚的地方,我戴着墨镜站在苏宛如的作品面前,有很多人驻足观看,很多的人,几乎要将最先站在作品面前的我挤出去,原本没有欣赏其它作品的想法,所以就一直站在苏宛如的作品面前。
人群中发出喳喳的赞叹,赞叹作品的传神,赞叹它的强烈的感染力,更赞叹它出自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小女孩之笔。
半小时后,我摘去墨镜,开始听苏宛如对作品的介绍。
“当一个人心思最为繁重的时候,最先表现出的是他的眼睛,内心深出的忧郁和思念就会从眼睛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这是忌讳眼泪的表达,语言没有介入,从创作者的角度讲,我捕捉到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么博大而又如此细腻……”
我重新戴上墨镜,眼前出现无穷无尽的幻景,交替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