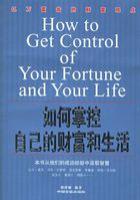“哼!”碧荷听罢,不由得冷笑一声,“倒好大的驾子,让我们娘娘去瞧她。”
潇云恨王夫人恨得牙痒,正愁无处释放心中那口怒气。她拢出插在玉颈瓶里凤藻宫送来的吐艳鲜花,一片一片将花瓣摘掉,又将所余花RUI扔在地上狠狠踩踏,淡黄色的汁液在洁白的地毯上绽放为一朵金色的迎春花。
云贵妃入宫时间不长,却颇得后宫太监、宫女的敬慕。太监、宫女们无论有事没事总会找到一些由头来给云贵妃请安。但凡进了临安宫,任谁也没有空手出来的时候。云贵妃的名头在后宫叫得越发响亮。
难得可贵的是,云贵妃并没有侍宠而骄,养福宫晨昏定省,一天都没落过。云贵妃还每日抽出时间往贤妃、兰妃等处闲话家常,姐姐长姐姐短,从没乱过理数。
太后细细品之,这云贵妃年纪虽轻,若不是出身卑微了些,确有母仪之相。
潇云守住临安宫,悄然计算着日子,只等龙子上身。
这些日子,水溶细察水涵行为举止。
他恪守水家祖训,对上至孝,对下礼贤,颇有当年父王之风采。只是其母李婵儿心藏狡诈,绝不是等闲之辈,须小心提防。因百缘寺之事,水溶终日闷闷不乐,难展欢颜。
“师兄,水涵与你一脉相承,也算是出身百缘寺,我绝不会看着百缘寺同门师兄再遭屠戮。”这日水涵来朱雀楼请安,忽然目光灼灼地说道。
水溶抬起刀削的棱角,挑起墨染的剑眉,心潮掀起万丈波涛。听他话中之意,看他眸底卷起的漩涡,他对当今堪是不满,辅王是他的亲表舅,他能悖逆当今?水溶疑惑地想道。是了,有什么可不想的呢?辅王还是大师兄的亲弟弟。唉!权谋之术,误了多少卿卿性命。
“师兄,唉。”水涵眼里闪过一丝前楚,喉结上下滑动,下了决心似地开口说道:“天下都道,圣上了厚待我水家。只是我知道,父王和兄长……”水涵漆黑的眸子深不见底,这是隐在他心底最深的痛。他记得你王永远都给他一个背影,从没正眼过他一次。他曾在心底无数次说过,父王,涵儿早晚让你刮目相看。一场变故,水家罹难,庶出的他终于可以挑起家族的重担。
水溶将水涵眼中那抹伤痛收在眼底,此是的水涵一如儿时的某个清晨,他低垂着头在其母身后,眼里了含着一汪清泉,楚楚可怜地轻唤着:“涵儿给父王请安。”父王总是吝啬地不给他一丝笑容,只挥挥手让年幼的水涵退下。水溶一直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水溶知道了答案。父王定是因为辅王之故,才不喜欢水涵。可是,他分明是,想到此水溶艰难地张了张嘴,而后猛地咽了口水,将“弟弟”二字硬生生咽回肚子里,轻飘飘吐出三字,“好好练功吧!”
“是。”水涵收回思绪,眨眨蒙雾双眼,咬了咬牙挥动双掌,纯洁的槐树随着掌风轻轻漫舞。
阴雨缠缠绵绵下个不停,百缘寺罹难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下来,春纤黑了也瘦了,宽服大袖套在她身上,看起来就像错穿了大人衣服的孩子。她夙兴夜寐,仍然没查到忘我大师下落,她甚至怀疑忘我大师已随那场大火化了。更让她心焦的是,师兄也有一个月没通音信了。
黛玉看着春纤的沉默,她心也开始不安稳起来。
宝玉缠绵病榻一个月有余,整个人清瘦了不少,原本婴儿般肥嫩嫩的脸,居然也有了些棱角。大病一场,宝玉转了性子。将屋里侍候的秋纹和麝月给了银子,任其赎身。一应饮食起居皆由贴身小厮侍候,身子再硬郎些他便搬出内宅,另择了院子,开始回学堂念书习武。
贾母和王夫人惊讶于宝玉的变化,王夫人暗暗窃喜,宝玉总算是长进了。只是贾母心里空落落,终日若有所失。
贾府日渐热闹,京城诰命贵妇不是来拜见贾母和王夫人便请求觐见公主和郡主。
贾母以二人懒见外客为由,依依回绝。各府的贺礼却填平了贾府的亏空。
“春纤,我想回趟林府老宅。”终于在一个飘雨的黄昏,黛玉再也沉不住气了。
“姑娘,且再等等。”春纤绷紧巴掌大的小脸,摇头说道。
“还等什么?”黛玉秋水般的眸子,漾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林家老宅地处偏僻,可近一个月来常来做买叫卖的在宅子附近转悠,我担心……”春纤伸出食指向皇宫方向指了指,“怕是上头派人盯着呢!怕是也盯着咱们呢。”
黛玉听罢,颓然地吐了口气,焦灼地说道:“这都一个月了,也不知道忘我大师他们脱险了没有?难道爹爹也被盯上了?”
“姑娘不必担心,若是上头抓住师兄的辫子,他早对咱们下手了。”春纤笃定地说道。
“嗯。”黛玉轻叹一声,如风雨中被淋湿了翅膀的蝴蝶。脑海中浮现忘尘的身影,可卿芳踪难觅,不知他哪儿去了?
春纤看出黛玉所想,却也不点破。小和尚离开京城已经有些日子,算算行该到江南了。
七天前水溶趁着夜色出了京城。城外,他脱了僧衣,换上早准备好的华服,光头沾了头套,用根簪子别住头发。
月光下,一俊逸美男打马离京。直奔记忆中的江南林府。
李国丈奉命早已悄悄到了江南,派出无数眼线日夜盯着江南林府。林如海或骑马或坐轿,每日两点一线,不是府衙门就是林府,李国丈找不到丝毫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