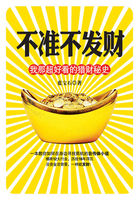“那怎么不坐火车啊?出去山就有车站。”刘汉卿难过地问。
“火车?什么叫火车啊?”褚大婶一脸困惑。
刘汉卿一下子明白了,山里很多人没见过火车。他心里觉得惭愧:我们这些人,虽然参加过浴血战斗,但我们上过军史、当过领导、去过各地大城市,而这些真正支持着战争基础的群众,却在这个山窝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想到这些,他直觉得揪心。
田大爷提着一个水壶,拿着一袋干粮,递到刘汉卿的手上:“带着在山坡上吃。捷舟你的驴正在吃草,你先帮着把羊赶到山坡上。”
刘汉卿提着赶羊鞭,转过身去,吆喝着羊群,正要上山,一群年轻人挑着一摞摞的条筐走了过来。
“孩子们,走得这么早,是往山下送吧?”田大爷跟在刘汉卿身后,惊喜地问。
“是啊,”领头的青年答道,“刘书记不是要求这个月底,必须把筐送到山下吗?长江大桥拦水筑墩,正等着急用呢!咱们朱崖支援国家建设项目,还从来没落后过!”
“唉,”田大爷长叹一声,“咱们倒是没落后,刘书记可落下来了!”
“刘书记怎么了?”年轻人停住脚步问。
“这不被打成右派,到咱这儿放羊来了吗?”田大爷指了指已走向山坡的刘汉卿。
“听说刘书记没日没夜地为国家建设操心费力,我们就是冲他这颗心,才不讲价钱,翻山越岭,割荆条,编筐篓。他这么好的人成了右派,难道当初他领导错了?那我们还支援什么?”“哐、哐”几声,年轻人们把扁担一撂,不走了。
走上山坡的刘汉卿听到身后的对话,赶紧回转过来。“这位兄弟”,他上前几步,拍拍带头青年的肩膀,面向众人,耐心地劝道,“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有空应该多和田大爷、褚大婶聊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当初干革命,就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当官。如果我们打江山,是为了坐天下,那和过去的农民起义、山大王就没什么区别了。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我们共产党人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不计待遇,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才取得解放后这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大家想想,刚解放时,我们有什么?连盒火柴都造不出来,用的是‘洋火’!这些年,我国建成投产了595个大中型工程,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成果。现在,我们能造汽车,造飞机,造轮船,模拟式计算机前不久也研制成功了;今年,我们的钢产量、煤产量,粮食、棉花产量,发电量都创了新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望超额完成……长江大桥是我们国家的重点工程啊,它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我们支援的任务耽误不得!”
年轻人听得直点头,田大爷也过来劝说:“孩子们,这个‘反右’的事,我弄不懂,但国家建设是实实在在的事,你落后,人家就欺负你!老刘说得对,天不早了,快赶路吧!”
年轻人不情愿地把扁担挑到了肩上,望着刘汉卿,刘汉卿挥了挥手,说:“为了国家的解放和富强,我们多少先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有多少人被误解过,我们庙崖就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流得太多,才改成了朱崖。在私欲还没有根除的时代,失误和误解看来是难免的,但和国家利益比,个人的进退荣辱算得了什么?”
“走吧!”带头的年轻人终于迈开了脚步,一行人迤逦远去。
望着他们消失在山路尽头的身影,捷舟帮刘汉卿把羊群赶到山上,羊儿贪婪地吃起草来,捷舟给刘汉卿打开布包,准备让他吃饭。
“哎,请问老乡,这个村是庙崖吗?”一个瘦高个子,背部驼弯,戴着眼镜,身着一套不中不西服装的人,正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下问路。
“是啊,你不是本村的吧?”捷舟问。
“对,我是来探亲的。”山下的人回答。
“听你口音好像胶东的?”刘汉卿好奇地问了一句。
“是啊,胶东樊村的。”
“樊村的?”刘汉卿不禁来了兴趣,“我一个同学就是樊村的,名叫姚自芳,你知道吗?”
“啊?你怎么认识的?”
“那是我同班同学。”
来人上下打量了刘汉卿一会儿:“你是刘汉卿吧?我就是姚自芳。”来人激动地向山上跑来。
两个久违的同学没想到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地方见面了。从两个人的交谈中,捷舟得知:大学毕业后,姚自芳到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结婚、生子,日子过得挺美满。谁想从四十年代末开始,为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美国麦卡锡主义抬头,而且越刮越凶,一亿多人口的美国,竟有八百多万人列入黑名单,有些四五岁的孩子都被列了进去。姚自芳工作生活中谨慎了又谨慎,谁料1954年还是被列上了黑名单。工作受到了影响,日常生活被监视。后来又被遣往偏僻的外地,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带领全家去了墨西哥,又从那到了南美洲。这些国家,近几年政党纷争,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工作难找,他儿子得了心肌炎,无钱治疗,他和妻子靠卖血维持儿子的治疗和一家的生活。后来,辗转到了印度,通过中国大使馆才回到国内。抗战时,日寇从胶东登陆,烧杀抢掠,他有个姑姑为躲避战乱,嫁到了庙崖,父亲考虑到这里是偏远地区,崇山峻岭,就带上家中的银元来到这里,埋在了姑姑家房后的一个山坡下。从国外回来后,全家被安排在青岛,为了给孩子治病和恢复身体,他专门找到这里,想看看姑姑和当年父亲埋下的银元还有没有。
“美国也在划右派啊!还划了这么多?”捷舟不解地问。
“不,他们是划左派!”姚自芳解释,“他们自己这样做,还攻击中国呢!”
听到这里,捷舟不由想起,近些日子,人们对反右的议论,埋怨情绪顿时少了些:“‘反右’扩大化把那么多人打成右派,不实事求是。但世界上不少政党与政府似乎都出过这种毛病,这是为什么呢?”他苦苦思索起来。
三个人正在聊着,田大爷牵着毛驴来到山下,他递给捷舟一包吃的说:“孩子,还有两天的路呢,边吃边走吧。”
天上的太阳,已经一竿多高了,为了赶路,捷舟挥手告别了田大爷和刘汉卿,回到古州,他根据要求,把一路的见闻写了下来,由学校交到地委。文中的情节勾起领导们对战争年代的记忆,都称赞写得实,没人挑刺。
但是,古州的形势仍在发生着变化,甄广怀接任专员后,心里有点虚,怕刘汉卿找关系再翻过身来,也怕刘汉卿揭他的短,更怕自己威信不高,群众背后骂自己,压不住阵脚。他想了很多办法,一心一意要把刘汉卿在古州搞臭。过去和刘汉卿走得近的人,他不断旁敲侧击,要他们划清界线,并且调整了好几个干部,以期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为了迎合甄广怀的心思,说刘汉卿坏话的干部多起来了。过去刘汉卿关怀多的人,有的为了划清界限,忙着表现自己。
刘汉卿过去带工作组下乡,老百姓多炒了个菜,喝了几盅酒,也有人上纲上线地揭发。
……
天天往刘汉卿家跑的杨林,压力越来越大,渐渐地有点承受不住了。有人为了揭发刘汉卿立功,把主意打到了杨林身上:这小子本来是日伪人员,却进机关、入了党、当了副处长,这是刘汉卿任用坏人的铁证。一张大字报在起草中,为了在文中“刻画”好杨林的形象,两个起草人看到杨林正在院里活动,专门跑过去上下打量,那眼神好似在端详可供自己往上爬的垫脚石,怪怪的、刺刺的,杨林直觉浑身发麻,冷嗖嗖的。
“不怕他们,我要坚持住,刘书记对我不错,是他把我从雪地里救出来的。”杨林躲过目光坚持着。
但是,四道冷光继续射来,偶然路过的干部,不自主地停下脚步,像看怪物似地瞅他几眼。慢慢的,他觉得那眼神透骨彻髓,比当年埋在雪里时还刺骨。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贴出了大字报——《我所认识的刘汉卿》。内容是说,当初刘汉卿为什么用他,是因为知道他有水平。刘汉卿的许多讲话,本来都是他准备发言的内容,结果让刘汉卿拿走了,讲后还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刘汉卿是窃贼、伪君子……
甄广怀认定杨林是刘汉卿的人,正默许下边拿他开刀,看到这张大字报,他高兴极了,这可是对刘汉卿反戈一击的活典型!在专署机关大会上,他表扬了杨林。在私下对杨林说:“好好干,前程远大着呢!”
杨林受到了鼓舞,又写了几张诋毁刘汉卿的大字报。机关干部和古州的老百姓知道后,背后都骂这些诋毁刘汉卿的人是坏了良心,杨林和魏建忠这两个人最坏,当初刘书记对他们那么好,他们现在这样做,简直狗都不如。魏建忠听到这些话心里难过,晚上常常睡不着觉。
杨林开始还不好意思见人,慢慢的,他不在乎了,麻木了,没事就往甄广怀家跑。不久,他由副处长提为副局长,和甄广怀气味相投,关系亲密,经常一起聊天,谈论怎么让刘汉卿再也翻不过身来。
杨林已经三十三岁了,一直独身。一天,甄广怀关心地劝他:“杨林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旧社会受到挫折,没有结婚,现在也该讨个老婆了。”
杨林无奈地说:“我已错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现在年纪大的我看不上,年纪轻的人不愿意跟我。”
“你看刘汉卿的妻子湘绮怎么样?年轻漂亮,端庄聪慧,在古州算是第一美人。”甄广怀不怀好意地指点着,他暗自盘算:这可是从心灵上击溃刘汉卿的好机会。
“那怎么成啊!”杨林不好意思地推辞道。
“怎么不成?论年龄,你比刘汉卿小,论地位,你是副局长,他是右派。”甄广怀继续诱导。
“湘绮不会同意吧?她对刘汉卿爱得很深。”
“咳,什么爱不爱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吃饭睡觉过日子吗?只要逼她就了范、结了婚,还不就是一对夫妻?”甄广怀怂恿着。
甄广怀引燃的欲望之火,使杨林很快迷上了湘绮。一个月后,不知他使了什么魔法,湘绮竟给刘汉卿寄去了要求离婚的信件。
这封信对刘汉卿的打击太大了,一直乐观的他一天不吃也不喝。儿子剑超特意从古州赶来,默默地站在床前,不断地劝慰。刘汉卿忽然坐起来,提笔写了一封长信,给湘绮带回去。他对剑超说:“我想通了,你阿姨还年轻,人不错,未来的路还长,既然她想离开,对她未来有好处,我也从此少一份牵挂。”
杨林和湘绮很快结婚了。古州的人们惦念着刘汉卿,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刘汉卿为古州的发展所做的工作,他走后,人们对湘绮都很尊重,上班、购物,抢着给她提供方便。现在听说她离婚了,而且和背叛了刘书记的杨林结婚,都很气愤,常在背后骂杨林是“白眼狼”,骂湘绮是“狐狸精”。
一个个风波,像冰刀霜剑般刺痛剑超年少的心灵,他又病倒了。捷舟跑去看他。湘绮也提着鸡汤来到病房,剑超气愤地把她赶了出去。捷舟似乎觉得湘绮有许多难言之隐,跑到门前问:“阿姨,还有其他事吗?”
湘绮无奈地说:“飘雪了,汉卿还有好多衣服没带,想找人给他送去,可是,现在谁敢沾边啊?这人心,变得也太快了!”秋夜的凉风掠起湘绮的衣角,她打了个寒战。
“何止人心啊!反右斗争,使人们对党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身后传来一个医生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