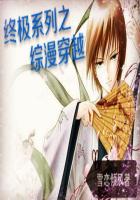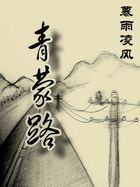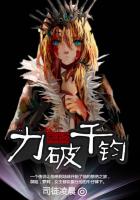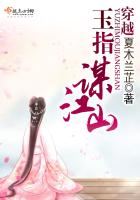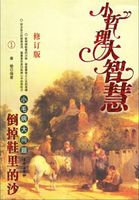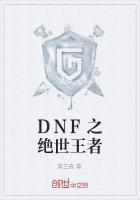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儿童文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儿童文学比之昔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的重庆儿童文学也与全国的发展形势同步,在民间儿童文学得以继续深化发展的配合与影响下,文人儿童文学得到飞跃发展,乃至形成重庆儿童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当然,若就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新时期以前的重庆儿童文学看,可根据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为两个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与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两个时段的发展形势各具特点与规模,表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儿童文学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 建国后17年的重庆儿童文学
共和国成立最初17年的重庆儿童文学,比之解放前是呈飞跃发展上升势头的,但这发展却分别显示于民间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掘与文人儿童文学风起云涌的巨大发展。
重庆民间口头儿童文学的发掘,首先体现在孙铭勋对巴渝儿歌的搜集整理上。孙铭勋是我国杰出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积极追随者和实践者。解放前夕,他在重庆按陶行知教育思想和主张办学。他因为爱孩子而在教育界获得“孙妈妈”的别称。孙铭勋对重庆儿童文学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以拓林为笔名,于1956年在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四川儿歌》。
在拓林儿歌中,形式短小活泼的游戏歌,是最精彩的部分。如《推磨摇磨》只有六句16个字:
推磨,
摇磨,
推粑粑,
请家家。
推豆腐,
请舅母。
搜集者在此童谣后加了一段文字来说明此游戏的做法。即:“和两三岁小孩对坐,拉着手,一进一退,作推磨摇磨状,同时唱这支歌。家家即外婆。”这不仅反映了成人与幼儿共同进行亲子游戏的重庆民间习俗,而且对儿歌具有可操作性的游戏精神予以了表现。更重要的是,童谣语句简洁通俗,特别通过叠词把童谣的用字减少到最低限度,很适于3―5岁未入学孩子的吟诵。加之词句琅琅上口,韵味十足,有助于孩提记忆。
与《推磨摇磨》类似的具体帮助幼儿进行游戏活动的精短童谣,在拓林儿歌中还有《虫虫飞》、《抽中指》等作品也很精彩。童谣如口语般长短句结合,语调铿锵,趣味浓烈,不仅表现了幼儿的烂漫天真,而且显示了巴渝乡村和小市民育儿过程中所显现的两代人之间的亲密无间关系。
在拓林儿歌中,还有把游戏与简单的劳作结合起来加以艺术描摹的。比如另一首描写推磨的儿歌唱道:
推磨,
摇磨,
干粑,
十个。
吃不完,
放在妈妈枕头边。
耗儿衔到踏板边,
猫儿衔到床角边,
狗儿衔到大门前,
老鹰衔到柏树颠。
得尔斯!得尔斯!
此童谣的前半,用两字一顿的语调来逼真表现推磨的动作节奏。后半则自然过渡到儿歌惯用的七字句,特别还用排比修辞来描摹耗儿、猫儿、狗儿和老鹰等四种动物偷吃干粑所造成的恶果,虽然十分夸张,但令孩提感到极大兴味。末尾二句,则以巴渝民众驱赶吆喝动物的象声词结尾,充满浓烈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征。
拓林儿歌除了以其内容的游戏性征服小读者之外,经他整理的儿谣还爱采用不同表现手法来反映作品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比如,《什么出来高又高》、《什么弯弯在天边》二诗均以一系列问句与答句的前后排列构成问答式,《十匹马儿跑》将从1到10的数词巧妙镶嵌在诗句之中构成数数歌,《捉小鸡》则以前句引出后句的顶真修辞方式推进情节发展而显示巴渝幼童的幽默感。上述作品因其艺术个性的鲜明生动,自20世纪50年代入选《四川儿歌》以来,数十年来还多次被我国各地陆续推出的各种优秀儿歌童谣选本所收录,这就极大提升了重庆口传儿歌在全国民间口头儿童文学中的地位。
1956年12月,重庆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编辑的综合性儿童文学选集《金贵明和他的爸爸》,内中选了李南力整理的民间故事《三个秀才》,这也是重庆民间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该故事不仅情节紧凑,而且由于大胆揭露封建官僚贪鄙的嘴脸,和讥刺穷秀才迂腐的书生气,所以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余地。
建国17年的重庆儿童文学在民间口传儿歌基础上,文人的儿童文学创作受到较大影响,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之中,首先应提及的是张继楼的儿歌和儿童诗的写作。张继楼是江苏宜兴人,从小受到苏南传统儿歌如“萤火虫,夜夜红,公公挑水浇胡葱”的影响,解放前夕随西南服务团文艺队入渝以来,非常注重对于重庆曲艺及民间文学的学习。重庆口传民间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极大地征服感染了张继楼。因此,他从1956年出版第一本童话诗集《母鸡和耗子》开始,陆续推出《唱个歌儿给外婆听》、《在城市的大街上》(1960)、《夏天到来虫虫飞》(1963)、《在农村的田野上》(1964)等儿童文学专集。
张继楼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儿歌显然是最出色的。而在他的众多儿歌中,尤以组诗《夏天到来虫虫飞》在全国的影响最大。该组诗通过对蚱蜢、蜜蜂、蜻蜓、蜈蚣、蚊子、蜘蛛、叫哥哥、萤火虫等八种昆虫的素描,把孩提顽皮与聪敏的个性都予以极传神的描摹。比如《蚱蜢》:
小蚱蜢,
学跳高,
一跳跳上狗尾草。
腿一弹,
脚一跷,
“哪个有我跳得高?”
草一摇,
摔一跤,
头上跌个大青包。
此诗虽只39字,但却对蚱蜢这自以为掌握了跳高技巧而洋洋得意的顽皮孩子形象,做了传神的白描。诗句用腿弹、脚跷、草摇这样极简约的造句,让儿歌用字显得更为洗练,准确地切合了幼儿对诗的理解。三个小节的末行虽为七字句,但既切合孩提口吻,又未用一个难字难词。语言简洁传神,这正是诗人技巧趋于成熟的表现。
张继楼在写儿歌的同时,还创作了一些适合幼儿阅读的短诗。作者从幼儿视觉出发,把电车比拟为“拖着辫子的姑娘”,把洒水车看成长着“雪白胡子”的老人,把林中蘑菇描写成头戴斗笠的娃娃,把黄桷树视为“鼓着绿色手掌”的山城卫士。这些充分体现了儿童奇妙想象的小诗,大部分收集在《城市的大街上》和《童年的彩墨画》等组诗中。
在建国17年的重庆儿童诗中,令人们不能忘怀的,还有军旅诗人雁翼与梁上泉。他们所写儿童诗的共同特点,就是往往以一个军人的视角切入童年生活。一文中谈起自己为什么要创作儿童文学时说过:“一个作家,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他个人的经历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的许多小战友们,在战场上牺牲了,可是我还活着。我的活和他们的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也许,正是他们英勇的死,才有我的活……’因此,艺术地记录他们的战绩,艺术地再现他们的形象,便成了我的创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雁翼1927年生于山东馆陶的卫河边,由于日寇的入侵,他14岁就参加八路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他先后任过勤务员、通讯员、警卫员和班长、排长等职务。青少年时代的戎马生涯,给诗人开辟了广阔的文学视野。因为他的许多小战友在残酷的战争生活中大部分都牺牲了,所以当雁翼成为诗人后,为了表达自己对逝者的怀念,他自然常常取材于其小战友的英雄事迹。
另一方面,雁翼之所以爱写儿童诗,也和他那难以忘怀的童年情结是分不开的。他曾在《儿童诗美的基础》见1981年7月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第7辑。一文中说过:“每一个人都享有自己的童年。”“童年的感情生活,是最富于浪漫色彩的。”“童年的思想,是最纯真的,纯真得像花朵上早晨的露珠。”“童年的心灵,是最洁白的,洁白得如水晶般透明。”“因而,人的童年,从本质上讲,是诗的。”雁翼如此留恋童真童趣,当他成为一个诗人,就不能不写童诗。
最能代表雁翼儿童诗创作成就的,是他的长篇叙事诗处女作《东平湖的鸟声》。该诗初稿于1956―1957年,1959年定稿。1959年在《少年文艺》杂志发表后,次年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该诗单行本。此诗除获得建国10周年优秀少儿文学一等奖外,还被译介到朝鲜等国出版。1965年作者又在该诗基础上加以扩展,续写了第二、三部《平原烈马》和《黄河红帆》。这三部系列长诗以后分别改名为《鸟声》《烈马》《红帆》,并总题为《紫燕传》,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80年该诗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第二次评奖的二等奖。这是至今为止重庆儿童文学创作在全国获得的最高奖项之一。1975年,作者根据《紫燕传》第一、二部改编为电影《黄河少年》,经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和放映后,更扩大了重庆儿童文学创作在全国的影响。
《东平湖的鸟声》在结构上由序歌和10个章节组成,叙写游击队侦察员小赵模仿鸟儿叫声在东平湖里向战友传递情报,后被日军发现而受伤被捕;几经身体摧残和出生入死考验后,小赵终于带着新发现的情报,机智逃出敌人魔掌而和正在寻找他的部队会合。叙事长诗透过惊险紧凑的故事情节、优美抒情的语言,将小赵临危不惧、机智勇敢的个性特征给予了生动的展示。
与雁翼比肩的另一军旅诗人梁上泉,也因他对孩子始终怀有一颗爱心而在从事成人诗创作的同时,热衷于儿童诗写作。他曾在近作《不老草》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6月版。的《人生印痕》中吟唱过:“放牛沿着童年的小路,/赤脚沾满清凉的晓露。”“童年吃过的清明粑,/到老还没完全消化。”这说明那永难忘怀的童年情结,是促成他为儿童写诗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中,梁上泉的儿童诗,除集中收录于195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的《从北京唱到边疆》(24首)、196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的《小雪花》(叙事诗)之外,散见的儿童诗还有辑录在1954年作家出版社所出的《山泉集》中的《孩子陪伴着我》、《将军夜过巴州》、《号兵的怀念》、《历史的风暴》、《还乡行》、《列车上》,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的《云南的云》中的《戴盾牌的老师》、《阿瓦山的儿子》,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所出的《寄在巴山蜀水间》中的《唱不完的颂歌》、《祖母的画像》,1962年重庆人民出版社所出的《大巴山月》中的《将军与孩子》、《题园林中学》,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歌飞大凉山》中的《桥》、《绿焰如火》等作品。通过上述诗作的比较研究发现,梁上泉儿童诗除少量以叙事为主的长诗如《祖母的画像》、《小雪花》和《火云鸟》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之外,大多系抒情短章。这些诗作不仅质朴明朗,感情真挚,充满童心,而且在艺术构思上,多以第一人称“我”的眼光去透视和描摹色彩缤纷的现实。因梁上泉在40多年前是以军旅诗人的身份闯入文坛的,所以他那童诗中的“我”,自然常以军人的姿态去审视和关注孩子生活,从而生动表现出两代人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和谐关系。这之中,除了写边防战士收到少先队员来信的《遥寄》,写边防战士歌声飞扬的《从北京唱到边疆》,写边防兵巡哨怕把熟睡孩子惊醒的《脚步轻轻》等诗外,还有好些同类型诗作都是以典型细节的描写而在读者中留下难忘印象的。诗人于1956年所写的《阿佤山的儿子》,以一个边防战士的眼光去观察诗歌主人公――小弟弟,他因“生长在阿佤山的峰顶,/从小就不怕雷雨风暴”,所以:
呵,我看见一个英武的民族,
在祖国的面前挺直了腰;
我看见一个未来的士兵,
站立在边防最前哨。
在诗中,作者以阿佤山孩子的年幼反衬其气质的高昂,从而把一个民族的新生予以了生动的展示。
儿童诗固然一般都会描写儿童,但梁上泉的儿童诗有时却并不直接描写儿童而只叙写与儿童有关的某些事物。如《孩子陪伴着我》写一个高原汽车兵的驾驶室里贴着一张《我们热爱和平》的招贴画,从而给主人公带来一片温暖。呈现在军人视角里的虽不是真实的孩子而只是一幅画片,但却同样起到了表现和描摹童心的作用。
在梁上泉的军人视角诗中,还有《将军夜过巴州》因用父女对话直接倾诉衷肠的方式写作,也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该诗一下笔,便以短句而像小令般的欢快语调,把小读者引向历经战火洗礼而今又变得更加壮美的巴州城下。且听:“兵车喇叭欢奏,/将军夜过巴州。/巴州城越来越近,/灯火垒起重楼,/他女儿睁开大眼,/向父亲的故乡问候。”接下来,便是父女俩关于故乡的城墙、广场、山脉和军歌的妙问巧答,由此表现了激荡在将军胸怀的一片赤子之心。
在建国17年的重庆文坛,还有与雁翼、梁上泉儿童诗风格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诗作,那就是充满沉重悲凉气氛的石天河童话诗。
石天河(1924―),原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23岁开始文学活动,次年在南京涉足新闻而参加革命地下工作。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军大西南。1952年在四川文联编《星星》诗刊,兼搞文学评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判刑劳改。平反后,他一直在永川的重庆师专即今之重庆文理学院执教。
1957年春天,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他萌生了歌颂艺术自由的强烈欲望,再加之诗人赤子之心始终不改,如此双重诱惑力的驱策,遂使作家先后创作了童话诗《无孽龙》和《少年石匠》。
或许就是因为石天河童年时在家挨过饿的缘故,所以他的那显然融合了自己生活经历的童话诗《无孽龙》见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8月版《石天河文集》第一卷。虽与20余年前巴金创作的童话《隐身珠》都取材于流传在四川灌县岷江河畔的民间传说“望娘滩”,而且主题颇有些相似――巴金童话意在颂扬教师鼓动种田人造反,石天河童诗则主要是向孩子讲述穷人对财主的复仇――但二者在构思与艺术表现上,又有明显的差异。
其一,巴金童话为散文体,因而展示情节与细节更细腻充分,而石天河童话为叙事诗体,所以在情节与情节之间的省略与跳跃则表现得更突出,这便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想象与思考的余地。
其二,巴金童话虚构主人公因放生被逮住的鱼儿而得到宝珠,石天河童话则说宝珠来源于主人公发现的那棵被视为朋友的野草。足见二者的基本情节有所不同。
此外,石天河童话结尾,还保留了原民间传说关于巨龙告别母亲时,因一步一回头?望其母而变成一个个“望娘滩”的细节,这种对岷江中石滩形成原因的神话化解释虽然荒诞,但却富于积极的科学探索精神。再有,石天河童话诗一方面肯定原有民间传说将弃母而去的龙称为“孽龙”,另一方面又因他为复仇而必然表现出对财主恶人的凶狠,所以决意“为他辩护”而改称其为“无孽龙”。石天河童话诗对主人公幻化为龙的情节做了如此辩证处理,其含义也颇引人深思。
建国17年的重庆文人儿童诗创作除集中显示于上述诸人的作品之外,本地综合性儿童文学集《金贵明和他的爸爸》一书,也收录了另一些重庆诗人的作品。这之中,杨星火的《黄河的秘密》,因抒写黄河治理引起孩子们关于黄河名称来历的争论,而引发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此诗熔叙事、抒情于一炉,把孩子们十分向往治黄工程的心理活动予以幽默机智的表现。
建国17年的重庆儿童文苑,除了儿童诗,还有儿童小说创作也不可小觑。其代表作家有揭祥麟等人。揭祥麟(1926―),重庆人,1944年,由于爱读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渝出版的《新华日报》,揭祥麟思想受到启发。后来,他把自己家贫而饱受病魔折腾的情况写信告诉报馆编辑先生。他在信末说,“现在虽‘劫后余生’,要活下去却很不容易。”几天后,该报“群众”专栏将他的原信与编辑先生的回复全部刊登出来。因为报纸鼓励他一定要有信心战胜病魔,用余生来为人民服务,所以揭祥麟在以后的业余创作中,便用“揭余生”来做了自己的笔名,同时还用另一笔名“鹿角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后来揭祥麟开始给陈伯吹在渝主持的刊物《小朋友》和重庆另一杂志《儿童世界》投稿,从而磨练了自己的创作技巧。《儿童世界》主编何公超有一次看了揭祥麟的来稿后,很赞赏他笔头所显露的儿童生活气息,于是复信鼓励他说:“祥麟小朋友,你写的儿童小说有生活,观察也很细。希望你多写一些孩子们喜欢的故事,讲给那些和你一样有过痛苦经历的孩子们听。”从此,他便和儿童文学结下深深的情缘,数十年一直未曾间断。1948年,揭祥麟在重庆乡间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尔后开始主编中共重庆地下组织所办《儿童生活报》。解放后,任共青团西南工委《红领巾》杂志编辑组长,后为中国作协重庆分会专业作家。“文革”以后,曾任重庆《世界儿童》杂志主编。1958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其代表作为三部中篇小说,即《桂花村的孩子们》、《抗丁记》、《雷雨前后》以上三个中篇等。
《桂花村的孩子们》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作品,曾获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三等奖。小说以农业社的秋收为背景,通过共青团支部书记曾贞组织孩子们拾谷穗的活动,把重庆山乡孩子们的生活和当地风土人情予以生动的表现。该小说还十分注重顽皮孩子的形象塑造。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了解孩子,善于组织情节和捕捉生活细节,使得作品自始至终像一幅色彩鲜艳的农村生活图画一般,再现了质朴勤劳的农民及其年少一代的精神风貌。
另一中篇《雷雨前后》通过一个叫满喜的少年几十天生活经历的叙写,一方面成功刻画了主人公活泼天真、热爱集体的可贵品格,另一方面表现了面对自然灾害考验的山乡农民的坚强勇毅。此外,该小说还通过富于幻想的另一少年向觉智熬尿取肥的科学实验描述,把故事展示得情趣横生,耐人嚼读。
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曾在撰文评介揭祥麟儿童小说时说:“他的作品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性强,富有真实感。他的作品语言明快而形象,表达事物、描绘人物常常形神毕现,甚有‘龙门阵’风味,因此揭祥麟充满泥土气息的中、短篇小说,一直受到小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除揭祥麟儿童小说外,建国17年间的重庆儿童小说还有纪朵的短篇《金贵明和他的爸爸》也值得一提。该小说因集中写采煤区区长和他的儿子金贵明发生在一天的故事,笔墨显得凝练集中。该小说虽然受当时流行的教育小说影响而不能把文学的审美摆在艺术描写的重要位置,但因其笔调清新而仍然能受到小读者的欢迎。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儿童文学
“文革”十年的重庆儿童文学,是畸形的文学。其作品在数量、质量与体裁门类上虽然远不及昔日,但其存在的事实却是不可抹杀的。此阶段的重庆儿童文学主要体现于儿童诗歌与儿童生活故事的创作。
一、儿童诗歌
文化大革命中,昔日为孩子写诗的作家都通通被打倒了,“文革”中的孩子们唱什么歌呢?据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安排到重庆图书馆来接受思想改造的作家陈荒煤回忆,“文革”中的重庆中学生最爱唱的就是从北京传来的《嚎歌》。所谓嚎歌,原是造反派强迫“牛鬼蛇神”们在接受红卫兵或群众组织批斗时唱的哀歌,其歌词为:“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嚎歌》的实质是红卫兵群众组织为“牛鬼”们代拟的强迫其认罪的自我哀鸣,最早流行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原党委书记李伯钊在其“文集”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和描述。以后受京版“嚎歌”影响,重庆红卫兵也编了与此类似的嚎歌,其中有“刘少奇,垮了台,孝子贤孙哭哀哀”之类的句子。
《嚎歌》的影响和辐射力是十分巨大的。由《嚎歌》派生出的同样体现了“文革”特点的其他红卫兵歌谣,还有以“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和“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为警句的红卫兵战歌,也值得一提。但这些作品大多是流行政治概念的图解,缺乏独特鲜明的个性描写和艺术价值。
受到嚎歌战歌高喊政治口号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重庆唯一的媒体《重庆日报》,也发表过不少以某区“红小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名义创作演出的歌谣。比如在1972年6月5日的该报“山花烂漫”副刊上,登载过一篇儿童歌舞表演《我们全家都是兵》。这其实就是一组儿歌大联唱,其中小主人公的爸爸是炼钢工,妈妈是街道治安委员,哥哥是解放军。他们的唱词都充满了标语口号与强烈火药味,与昔日红卫兵歌谣的内容和艺术风格完全如出一辙。与《我们全家都是兵》发表于同一版面的,还有题为《怀念你,印度支那的小战友》的儿童朗诵诗。该作品一开篇就有这样几句,“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寻找印度支那。/密林里的小战友啊,/此刻你们战斗在哪座山下?/神圣领土不容敌人侵犯,/仇恨的烈火在心中燃烧,/你们多么勇敢,多么坚强,/满腔怒火把敌杀!”同样,除了空喊口号,此诗还力求向国外输出阶级斗争理论,显示了在极左的年代某种革命救世主的姿态。
“文革”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四人帮”在炮制《沙家浜》等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同时,还炮制了天津小靳庄的农民诗歌和北京西四北小学的儿歌创作。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重庆的一些小学也闻风而动,纷纷在《重庆日报》上推出本地版的“革命”儿歌。这之中,刊于该报1975年2月15日的某厂子弟校学生创作的儿歌专版,以及继此之后,刊登于1976年2月23日该报副刊的由同一学校学生所创作的“评《水浒》批宋江”的儿歌专栏最为典型。
在上述小学生的儿歌专版专栏中,有下列儿歌充分表现了说教和概念化特色。例如:
你打铁,我打铁,/毛铁炼成好钢铁,/做盏红灯送大姐,/大姐做工干劲大,/晚上灯下学马列。
柳下跖,真勇敢,/不怕地来不怕天,/坚决打倒奴隶主,/彻底砸烂铁锁链。
小铅笔,金光闪,/我写儿歌来参战,/批臭林贼“天才论”,/不信“天才”信实践。
除刊发上述儿歌外,报社还同时配发以该校名义所写的一篇评论:《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开展革命儿歌活动》。该文强调学校不仅组织师生“编写了革命儿歌2200多首,重要的是通过编写革命儿歌,进一步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和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有效地抵制了坏儿歌的腐蚀和毒害,在全校出现了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新局面。”
该文章虽然强调儿歌写作的意义重大,但实际却掩盖了“四人帮”一伙企图用儿歌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险恶用心。因被“四人帮”愚弄而把重庆的儿歌创作引入歧途,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二、儿童生活故事
“文革”中重庆的儿童生活故事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全市主流媒体的《重庆日报》副刊版面上,有时仍能寻到它的踪迹。比如在1973年5月31日的该报副刊上,就载有《向阳苗》(朱明珍)一文。该文叙写重庆某厂子弟校一学生在厂区拾到一只名贵手表,但她不受这贵重物品诱惑,多方寻找,终于将手表交回失主手中。这篇褒奖拾金不昧的生活故事,虽因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而降低了文学因素,但其语言朴素,叙写逼真,体现了“文革”文学普遍强调的教育性主题,因而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继《向阳苗》之后,同年11月11日的该报文学副刊上还发表了儿童小说《庆生和蛮蛮》(华放)。这近4000字的短篇,写从小生活在柳湾村的两兄弟――13岁的农中学生庆生与8岁小学生蛮蛮清晨去村南坡地割猪草,发现地主罗大鼻子在偷生产队的包谷,于是哥哥当机立断留下监视动静,同时派弟弟绕道回村向支书大伯报告敌情。由此演出了一场红卫兵智擒顽敌的阶级斗争戏。
该小说虽借山村景物描写烘托气氛和塑造人物性格,但作为小说的基本故事构架,并未超越60年代重庆合川少先队员刘文学因勇斗地主分子而光荣牺牲的英雄事迹。况且,刘文学事迹被媒体披露后,上海儿童文学作家贺宜为此专门创作并出版了题为《刘文学》的长篇传记体小说。如今《庆生和蛮蛮》的作者在主干情节的设计上重蹈他人覆辙,活脱脱克隆了一个并不让人感到新鲜的新闻事件,这就在客观上暴露了“文革”重庆儿童文学的作者缺乏真实儿童生活,仅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空洞理念出发进行先验的创作,其艺术生命肯定是十分短暂的。“文革”时期的重庆儿童文学,并不是毫无作为,但它留给人们的教训,应该好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