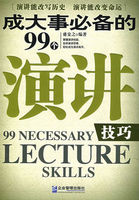6月里的一天,他又跟父亲去打猎。他们来到小橡树丛里打鹌鹑。突然,宝贝儿又伏在地上做出扑咬的姿态,父亲来不及打枪就叫了一声:“抓住它!”猛地见宝贝儿的鼻子前面跳出一只鹌鹑,飞走了。可是它飞得很奇怪,翻着跟头,转来转去,又落在地上,像是受了伤或是翅膀坏了。宝贝儿拼命去追它,把它捕住了。如果鹌鹑好好地飞,宝贝儿就不会这样去追它,也不可能把它追上。
父亲从宝贝儿嘴里接过鹌鹑,把它肚子朝天放在掌心上。
“怎么回事?”罗斯宾问,“这只鹌鹑本来就是受伤的吗?”
“不,没有,”父亲说,“它根本就没有伤。准是附近有它的一窝小鹌鹑,它为了把狗引开,才装做受了伤的样子……可是,它装得过头了,结果真的被宝贝儿逮住了。”
罗斯宾连忙靠近鹌鹑看了看。它耷拉着小脑袋,一动不动,只用一只褐色的小眼睛从旁边看着他。它仿佛是在说:“为什么我应该死呢?我是在尽我的责任,想把狗引开,保全我那些孩子的生命啊!”
这时候罗斯宾多么可怜它,多么希望它能够活下来啊。可是,它全身哆嗦,伸直了腿,闭上小眼睛死了。
罗斯宾哭着问父亲:“现在怎么办,还有谁来喂它的孩子?”“别担心,”父亲定睛看了看他说,“还有雄鹌鹑,孩子们的爸爸……不,等一等,你看,宝贝儿又想去扑咬什么猎物了!那不正是鹌鹑的巢吗?”
真的,在距离宝贝儿的鼻子两尺远的草丛里,紧紧地并排蹲着四只小鹌鹑,全都伸长了脖子在不住地哆嗦着。
“快把宝贝儿叫回来啊!”罗斯宾拼命地叫。
谢谢父亲,他很快把宝贝儿叫回来了……
这一天,他们虽然让鹌鹑的四个孩子保全了生命,但罗斯宾心里还是很难过。于是,他就从父亲手里要来了这只死鹌鹑,给它在巢边做了一个小小的鸟坟,埋葬了它。
说来奇怪,从此罗斯宾再也不想有自己的猎枪了……
珍贵的遗产
本性和教育有某些方面相似:教育很可以改变一个人,但这样做它就创造了一种第二本性。
——德谟克利特
琳达永远不会忘记1965年夏季,她的母亲当时只有36岁,却突然病故。当天下午,一位警官来到了她家,问爸爸是否同意献出母亲的主动脉瓣膜和角膜,这使她非常惊惧。他们想解剖母亲的遗体,切取她的部分器官。想到这儿,琳达难过极了,哭着跑进了房间。
那时,琳达才14岁。她爱妈妈,她不理解人们要妈妈的器官干什么。然而,最使她不能理解的是爸爸的回答,他对警官说:“我同意。”
琳达对着父亲大叫道:“我不许他们那样干,妈妈是完完整整地来到这个世上的,现在也应当让她完完整整地离去。”
父亲用双臂将她搂在怀里,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琳达,你要知道,一个人死后,所能奉献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她的器官。我和你妈妈认为,如果我们死后所奉献的器官能改善别人的生存状况,那么我们就没有白死。我和你妈妈,早就决定了做器官捐献者。”
父亲的话,对琳达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后来,琳达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1980年,父亲患了严重的肺气肿,生活不便,于是搬来同她住在一起。这以后的6年里,她和父亲谈论过许多有关生与死的话题。
父亲对琳达说,他想死后把他所有完好的内脏都捐献出来,尤其是他的眼睛,他说:“一个人所能给予别人的莫过于光明。没有什么能比赐给一个孩子光明,让他们也能像琳达的女儿望迪那样画马更美好了。”
望迪最喜欢画马,她的画一次次获奖。父亲又说:“想一想,当那些盲人的父母看到孩子重见光明,并且像望迪一样画画时,他们的父母该是多么的自豪。再想想,如果你看到,在我死后我的眼睛能使一个失明的孩子重见光明,并且还能像望迪一样画画,那你一定也会感到自豪的。”
琳达把父亲的话告诉了望迪,她显得异常激动,紧紧地拥抱着她的外公。她只有14岁,和琳达当年首次接受捐赠器官教育时同龄。然而她们两代人的思想境界却是多么的不同啊。
1986年4月11日,父亲去世了。她们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眼睛捐献出来。3天后,望迪对琳达说:“妈妈,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帮助外公实现了他的心愿。”
琳达有些不理解地问:“这使你感到骄傲?”
望迪说:“是的,妈妈。你能想象得出看不见万物的滋味吗?等我死后,我也要像外公那样把眼睛捐献出来。”
从那时起,琳达开始真正懂得了,父亲捐献出的不仅仅是他的眼睛,还有女儿那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骄傲。
琳达紧紧地抱住了女儿,她思绪万千。然而,琳达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她竟然又一次在捐赠器官书上签了字。望迪在路边骑马时,被一辆卡车夺去了生命。她签了字,这时女儿稚气而又认真的话语在她的耳边响起,“你能想象得出看不见万物的滋味吗?”
望迪死后三个星期,琳达收到了一封俄勒冈州眼库的来信:
亲爱的里弗先生及夫人:
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移植手术非常成功。一位盲人又重见了光明。他们就是对你们的女儿活着的纪念,您的女儿在九泉之下也一定能分享到这份快乐。
琳达想,今后在她生活的国家里,如果那个接受过眼睛移植的人有了一个新的爱好,爱马和画马的话,那就是女儿仍在不停地画着。
父亲这样教育我
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出一个会不停地提出问题的人。
——克瑞顿
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在周末带着费曼去山上玩,在漫步丛林时给他讲很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也有别的孩子跟着他的父亲去山上玩,当孩子们聚在一起时,一个小朋友问费曼:“你瞧见那只鸟儿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费曼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只黑颈鸫呀!你爸爸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
“看见那只鸟儿了吗?”爸爸说,“那是只斯氏鸣禽。”(费曼猜想他其实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意大利人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现在,你只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可还是一点也不了解它。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于是费曼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他说:“瞧,那鸟儿是在啄它的羽毛。可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大概是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要把羽毛梳理整齐。”费曼说。
可结果发现,鸟儿们在结束飞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
“因为有虱子。”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蜡,蜡又有蟥来吃,蟥吃了不消化,就拉出粘粘的像糖一样的东西,于是细菌就在这上面生长。”
“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现在,费曼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蟥。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又有一次,他摘了一片树叶,他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C形的坏死的地方。“这是一只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蛆,蛆以吃树叶为生。它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它边吃边长大,吃的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变成了蛹,又变成了蝇,从树叶上飞走,它又会飞到另一片树叶上去产卵。”
同上面他所举的例子一样,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则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
一天,费曼在玩马车玩具,车卡里有一个小球。他说:“爸,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
“因为运动的物质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这是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费曼一个名词。父亲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进行兴趣盎然的讨论,没有任何压力,这使费曼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费曼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致好心家长的信
心平气和的、认真的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才是家庭教导技术应有的外在表现,而不应当是专横、愤怒、叫喊、央告、恳求。
——马卡连柯
英国的诺曼·文森特·皮尔曾写过一篇文章《致好心家长的信》,文中强调了在青年人初次踏入社会时,追求独立的重要性,内容颇值得借鉴:
“亲爱的弗雷德:
你在信中央求我办的事当然并不麻烦。你的儿子约翰不大喜欢目前的工作,你认为他干别的活会更顺心一些。你知道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的朋友,问我是否能给他通个电话,为你的孩子美言几句。
我对此的最初反应也许正是你所期待的。为什么不是呢?这是非常自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欣然从命!我拿起话筒。突然,一个奇怪的念头闪过脑际。千事万事,我却想起一只猫。呆呆的,我放下了电话。
上周星期五,我看到了街道上的一个场面。人们放下手里的活,津津有味地往窗外观望。从对面的房子里,主妇的一只波斯猫跑了出来,爬上几层楼高的壁架。猫沿着壁架一直走到尽头,它在那儿被吓呆了。它既不能向前走,又不想退回来,只是坐在那儿,漂亮可爱又孤立无援哀怜地叫着。主人又是乞求,又是哄骗,又是发誓。后来,她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员架上梯子,总算把猫抱了下来。
弗雷德,这就是我看过你的信后想起来的事情。我也想到了约翰。我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住在我家对面;后来他跟我的孩子一起长大,最后大学毕了业。
我还记得每当他要做出决定或想实现一个计划时,你总是免不了插手。还记得他打算造木屋那件事吗?你认为太危险,叫他不要干;当他考虑从大学退出一年,自己在社会上闯一闯的时候,你觉得那样做不明智,于是他也就作罢了;还有那个几乎与他成婚的女孩,你认为他还太年轻也最终放弃了。现在他干的工作是你帮他找的,对不对?
你求我帮一帮约翰,那好,我想我只有对你讲一讲这些话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别再干涉你儿子的生活了。让他长大,做个男子汉,而不是一个6英尺高、被无形的围裙带拴住的依赖者。你知道为什么那只波斯猫在壁架上被吓瘫了吗?因为它一直被关在屋里被庇护起来,以致遇到连最普通的猫也能应付的情况时,竟束手无策了。
这个世纪到处都是像约翰这样的孩子:举止文雅、脾气和顺,心地善良,但同时也踌躇犹豫、举棋不定以及胆小软弱。我在布道中见过这样的人。他有时迷惑不解,愤恨不满;有时又麻木不仁,冷漠懒散。是谁把他们弄成这个样子的呢?是父母,是充满爱心、情真意切、小心谨慎的父母,是那些以十分无知地指导和保护孩子为开始,最终却由于过分庇护而扼杀了他们的父母。
我常听人们抱怨说,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难找到领袖了,即那些富有创造性、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和勇敢无畏的男子和女子。也许我们不想得到这些,因为受到过分庇护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发展这些品质。如果每一个困难都为他们解决了,他们为什么要发展呢?”
永远和你在一起
对孩子来说,父母的慈善的价值在于它比任何别的情感都更加可靠和值得信赖。
——罗素
“妈妈”,从女儿莫拉异乎寻常的颤动的声音中,阿曼达立即知道:这不是每周例行的来自学院的平安电话。“妈妈,我们宿舍的一位朋友想自杀,她要吞毒药丸。我们迫使她扔了毒药,陪她坐了一整夜。妈妈,她从前就自杀过。” “你的朋友得到了医生的照顾吗?”阿曼达问道。她极力用平和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没有,现在还好。另外,她也不想让我们张扬这件事”。
“你们这些年轻人还不能自己处理这类问题。”阿曼达告诫道,“你的朋友需要专职人员的帮助;把发生的事情报告你们的宿舍指导员,她知道该怎么办。”对于一个18岁的姑娘,这是多么重的担子啊。
“我感到害怕,妈妈,你想象不出我是多么害怕。” “其实,莫拉,我也害怕,为你朋友,也为你。”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握着她的手,倾听她的诉说。”此时,阿曼达想,如果自己能握着莫拉的手,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