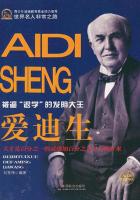在浏览了一下市场行情之后,墨菲·布隆代尔开始工作。不过时不时地他也会隔着透明玻璃望一眼右边挨着的那个女同事。他的眼光很复杂。这是个平凡无味,但是人很聪明的女人,名字叫凯特·米罗。
她比所有人都更严谨。每天早上她都是七点整进办公室,一直待到最后熄灯为止。她甚至会半夜起来,只是为了不错过亚洲一些股市的开盘信息。
一般来说,对于她的这些情况,墨菲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似乎是出于命运的嘲弄——他自己也对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感到好笑——他们有相同的年龄,都来自美国,曾经并肩一起做相同的工作有几个月。更重要的是,他们又都是单身,工作能力都被公司里的同事竖大拇指。
他俩甚至已经“被结婚“了十次。
凯特·米罗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简单、幽默的大女孩。有时候她会陪他去咖啡厅。在那里会跟他聊《泰晤士金融报》上的内容,还有跟老伦敦有关的闲话。然后是似乎约定俗成的大笑,再然后就是离开。那些笑声墨菲其实并不喜欢,甚至有点反感,但是很明显它们会让别人开心。
同事里面像马克斯·巴尼那样,对墨菲多少还有点爱心的人看到他每天早上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而旁边就是他那纯洁无瑕,但是又有点怪异的“未婚妻“,都开始严肃地担心总有一天他会被“套上龙套“。
“小心,我的老朋友!“马克斯·巴尼已经警告过他,“这个淫荡的斯达汉诺夫主义者迟早会吃掉你!“
但是绝对不可能——每次墨菲都反驳。然而他又不能在入门大厅处贴一张大告示或者海报来宣告自己与凯特之间的清白。
“今年夏天你做点什么?“她在电梯里问他。
“什么想法都还没有呢。还在等公司的情况。“他有点戒备地回答说。
咖啡厅已经站满了人。 从十点钟开始,咖啡机旁边的非正式会议参加者就会越来越多。咖啡机似乎变成了一个力比多离心机,旁边的大笑声、吵闹声、手机的铃声此起彼伏,组合在一起,以至于让墨菲差点没有听到自己手机的来电铃声。
“是我,“一个有点不确定的嗓音,“你在听我说话吗?“
“在听,“他回答了一声,同时给凯特·米罗做手势,示意她可以走了。
然后他立刻转身走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并关上门,收拾了一张桌子,将咖啡放在上面。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电话里已经没有了声音。
“娜拉,娜拉,你还在吗?“他重复了几遍。那声音让人觉得他是在黑暗中摸索一样。
“我在。“她终于开口,似乎他这样很好玩。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昨天给你寄了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我知道我还欠你很多,但是暂时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刚找到了工作。“
“可是,你什么都不欠我啊。“他激动地说。这时他注意到那两个外汇经济师——麦克和彼得——正在窗户外盯着他看,活像两只蹩脚的狐狸。
“我不相信你跟我打电话只是为了这个。“他继续说着,同时转过身,背对着那两个人。
“也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她温柔地补充了一句,“有时候,看着时间就这么过去,我就会想有一天回到伦敦的时候,你或许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会再也找不到你,因为那时你已经忘了我。“
他真想如此回答她:人不可能什么都拥有,不能既在场,又不在场,既忠实又不忠实。不管怎样,她不能同时给他自由——就像她离开的时候那样,而又想让他继续做她的囚徒。
但是他做不到。他很害怕她会亲口说出让他重获自由,那样他会继续痛苦下去。
“实际上,你知道吗?“她对他说,“我觉得没有我你过得很好,你不过试图证明自己过得不好而已。“
“可是,我什么都不想证明。“墨菲说完这句话就看到了安德森小姐。她挺着胸,鼻孔有点颤动地突然出现在这个房间里。
“十分钟后开会。“她喊了一句,然后把门砰地关上了。
“娜拉,待会儿再打给我。“他在电话里小声说。但是她应该已经挂上了电话——听筒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声音。
当其他人都急匆匆地走向会议室的时候,他又待了一会儿喝咖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从帘子的缝隙中看着窗外步伐轻盈的女路人,还有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的汽车——他突然感到一阵怀旧的思绪涌上心头。那种思绪是如此的强烈。
像他这样的年纪,人们都已经有了应有的爱情。墨菲有点自怜。但是他不想继续自己怜悯自己,准备享受生活,并逃掉这次有关投机基金的会议。然而当他看到安德森小姐双手交叉在胸前,正在监督所有人的时候,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于是他坐到了会议室的最后面,最靠近出口的位置。当出口处没有人,所有人都被保罗维茨那沙哑的嗓音腻烦得恹恹欲睡的时候,他悄悄打开后门,蹑手蹑脚地轻轻走了出去,直奔电梯。
走到大街上后,他在齐普赛街附近逗留了一会儿。风有点大,吹得他有点摇摇晃晃。但是他仰望着天空,看着浮云飘过,心中竟然也飘飘然起来,似乎双脚就要脱离地面。
过了一会儿,由于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他随心所欲地跟着人群走向了摩尔门和芜田的圣玛丽大教堂,决定先去教堂待一会儿。
走进阴暗凉爽的教堂之后,相信圣徒和圣徒们神力的墨菲不禁在长凳上做了一个长长的祷告,然后还做了忏悔。但是忏悔的过程中,思绪情不自禁地就已经飘向了远方。那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思绪,自然是跟娜拉有关。他不清楚娜拉那目的不明的举动,也难以厘清她与自己模糊复杂的关系。
最后,当他还在想这些事的时候,还沉浸在回忆与思考中的时候,尽管路上无休止的喧闹声还是从侧门传进来,但是内心逐渐找到了静寂。
也许他来找的正是这种内心的静寂。
外面,退休的老人,无所事事的人,被社会抛弃的人……所有被经济奇迹淘汰的人都坐在花园的椅子上晒太阳,就像是一群徘徊在食物链最低端的动物。
看到他们,墨菲再次想到将来他会过上一种“模范“生活,没有名字、黯淡无光的生活,整日为别人的事业忠实地忙碌着——即使有世上最好的打算,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然后,当他听到教堂的钟敲了三下的时候,一想到此时娜拉正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他甚至因孤独而突然颤抖起来。
于是他站起来准备去老伦敦,好返回办公室——他可以找借口说是跟医生见面。路过神殿前面的一个小店的时候,他要了一份三明治。这时,视野中左面的角落处出现了一只又脏又丑的老狗。
狗很瘦,还瞎了一只眼,像是两只狗合二为一——头是德国猎犬,身子却是卷毛狗。它瑟瑟缩缩地走向墨菲,似乎是为自己的丑陋而感到难为情。
然而墨菲绝不是在找狗,而这条狗更不可能是他愿意找的狗。
出于怜悯的冲动,他还是给了这条狗一块自己的三明治。但是他非常希望它会立即消失,就像变魔术一样突然不见。
它三两口吃完了三明治。
然而,那只心怀感激的狗却一直在他的膝盖前安静地抬着头,直到最后墨菲被它的坚持所感动,将它那因感动而摇晃的身躯抱在怀中。他一点都不顾忌旁边人的目光,还开始很严肃地对着狗的耳朵说话,告诉它他现在必须回去工作,所以它只能另找一个好心人。
“你懂了吗?“他最后说。
那只狗还是犹豫不决,用那双已经患了白内障的眼一直盯着墨菲。而墨菲在抱住它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自己比刚才老了许多。
他越是抱着它,就越感到自己更老。
似乎由于偶然的好感,他与狗合二为一了,现在将跟它一起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