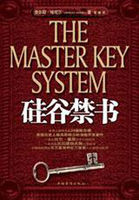莫高窟的夜是这样宁静。静得让人听到大地发出的呻吟。对于饱受喧嚣的文化人来说,能够拥有这样静谧的夜晚,也许是最大的享受了,可以思索,可以幻想,可以伤感,可以怀忧,而我们的敦煌学家樊锦诗,最欣赏最喜爱的,莫过于千佛洞的夜晚了。多少年来,她总是在夜色中独步,在星光下徘徊,思考着,遐想着,任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望着那一排排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洞窟,她会想:天苍苍,野茫茫,我们的祖先从洪荒时代走来了!什么时候他们创造了文字?对了,一定是从描画开始的,是从在岩壁上描画开始的。于是有了文字,有了艺术,有了敦煌金碧辉煌、栩栩如生的佛像和壁画。我们的祖先多么伟大!
夜深了,铁马风铃在清风中传来悦耳的音响。世世代代,在这块佛教艺术的圣地上,走过多少人啊!来了又去了,一串串脚印踏出了…条贯通欧亚大陆的著名古道……铃声叮咚,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迎面而来。真想随他们一道去罗马帝国,去古代波斯,去威震四方的长安城……消逝了,这一切都消逝了。但是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有责任在留有他们生活画面的敦煌艺术中,将历史的足迹考证出来,奉献给世界文明啊!——这是多么重大而又荣耀的职责!
樊锦诗全身心地投人了敦煌学的考证和研究。多年来成就显著,硕果累累。她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莫高窟290窟的佛传故事画》、《莫髙窟北朝洞窟本生困缘故事画补考》、《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和南朝影响》、《敦煌壁画的保护》、《丝绸古道话沧桑》、《莫高窟唐前期石窟的洞窟形制及题材布局》、《莫高窟发现的丝织物及其他》等重要著作和论文。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一书,运用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第一次明确划分了莫高窟早期北凉、北魏中期、北魏晚期至西魏前期、西魏后期和北周四个不同的石窟艺术发展阶段,解开了多年来早期石窟分期中的疑团,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樊锦降确认了一批北魏以前的石窟遗存,断代为北凉洞窟。同时又区分了北周和隋代之间的界限,推断出一批建德时期的北周石窟。在《莫高窟隋代分期》一文中,又将时间虽短但造窟频繁的隋代莫高窟分为三期,脉络清晰地阐述厂这个承上启下朝代的重要变化过程,填补了隋代莫髙窟研究的空白。她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敦煌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颗耀眼的新星。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将她的论著翻译成日文,作为教材,进行讲授。1989年世界第33届国际东方学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樊锦诗应邀作了关于《敦煌石窟的现状与未来》的专题讲演。日本著名的石窟考古专家长光敏雄先生专程赴敦煌和樊锦時切磋学问。
我参观了这位“敦煌女儿”的居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座书库!是书的海洋,书的世界。大大小小的书架上摆满了几乎所有关于敦煌的学术著作和画册,就连沙发和茶几上也放满了各种书刊。为了写作方便,还特意在床边加了块木板,专门用来放置书刊资料。睡觉时想起了什么,翻起身来就查就写。而院里分来的苹果和葡萄,却被漫不经心地放置在水泥地面上,有些已经溃烂了。看来我们的主人是很少想起这些水果的。樊锦诗告诉我:“对我们这些又要搞学术研究,又要做业务领导的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休息这一说。每天5点准时起床,一直忙到夜里12点。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这一点我在采访期间有着亲身的体会。整整一个月时间里,她没有能够坐下来和我认真地谈一谈。我总是找不到她。这个娇小单薄的女人,像一只风轮似的在敦煌的石窟区、展览区、生活区、工作区轮流转动着,行踪快得像闪电。看见了她的身影,撵到跟前,又不见了。那时她正忙着纪念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50周年的筹备工作。届时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由口本帮助建造的敦煌文物陈列馆举行开馆典礼,日本国前首相竹下登先生及一批国会议员将前来参加揭幕仪式。二是要召开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除了组织学者们撰写研究文章外,她自己也要拿出学术论文。‘天深夜,因为天气闷热睡不着,我到陈列馆附近去溜达。这是一座极其宏伟的现代化陈列馆’除了许多仿制的洞窟和壁画彩塑之外,还要展出近100年来的图片和实物,工作量非常大,而时间又十分紧迫。听到里面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便走了进去。原来樊锦诗正领着一帮姑娘在布置展览。我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一个姑娘偷偷地告诉我,昨天早晨,她迟到了一会儿,便不好意思地走到樊锦诗跟前,说:“樊院长,你的这件衣服真漂亮。”樊锦诗说:“你先别管我漂亮不漂亮!请你回答,你为什么迟到了10分钟?”看看樊锦诗到另一头去整理图片,姑娘用不解的目光望着我:“你说说,她那么瘦小的一个身体,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儿?”
这句似乎不经意的问话,使我永远地记住了“敦煌女儿”那双瘦削的肩膀。那是双在大漠瀚海中负重远行的肩膀,那是民族的肩膀。
然而家庭的闲难却长久地闲扰着这位闰际知名的敦焯学家樊锦诗。丈夫长期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生活,身体越来越差,经常感冒发髙烧。而孩子们又长期得不到母亲的温暖,吃不好穿不好,性格也变得孤僻起来。作为一个母亲,她常常有一种负罪感。但是她又太爱敦煌了,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使她最为心碎的是那年春节,因为段文杰院长病重住院,研究院的工作离不开,她未能赶回武汉和家人团聚。除夕那天,她收到小儿子字体稚嫩的来信。
亲爱的妈妈:
你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了,我都快不认识你了!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邻居家的孩子们都穿了新衣服,在院子里放炮了。可是我们家呢?爸爸刚从考古工地上回来,累得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和哥哥还吃的是方便面,墙上落满了灰,被子都没有人拆洗一下。这还像个过年的样子吗?妈妈,赶快回来吧,回来和我们一起过年。
你的儿子晓民
樊锦诗读着孩子的信,泪如雨下。她似乎听到了一只待哺的羔羊咩咩哀叫的声音。除夕夜到了,居民区里到处响着鞭炮声。举目四望,家家灯火辉煌,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眼前出现自己家里冰锅冷灶,孩子们瑟缩着身子,围在患病丈夫床前的情景,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她的心头。砝码开始向武汉倾斜了。那一夜她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为了排解忧伤,她钻进洞子里散心。这已经是多年的习惯了,每当遇上不顺心的事,她总是到石窟里去观看壁画和佛像,使心里的疙瘩在艺术欣赏之中得到化解。这一次她看的是《宋国夫人出行图》——樊锦诗最为赞赏的敦煌壁画之一。宋国夫人是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的妻子。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占据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大片土地,斩断了唐王朝的西部臂膀。唐大中二年,敦煌人张议潮揭竿而起,发动了包括汉、粟特、回鹘、吐谷浑在内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推翻了统治河西地区达80年之久的吐蕃贵族,并一举收复了包括甘肃兰州、岷县、临夏,新疆哈密、青海贵德、乐都在内的中闰西部10州,使这些地方重归大唐版图。在这次波澜壮阔的起义中,张议潮的夫人广平宋氏表现得十分出色。在将军帐里,她帮助丈夫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两军对阵中,她手持花枪,打马直刺敌酋。战争结束后,张议潮被唐王朝委任为河西11州节度使,宋氏则被敕封为宋国夫人。壁画上的《宋国夫人出行图》,场面宏大,气势磅礴。那位协助丈夫收复失地,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重大贡献的宋国夫人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意气风发,她的身边是众多前呼后拥的车骑随从和边走边舞的男女伎乐。一位古代的敦煌巾帼英雄跃然壁上,呼之欲出。
一千多年前的封建时代,敦煌尚且有如此杰出的妇女,坚定地守护着这块神圣的土地,为什么现在我们却徘徊犹豫,动摇不定了?看着看着,她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心中的砝码又向敦煌倾斜了。
多少年来,樊锦诗和丈夫的关系一直是这样:每次回家,开头的一些日子,夫妻俩总是亲亲热热、恩恩爱爱,家庭里呈现出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慢慢的,“蜜月”结束了,两位髙级知识分子开始争吵。而“战争”往往是彭金章挑起的:
“锦诗,你还是冋来吧!”
“说过多少次了,敦煌不放我。”
“到底是敦燒不放你,还是你离不开敦煌?”
“两种原因都有。每次回武汉,敦煌人都眼巴巴地瞅着我,我不能伤他们的心。”
“你就愿意伤我们的心?”
“我谁的心都不愿意伤!”
“实际上你已经伤了我和孩子们了!”
“那你为什么不到敦煌去?”
“人家都是孔雀东南飞。总不能为了你一个,我们父子三人一齐飞向沙漠呀!”
不过吵归吵,最后还是和和气气,相敬如宾了一那样短暂的探亲假,加倍珍惜都来不及呢!
有一次,彭金章使出了杀手锏。他召开了家庭会议,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究竟是樊锦诗调回武汉,还是他上敦煌。同意妈妈回武汉的举右手,同意爸爸到敦煌的举左手。孩子们看看妈妈,又看看爸爸,都不举手。彭金章带着悲音说:“予民,晓民,你们都大了。我们一家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不管是妈妈调武汉,还是我调敦煌,你们都要有个态度。我保证尊重大家的意见。你们愿意让我上敦煌,我立马打起背包和妈妈一起走!”
予民看了妈妈一眼,怯生生地举起了右手。晓民躲闪着妈妈的目光,也举起了右手。看看孩子们都表了态,彭金章慢慢地举起了右手。三比一:樊锦诗回武汉!
泪珠在眼眶里滚动着,樊锦诗咬着嘴唇,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大家的意见。
她向丈夫和孩子们许诺:一个月以后听消息。她准备一回敦煌就找组织谈话,提出调动工作的事。谁知回到敦煌,刚进办公室,段文杰院长就来找她了:“锦诗,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坐飞机到北京去!”“什么事?”
“我送你去机场。咱们在车上边走边说。”
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关系到敦煌百年大计的非常紧迫的事情。1986年金秋时节,我国外交部邀请各国驻华大使参观敦煌莫髙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同代表泰勒先生也应邀前往。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女士陪同参观,向众人详细介绍了莫高窟的过去和现在,介绍了它的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同时也提到了石窟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外国专家的合作。泰勒先生回京后,拟定了一个合作保护莫髙窟的计划,和各国使馆联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很快回复:美国有个盖蒂基金会,是专门从事重要文物保护的,曾经参加过埃及爱弗塔林古墓葬壁画的保护以及狮身人面像的修复。他们治沙是采用设置尼龙防沙网的办法。盖蒂基金会保护研究所所长刘易斯:“蒙雷尔先生现在北京。敦煌研究院如有兴趣,请即派人来京接洽。”
临上飞机时,段文杰院长捤着樊锦诗的手说:“锦诗,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樊锦诗重重地点了点头。她知道这句话的分量。长期以来,莫髙窟的防沙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曾经和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合作,采用“堵”的办法,在石窟顶修筑了一条长达1088米的防沙墙,企图把风沙堵住,结果没有成功。后来又采用“清”的办法,就是让风把沙子吹下来,再用人工将它清除掉。这种办法虽然效果较好,但要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是研究院的一个沉重负担。他们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理想的防沙办法。
樊锦诗飞到北京,来不及洗把脸,换件衣服,便匆匆赶往历史博物馆。刘易斯蒙雷尔先生正陪国家文物局领导在那里观看他带来的修复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录像片。樊锦诗悄悄走了进去,找一个角落坐下,对身边的同志说:“不要告诉蒙雷尔先生我来了。”她觉得自己未加梳洗便来会见外国朋友,似乎有些不礼貌。这时刘易斯,蒙雷尔已经转过头来,大声询问:“敦煌研究院的樊女士来了没有?”
国家文物局的同志把她介绍给了蒙雷尔。直率的美国人对风尘仆仆的樊锦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天,在国家文物局的安排下,樊锦诗和刘易斯·蒙雷尔正式会谈。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美方同意提供全套防沙设施。工程由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二方合作进行,樊锦诗为总负责人。
她和沙漠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设计了一个“之”字形的防沙网设置方案。为了检验这个方案是否符合实际,她和设计人员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冒着8级大风,到风速最大、风力最强、飞沙最多的风口去做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将“之”字形方案修改成为“仝”形方案。这是一个科学的方案:“人”字的头顶,是一望无际的鸣沙山:“二”字的身后,是莫高窟的窟口崖面。这个防沙图案,既可以阻挡多方来沙,把沙子阻挡在尼龙网前面;又可以导沙,使沙子沿着尼龙网设置的走向,从窟口崖面两侧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