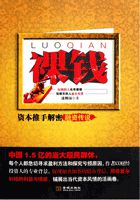惜别阳光
在婚床鲜花堆簇的枕下
躺着漆黑的棺木
——蓝蓝《枕下》
士薇恍恍惚惚地醒来,微微地睁开眼睛,她看到了一束光。那光刺得她的眼疼,她的眼睛又闭上了。但隔着眼皮她依然能感受到那光的存在,那光把她眼前的世界照的一片混沌,她仿佛置身在深深的水底。阳光照在水面上,穿透了上面的水层,绿绿的水就变成了一片明亮的混沌,仿佛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是太阳,强烈的阳光使得她睁不开眼。我这是在哪儿呢?我现在在床上躺着,一切都摇摇晃晃,是红霞吗?李红霞,你不要老在上面晃,你穿衣服慢点好不好?你看谁像你,张婉像你吗?尹素兰像你吗?牛文丽像你吗?人家起床都是悄悄的,就你这样在上面摇摇晃晃的,你看一个寝室里谁像你!是啊,没有人像她,可是谁像我呢?我总是这样懒懒地睡觉,操场里踏踏的脚步声传过来,都跑早操了,这个觉我是睡不好了,讨厌的脚步声!那脚步声要是换上沙沙的雨水有多好,沙沙的春雨,清新的空气,下雨的日子真是睡觉的好日子,懒懒地躲在被窝里,听着春风在室外呼呼地摇着草黄色的树叶,哗——哗——永远没个停,可是不中,妈妈会过来掂耳朵的,妈妈已经做好了早饭,你闻哪小薇,空气中都布满了你喜欢的香气,妈,谁要吃那么多油,我不要吗,你看我这身子已经发胖了。胖什么胖,像你这样的身材再胖一些才好,快起来,起来吃饭了!你看外面的春雨,把草坪都洗涤得清清爽爽,快起来呀,你看呀那多像一幅画。这是一幅画吗?是一幅画,庆伟,你看哪,你看那幅画,你讨厌呀庆伟,你看这幅画,这绿色的草坪,灿烂的阳光,红色的遮阳伞。庆伟,你觉不觉得这个女孩子有些夸张?多好的阳光呀,可是她为什么要拿上一把伞呢?是给谁看呢?庆伟你说她是拿给谁看呢?是为那个男人吗?他是个男孩子吗?不是,他不是个男孩子,他是个男人,一个很英俊的男人,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就像你,是不是?庆伟呀,我的命,我爱你,我们结婚吧,结婚,庆伟,我们结婚!我们会得到幸福,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对,还有萌萌。萌萌,萌萌,叫阿姨看看,你这讨厌的孩子,为什么不让我看呢,再过些日子我就是你的妈妈了,我们从此就要在一块生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要跑啊,小心滑倒!庆伟,你看这孩子,我们结了婚怎么办,她这样仇恨我,把她送回她母亲那儿去吧?你不什么不?你喜欢她我能不喜欢她?问题是她不喜欢我。会慢慢好起来吗?庆伟,会好起来吗?她总是这样任性,你说萌萌同我一样任性吗?庆伟,我看到了混混沌沌的光亮,这是阳光吗?不是不是,这是值班室里的灯光。值班室里的灯光照着我和你,庆伟,我看不够你,我们在一块有说不完的话儿,是吗?庆伟,你听外面多静呀,夜已经深了,拉灭这讨厌的灯吧。庆伟,我爱你,拥抱我吧,庆伟,哎呀,我的天哪,你的手……你的嘴呢?快点含住乳头呀……我的天哪,你的手……轻点,轻点……我受不了了,哥哥,我的亲哥哥……我爱你……呀,我的亲哥哥,我们结婚吧,哥哥!月光从窗子里透进来,照着你和我,我们躺在那儿,静静的夜呀……哥哥,你闻到什么气味了吗?是来苏水的气味吗?不是不是,是难闻的臊尿气,哪来的臊尿气呢?我这是在哪儿呢?士薇静静地躺在那里,在寂静里她听到了有一对整齐的脚步声从冷漠的走廊里传过来。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是一个有雾的日子,浓重的雾气几乎包裹住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这一天年轻的法警琼六点起床,她草草地吃了一点东西,就骑车穿过市区的一些街道,她要在七点钟之前赶到地处郊外的监狱里去。赵琼骑车走在雾气濛濛的路上,心情有些紧张。作为一名法警,多年以来她对执行枪决任务有一种隐隐的渴望。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她在过去的时光里没有一次持枪押着罪犯乘车飞速驶向刑场的经历,那些有关枪决死囚犯的情景大多来自间接的讲述,那些讲述一次次地使她的那种愿望不停地增长。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一个女性,一个做了母亲的女性为什么会对那种血淋淋的场景产生兴趣呢?或者说她为什么会对死亡那么的感兴趣呢?她一次次地想象着那些死囚犯倒在她枪口下的情景,那些死者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射击的对象,而授予她这种射击权利的是她背后的巨大的国家机器。由于某些犯罪事实,法律裁定了某个人的命运。而她,今天就要成为某个人的命运的执行者。在夜间,她似乎有些兴奋的睡不着觉,她反复地在心里念叨着那个女人的名字:孙士薇,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在这之前赵琼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一面,她只是在一些相关的材料里看到过这个几乎同她一样年轻的女人的一些情况。那个名叫孙士薇的女人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她毕业于省内一所有名的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琼所供职的这座北方小城的一所条件最好的医院里。赵琼睡不着的时候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想象过士薇的模样。琼想,二十四岁的一个未婚女子,那应该是一个很漂亮让人嫉妒的女人,一个妇产科医生,说不准在过去的某一天她还在那所医院里见过她。她穿着一件白大褂,戴着一幅金丝眼镜,走路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长得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像一朵在绿色的荷塘里沐浴着阳光的芳荷。琼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不由得替那个名叫士薇的女人有些惋惜。她躺在被窝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在明天,她就要亲手从水塘里摘下那朵水灵灵的荷花吗?那荷花会在阳光下一点一点地枯萎吗?她似乎又感到自己有些残忍,她后悔自己不该来承担这次任务,可是女囚犯需要女法警来押送,她不知道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是法律,还是道德?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被两个男人押着难道就不合乎道德了吗?这真无从说起。难道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吗?可她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呢?她没有弄明白是不是那种带有刺激性的渴望使她默认了上级对这次任务的决定,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那个名叫孙士薇的女孩子,不,女人……赵琼在心里重复了一下这个词:女人。她为什么要称那个和她一样大小年龄的女人为女孩呢?就她们两个的职业来讲,那个名叫士薇的女人就更女性化一些,一个戴着金丝眼镜身上散发着某种特殊气味的女人总使人感到亲切,而我呢?琼一边骑车行走在渐渐接近监狱的道路上一边这样想,人们在看到我时想的更多的是法律、监狱和死亡,人们似乎感受不到我微笑的面容,这真是不公平。那个和我一样岁数的女人白天像天使一般目中无人地出入医院的门诊和病房,而夜间却和她喜欢的男人偷情,她在偷情!她躺在一个她喜欢的男人的怀抱里如醉如痴,这个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女人!她凭什么这样?或许就是这些难以言明的原因使赵琼才接受了这个特殊的任务。本来她可以对自己的上司说,我不能,我家里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但是她没有说,那个时候她抬起头来,目光穿过一片撒满阳光的空间,她有些茫然地想,我要亲眼看着那个漂亮的女人那个浪漫的女人是怎样在我的面前倒下去的!那个女人就像一朵充满芳香的荷花,可是那朵荷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灿烂的阳光里被我轻而易举地摘采下来。
那个有着浓重雾气的早晨,一个名叫赵琼的法警七点种准时赶到了地处郊外的监狱,在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琼见到了她的几个同事,周瑛、祁德芳,还有那个高个子杨晨,她们和众多的面目严肃的男同事一样全副武装,七点一刻,他们那个中等身材的上司出现在会议室里。他面对法警寻视了一下说,开始吧!
赵琼和杨晨按照事先的计划逐渐接近那个名叫士薇的死囚犯。她们一同走过一道戒备森严的小铁门,穿过一片飘荡着雾气的开阔地,而后又走过一道铁门,进入了一条被灯光照亮的长长的走廊,她们的皮鞋一下一下地敲击着脚下坚硬的地面,最后她们在九号门前停住了。她们在绿色的门前和看守对视了一下,那个看守晃了一下手中的钥匙,而后插入了锁孔。在铁门推开的时候,琼闻到了一股尿臊气扑鼻而来。接着她看到了那个坐在地铺上的女人,尽管戴着墨镜,但在琼的感觉里那个女人仍面色苍白。
士薇听到一种沉重的声音朝她压过来,那种声音一下又一下地击打在她的心上,她一个机灵坐起来,那种声音在门外消失了,接着她听到了钥匙插进锁孔里的声音。随着房门的推开涌进了大量的光亮,她看到两个戴墨镜的女法警出现在她的视线里。两个女人,她们为什么要戴上墨镜呢?她们不想让我看到她们的眼睛吗?眼睛,我什么样的眼睛没有见过?老人的眼睛,孩子的眼睛,男人的眼睛,女人的眼睛,眼睛的结构真正太复杂了,在五官里,结构最复杂表情最丰富的就数眼睛了。可是她们为什么要戴上墨镜呢?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呀,可是她们为什么要堵上自己的眼睛呢?这时她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叫孙士薇吗?
是的,我叫孙士薇。可是我不愿意理睬你们,你们明明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还要问呢?这就是验明证身吗?是的,她们是在验明证身!我就是那个犯了死罪的孙士薇。我犯了死罪了吗?我真的像做梦一样,多少日子以来我都在这梦境里,在别人的目光下在这间空气污浊的屋子里生活,我最讨厌这种气味,每天上班后都是我去推开那扇宽大的窗子,让新鲜的空气和阳光涌进来,可是我已经有很多日子没有闻到新鲜的空气没有看到阳光了!我已经没有享受新鲜空气和阳光的权力了吗?没有,庆伟,你还记得那片绿色的草坪和那把红色的遮阳伞了吗?庆伟,我的爱,你在哪?她们随手递给我的是什么呢?是一根细细的用绳子做成的腰带吗?是的,是腰带,她们怕我自杀,她们在这之前收走了我的腰带,你们这些蠢货,我就不想死,我要是想死,你们能拦得住吗?我要想自杀,那不是有墙壁吗?我用头朝那墙壁撞过去你们谁能拦得住呢?我用我的牙齿咬断我的静脉你们谁又知道呢?你们忘记了我是个医生,不,我不想死,我还有我的庆伟。哥哥,你在哪儿?我现在只想看你一眼,哥哥,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