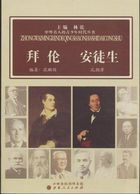一个星期后,谢工重新出现。一问,原来是病了。知道谢工也是单身,儿女都在国外。那次,谢工病后初愈,唱得特别卖力,场外掌声阵阵。
下了场,徐姨说:“你今天唱得真好。”
谢工笑了:“野唱,野唱啊。”
徐姨就在含光门里住,路近,唱罢了,便邀谢工到家里喝茶。谢工去了一次,又去了一次,再去了数次。
半年后,徐姨与谢工的婚礼在环城公园里举行,还邀请了市里的秦腔名演员参加。票友众多,场面热烈。电视台记者闻讯赶来,采访俩位“新人”,请他们谈谈退休后的生活还有恋爱经过等等。
记者问:“谁是你们的介绍人?”
他们齐声说:“是秦腔。”
记者拍摄了现场表演,佩服说:“俩老唱得真好。”
他们笑了:“野唱,野唱。”
2008年3月1日
巴教授与流浪狗
巴教授明年就80岁了,但他一点儿也不显老,精气神很足。
从年轻时他就养成了习惯,凡要上讲台,必然头发齐整,领带端正,衣装规范,皮鞋铮亮。他讲课条理清晰,表达准确,声音宏亮,手势有力,口齿和仪态十分谐调。尽管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可走下讲台是人生的自然规律。
虽然不上讲台了,但生活的面容并没改变,既就下楼散步,上街买菜,依然是着装整齐,一丝不苟。尤其是逛书店,还会往衣领上洒几滴香水,嘴中嚼个口香糖,他觉得这样才配得上书香。
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内心深处,巴教授是日渐孤独苍老了。几年前,老伴去世,让他感到失去了某种隐隐地依靠。虽然争吵了矛盾了一辈子,有时气不过还离家出走,可他这只老船,终是摆不脱天定的港湾。如果没有固定的码头,船就会漂泊下去而无法静止下来。可人有时是需要安静地躺在那儿好好休息,想想心事的,这由老伴打理的房屋,就是他的码头他的憩床。老伴走了后,儿子几次要接他去深圳与儿孙同住。可他不去,嫌南方空气潮湿,他离不开北方古城的干爽,离不开师大优雅的环境,说到底,是离不开身边早已熟稔透顶几乎伸手可触的气息。
一个星期天中午,巴教授去小区外的湘菜馆用餐,进门点点头,老板娘就知道一切按老规矩办。片刻,一盘萝卜干炒腊肉、一盘青菜老豆腐、还有一碗蒸米饭就端上来了。巴教授吃饭时,不小心将一片香浓的腊肉掉在了地上,有一只小狗扑上来收获了它,有意思的是,小狗嚼吞了腊肉,竟身子一抬,两个前爪抱在一起给他行了个作揖礼。严肃的巴教授被逗笑了,于是又挟了一块腊肉抛给小狗,狗儿又回了一个作揖礼。老板娘上来说,这是个流浪狗,教授你别理它。接着把小狗撵出了餐馆。
巴教授用完餐,返回小区,爬上5楼他的寓所。对于老人来说,5楼有点高,又没电梯,但巴教授不愿换地方,5楼视线好空气好,并且爬楼梯也是锻炼身体嘛。
掏出钥匙,拧开房门,突然脚下一个东西窜进房里去了。进房仔细一看,原来正是那流浪狗。他用棍子去赶那小狗,小东西在他面前翻了个筋斗,然后又抱起前爪向他行礼,并且眼眶里有亮汪汪的东西在闪动。巴教授心中一下软了,看来这家伙与自已有缘啊。于是叹口气说,那你留下,名字就叫缘缘吧。
教授收留了小狗,他们相处的很好。教授买了好吃的,总要给缘缘留一份,并且还为缘缘在角落里搞了个舒适的小床,还不定期的为缘缘洗澡,送缘缘去宠物医院检查身体。缘缘总是有恩必谢,行礼是经常性的动作了。另外,教授晚上洗脚,缘缘便为他叼来拖鞋;教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缘缘便爬上来卧在他的怀里;教授看书睡着了忘记关灯,缘缘便跳上来拉动台灯的开关线绳儿。
傍晚,常常在饭后,他们一起去散步。教授在前边身板儿挺直地走着,缘缘在后边摇着尾巴跟随,成为师大小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熟人见了他们打招呼,同时把手中吃的东西分一点儿给缘缘,缘缘总是及时作揖回礼,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这天早上,教授起床洗漱后突然觉得不舒服,一头倒在沙发上,痉孪着说不出话儿来。缘缘上前来拉扯着教授的裤脚,窜上窜下叫个不停,但没作用,教授慢慢地沉静下去。缘缘爬在厨房的阳台上狂叫起来,可仍没引起过往行人的注意。这时,缘缘跃起,一头从高高的5楼上跳了下去,它的身躯在空中划了一个长长的弧线,然后坠落,停止。
有人看见了死狗,还认出它是教授的缘缘,就上楼来敲门,没有反应,觉出了有事,便叫来保安撬开房门,发现了窒息的老教授。可是送到医院已经太迟,急性脑血栓夺去了他善良的生命。
儿子从深圳赶回来安葬老父亲,同时听闻了缘缘的故事。他把缘缘和教授埋在了一起,他想,这可能也是老人的意愿。缘缘是为父亲献身的,就让它的灵魂和体温,继续陪伴着上了天堂的老父亲吧。
2007,8,27日于朱雀门
声音的方向
长街上,有歌声飘来,抬头一看,对面走来一对卖唱的青年男女。那男的身材清瘦单薄,是个瞎子,他一只手扶着木推车,另一只手举着话筒,竟自歌唱着。他的声音有点儿沙哑,但苍劲动听,曲调也比较悠扬,带着民歌的风味。他身边的女子个头稍低,显得丰满健康,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扑闪扑闪,似会说话。她推着木制小推车,车板上放着扩音机和喇叭。车子缓缓前行,带着瞎子,带着歌声,带着一种祈望而来。
我将一张纸币放在车板上,轻声问:“你们从哪儿来?”
他们停下脚步。
姑娘望着我闪了一下眼睛,用手去摸了一下男子的手背。
男子意会了,微笑地说:“谢谢,好人。”
从男子的口音中,我听出了他们的大概来处。
“你们好像是陕南人吧?”我说。
男子回答:“是啊,我们是白河人。先生去过白河吗?”
白河是陕南的一个小县份,位于秦楚交界地带,那儿民风淳厚,人比较聪明精巧。过去在陕南工作时,我曾多次去这个县里采风。
“去过去过,我也是陕南人。”我忙说。
男子握住我的手,摇着:“遇到老乡了,谢谢。”
“你们出来谋生活,不容易啊。”我说着,掏出口袋里装得所有的也不太多的钱,全部放在他们的车板上。
姑娘的眼睛潮了,但还是没说话。
她用手掌又使劲儿拍拍男子的手背。
男子说:“我爱人是哑巴,她说她很感谢你。”
我顿时楞住了。
原来这是两个残疾人。男子看不见光明,由女人给他带路;女人发不出声音,由男子代她说话。他们这样相互补充着,相互帮助着,把生活进行下去。
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很简单甚至很艰辛,但很恩爱。
从这对浪迹江湖的平民身上,我们感受到一种夫妻的奥义和人间的温情。
小车向前推去,歌声向前飘去。
我留恋地打量着声音的方向。
2007,6,27日午后于西安朱雀门
古都札记
秦镇凉皮
一碗凉皮,从秦朝吃到如今。
吃的是香味,吃的是风格,吃的是乡土民俗。
产凉皮的秦渡镇,座落在长安县与户县交界处的沣河西岸。沣河滩道很宽,但水流却又浑又小。能叫秦渡,想当年应该是颇有气势的吧。
历史有时无法想像,那年代没有摄影,不可能真实的再现实况。而绘画和文字又太抽象,融入文人的情绪很多。所以,大秦第一渡的风采难觅其踪。
只有凉皮流传下来。
现在,凉皮在全国已经很普及,尤其受女孩子的欢迎。
当今是个盗版盛行的时代。要吃祖传的、最正宗的凉皮,还得去秦渡镇。
凉皮诞生在这儿。这儿的凉皮是御封的贡品。
秦始皇统一天下,关中平原藏龙卧虎。秦渡镇周围,有稻田10数万亩,是王朝的粮仓之一。可是有一年,久旱无雨,田地干枯,打下来的稻谷尽是稗秕,碾出的少量的大米质量极差,没法向朝廷纳贡。这时,有个叫李十二的农民,心生一计,他将打下的大米用水拌湿碾成米粉,放在锅笼里蒸熟,然后切成条状,起名为大米面皮子,权做贡粮,送往咸阳。秦始皇吃了面皮子以后,觉得味美可口,龙颜大悦,便钦命秦渡镇的面皮子为贡物,今后可以只献面皮不纳大米。
李十二成了当地名人,在他的带领下,面皮子越做越精。后来,李十二在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去世,家家蒸面皮记念。凉皮从此流传下来,成了长安的名食。
秦镇凉皮的特点是:筋、薄、细、穰,看上去色白如雪,光润似脂;嚼起来柔韧绵厚,口感尚佳。再配以嫩菠菜、黄豆芽,调以辣椒红油、香醋等等,回味无穷。容易入口充饥,强筋健骨,可能还有美容的作用吧?要不,为什么女孩子喜食?我认识的漂亮的美眉,几乎都对凉皮感兴趣。
今天在秦渡镇的路旁小店里,看到几个女士大吃凉皮,不知是兴奋、是天热、还是味辣?她们脸蛋红红的,嘴唇红红的,精神也是红红的。我突然觉得,吃凉皮的女士们,是不用再化妆的。
听说每天都有很多人从西安开车过来买凉皮,有些一买就是几十斤。还有人下班后晚上过来吃凉皮,再饮以户县出产的黄酒,其乐融融。
有美食,有美酒,有美人,入夜的梦可能也是美的吧。
甜水井
甜水井是一条街名,在西安古城内的西南角。过去,全城只有这一个地方的水是甜的。以含光门内的马路为界,马路的东边,冰窖巷呀,报恩寺街呀的水都是苦的,怪不怪,自然界有很多事情真是说不清。解放前,西门里有一口大井,4个辘轳,8个大桶,不停地打水,供全西安的商号使用。周围的居民,自然也享福了。就是那些过路人,也要绕进街旁的四合院里去讨水喝呢。
现在,家家户户都用的是自来水,统一供水,味道一样,那些四合院也拆了。为拆那边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旧宅,曾闹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最终高楼还是林立了。我小时候,曾跟随父母在甜水井旁的夏家什字街住过几年,于砖铺的巷道上游戏,于深大的老院子里捉迷藏,如今砖失院没,面目全非。
但我与甜水井的缘份,似乎割舍不断,几十年后,又住到离它不远的四府街上,并且常去甜水井街附近买东西。那儿有个比较大的菜市场,品种齐全、时鲜价廉;那儿有个超市,各色成品食物任你挑选;那儿有西安城里最大的天主教堂;那儿还有茶行咖啡、干洗店、杂货铺、幼儿园、修车配锁等等,总之,家常生活的味儿浓厚,又随意方便。在现代化的都市里,这点特别使人留恋。
有一度,甜水井那边显得混杂脏乱,地面不平坦,房屋不整齐,道路拥挤难行,后来,政府下决心治理西南城角,将洼地平了,烂屋推了,重新规划一番。一条大道宽直通畅,几个小区优雅整洁,角上还搞了个公园,面积虽然不大,可小巧安静。最值得称道的是,西南城角出现了一个“无极古玩城”,一溜儿二、三层高的仿古建筑,楼前那些拴马桩、石狮子、石门墩、旧木车,散发着旷古幽象。每到周末,各家斋号陈列的,地面小摊铺展的,全是文物古赏,几千年的民间遗存,都在这儿出现了。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摆在汉唐的长安城里,它就具有了真实的意味。
古玩城大门的北手,有一家“青都里”炭烧店,一层是烧烤饭庄,二层是茶秀酒巴,地下一层是棋牌室,装修典雅个性,偏重于日韩料理。楼侧还有个很宽敞的平台,摆数排木质桌椅。夏夜,坐在平台上品茶饮酒,闲谈历史,一旁是安稳高耸的古城墙,一旁是树木葱郁的小公园,惬意极了。
那冲茶的水,标明来自“甜水井”,也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你现在就坐在真实的古老的甜水井边上。
贝币的故事
最近,古城西安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博物馆:钱币博物馆。站在馆内的橱窗前,望着那些精致的展品,我怦然心动。
中国货币的最早形式,是一种指甲盖儿大小般的贝壳。那是远古时期,人类的肌体很发达,不需穿衣服、不需化妆,最多只用一片树叶或兽皮挂在腰间遮住隐秘处。并且人的大脑思维也才刚刚启动,众人皆为兄弟姐妹,有好吃的东西大家共同分享,有洪水猛兽大家共同抵抗,有壮丽的景观大家共同欣赏。没有地界的划分,没有人与人的争斗,没有心与心的算计。
后来有一个聪明爱美的人,在海边的沙滩上,拣到一枚非常精致漂亮的小贝壳,它有指甲盖儿那么大,呈现着天然纯净的象牙白色,隐约可以看见暗藏在深处的血丝儿。它一面是浑圆隆起的丘状,另一面则椭圆扁平,中间裂开一条长缝,两边排列着整齐精细的齿态。凑在耳边一听,缝隙中还发出细微的声音,似乎在传送什么幽曲。这爱美的人就用一根树皮绳儿拴起来挂在胸前。没想到,这小贝壳引起了不少人的喜爱,你瞧瞧,我摸摸,成了小宠物。这人脸上有了光彩,心中有了骄傲,他又去海边上捡了不少类形相似的小贝壳,挂满了胸前,十分地炫耀。同时,占有欲使他心态发生了变化,谁想要小贝壳,就得帮我找吃的喝的、帮我干活、在我面前讨好。
慢慢地,到了奴隶社会,小贝壳就演变成货币。奴隶主占有人力,自然也占有了货币。他们用小贝壳交换女人、交换食物、交换自己想要而又没有的东西。
再后来,人们可能觉得小贝壳作为货币太自然、太随意、太唾手可得,就用手工制造起石币、布币、铁币、铜币、金币、纸币来。美丽的小贝壳被抛弃了,女性生殖崇拜的时代也过去了,人工、暴力、男权越来越强大。
端详着这些小贝壳,我沉思良久。它们本来是大自然的产物,是纯洁的精灵,是美的象征,只因人为的原因,它们变成了货币,染上了血迹,印上了风尘,注入了邪恶。我仿佛听到一缕缕如泣如诉般的幽怨之音,正从贝壳中飘荡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