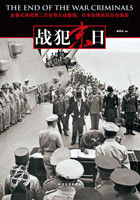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母女俩经历的不幸生活。故事可能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因为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程师偷丁块猪肉,导致丈夫出走。这使母女俩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亲的所有愿望就是找到出走变心的史夫。这是绝望的“寻找”,其结果星女儿也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也终于死去。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尖锐地器露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和他们在这种困境中的无助。巾同社会是一个落差极大的丰十会,在沿海地区和发达的大城市,改革开放无疑带来社会相当大的进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相应的飞跃。最先进的后工业化社会的那些现象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比比皆是,传媒、广告业、时裴、各种演艺和体育竞赛、电脑、网络……等等,但中国的基层社会依然贫穷落后,从现在的各种传媒中不难看到鬼子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
鬼子并不单纯描述苦难生活的一些事实,这篇小说蕴含的实际主题,在于揭示经济变动时期家庭所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对于一些弱势群体来说,经济变动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另部分人却更加贫穷,他们别无选择。这位母亲可能属于这一类型。她虽然身为工程师,也属于科技知识分子一类,但她的恩想观念却依然停留在半个世纪前。我们也许会责备她自作自受,但作为生活的弱者,她们无能为力。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弱者,没有那么多自强不息的人。她们的生活只能靠外部较好的环境来建立安全感,一处在困境中则只能任凭生活走向崩溃的结局。父亲当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坏蛋,被当今商业社会激发起的欲望所俘获,个人的欲望满足完全淹没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最不幸的也许还是寒露。这个未成年的中学生由于家庭的破碎而走向个人生活的绝境,她四处寻找父亲不过是她生活无望的一个象征,就是找回了父亲,她又能如何呢,所有不该经受的苦难,她都经历了。
这部小说把一个家庭的生活推到苦难的极端,母亲的故事有如“为奴隶的母亲”的现代演绎,打瞌睡的女孩寒露的故事则更其于《卖火柴的小女孩》。毫无疑问,这篇小说对苦难生活的书写催人泪下,对底层人民不幸的反映在当今小说中也是绝无仅有。鬼子小说的叙事凝练而冷峻,直接切人生活的实质,他的叙事儿乎是偏执地向前推进,固执地走向极端。鬼子的小说也有值得追问的地方。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相肖纯粹,干净利落,鬼子的那种凝练冷峻的叙事风格表现得非常充分。这篇小说还接近电影的表现手法,鬼子不贝是把握情绪和情感的单纯方面,同时在把一种情感氛围推向极致。他处理那些结构的转折也很像电影,例如“偷肉”、“父亲出走”、“失身”等等关键性的情节转换,带动了人物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显示出情节本身的内在生长力。那些情境的处理也很具有电影的氛围,如在宾馆寻找父亲,那种表现情感的现场情境气氛就极有表现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鬼子的小说情节过于硬性,它们像是一个符合目的性的必然过程。鬼子只关心苦难和不幸,他过分专注于他要达到的目的,以至于人物所经受的苦难像是叙述的强加,叙述总是不顾一切地层层加码,直到把苦难和不幸推到极端。这使他的人物总是有单面化和类型化的特点,好人就是好,坏人就绝顶的坏,不幸就是绝对的不幸,苦难就必然陷入绝境。当然,书写苦难本身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没有彻底没有绝对就没有苦难,对于某一部小说这样写也许是必要的,我只是担忧鬼子如何处理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和相对性。当然,鬼子可以以他的方式去表现他所理解的生活,去演奏他的苦难奏鸣曲。
阅读李冯的小说永远是一件漫不经心的事,他可能恰恰和鬼子处在某种状态的两极。李冯的小说总是在轻松自如中给人以明晰的快感,那些快乐和智慧的趣味是随时随地从段落和句子中看似不经意地讲述的人和事中透露出来的。近二年李冯的小说风格变化不大,写作的主题也还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方而是当下的边缘文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对近现代历史的演绎。《一周半》描写两个外省青年人进京,试用以自由撰稿人的方式在北京谋求发展,但他们很快就被生活的现实性所压垮,面对经济的困窘和个人的生理欲望无能为力。李冯写出了一部分“藏匿于高校的异类”不安分的生活幻想,一种在商业主义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幼稚病。概括李冯小说的主题和内容并不难,但李冯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对那些生活过程的灵巧而机智的表达。随意出现的生活场景,偶然涌现的想象,李冯的小说就像是不经意打开的一个生活侧面,你随时随地部可眺望到那么一些情趣。鬼子的小说像一堵硬梆梆的墙,他总是去发掘墙下的生活死角;东西的小说有如指给你看那些翻墙者,他总是不怀好意地去拉扯那些翻墙者的腿部关节,致使他们的姿态怪异可笑;而李冯则是在墙上随意乱画,或是打开一扇窗户,他自己就跳将过去。李冯的小说如同可写性文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开始,也不知道他要在哪里结束;开始和结束都是暂时的,也不重要,它们不过是短暂的停顿。李冯的那个叙述人不断参与到叙事中,他的感觉细致,稍稍超出常人,既在情理之中,x在意料之补。那些平常的生活细节,其实常常越出生活的正常轨迹。
例如这种描写:
我在车站广场的人群中寻找老吴,最后在一个角落的一堆民工中找到了他。老吴出发前新剃了个头,所以发青的脑门在人堆里很显眼。他怀里抱着一只纸箱,看到了我,他端着纸箱站起来,似乎是想把它交给我。我试图接过来,它分量非常沉,但老吴实际上却抱紧它不放。“老吴,你到了多久?”栽问。“三个小时。”他说。“三个小时?你就一直坐在这儿?”我吓了一跳。“火车开得比你想象的快。”老吴憨憨地笑笑,显得有些精神恍惚。
这种描写看上去平实,但每一句似乎都暗含着对生活进行重新组装的可能。老吴的光头形象,他抱着一个纸箱的姿态,他精神恍惚的神情……等等,仔细辨析,小难发现在李冯小说叙述的平实外表下,掩盖着对生活重新改写的那种力量。如果说鬼子是重拳出击,东西是怪招频出,李冯则是四两拨千斤。鬼子是拿一副鞭子拷打生活,东西是拿一把锥于扎生活,李冯则是手持一支狗尾巴草,给生活搔痒。有时候,这种搔痒搔到要害处也会叫人受不了。李冯的那些漫不经心的嘲弄,使生活在变质的那个瞬间突然变得陌生,突然使人涌溢出挚爱生活和生命的感受。老吴拍打电脑,老吴冲动地买下电话,老吴渴望和那个光头女孩约会,暮色中二男二女在胡同里有目的又没有目的地行走……这些非常平实的日常生活细节,隐藏着复杂的心理,涌动着难以压制的生活渴望。什么是有质感的生活?有时候是要把人、把生命压垮的那种东西(如鬼子笔下的有些场景)。有时候就是那些突然涌溢出来的愿望。这篇小说在李冯的小说中并不能算是突出的和典型的,但却是耐人寻味的那种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冯的小说在趣味和风格方面有点类似汪曾棋,尽管他们所写的生活性质完全不同,但那种格调,那种韵味,那种情致,有某些异曲同工之意。当然,汪曾棋的那种老到和意境是李冯所不具有的,但李冯有另一种东西。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经验,有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在本质方面是不可比的,但作为汉语写作,他们又有某种共通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在平淡之处,显示隽永和不可磨灭的痕迹。
李冯的写作确实有向着俏皮方面发展的趋势,这不仅在他的一些关于现实的小说中可以见出(例如这里提到的《一周半》以及《在天上》等等),在一些改写近现代历史的故事中也越发明显。他在1999年发表的《谭嗣同》就完全像是历史讽刺小说。对历史的改写和颠覆一直是李冯的业余爱好。之所以说是业余爱好,因为李冯写这些小说像是从不刻意要去完成。他的那篇关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小说,同样是在解构历史。历史英雄和名人,都在他的改写中变成一个普通人。对历史进行解魅,从中获取叙述的快乐,这是李冯的特殊才情。
李冯最近写的《在天上》和《七短章》都是不错的作品,依然是那样轻松从容地剖析生活。对于李冯来说,生活在哪里变质,哪里就有快乐出现。生活的那些动人之处,恰在于那些变形错位的环节。那个一心想换系的铁梅和“我”(《在天上》),那个在安美美安莉莉之间周旋的杜马,这些人物都有些神经兮兮,但他们总是渴望越轨。也许是一种生活的勇气,也许是当代生活在最本质方面出了毛病,李冯总是躲在幕后,不置可否。他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并自己作出判断。在广西的三剑客中,李冯也许是最不负责任的一个,这与最负责任的鬼子形成强烈的反差。
鬼子决不含糊地告诉你,什么是生活中该诅咒的东西;东西也明白地告诉你什么是生活中应该撕开来看看的东西;李冯则只告诉你什么是有趣的可以随便看看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这=个作家同出于广西,他们的风格其实大相径庭,但他们的存在给当代文坛输入了活力,他们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在当代中国文学最薄弱的那些环节起到了支撑的作用。鬼子多少有些暴力化的写作倾向,给软弱的文学写作注入一种强硬的力量;东西的诡秘使当代小说叙述的呆板裂开一道缝隙;而李冯的灵巧也使笨重的文学获得暂时的轻松。但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就无可挑剔,也不必挑剔。事实上,我总是觉得,鬼子的写作过于沉重,东西过于诡诈,李冯则过于轻巧……
这当然都是他们的特点,我不知道如果他们之间稍微靠拢一点,是否会抹去各自的特点?或者各自就走向个人的极端,独树一帜也未尝不可?我无法得出结论,但我拭目以待。
1999年12月21日于北京望京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