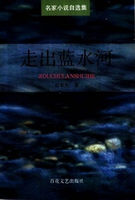那天晚上大舅是喝了一些酒的,说白了都是酒惹的祸。一般出这种男女之间的事,男人都要用酒来做掩护,有喝多的没喝多的,都会适时不适时地使用酒这个道具。也确实,酒能乱性嘛,喝多了酒的人干出什么事来都能让大家觉得是应该的,甚至是可以谅解的。但大舅没有,他坚决不用酒做借口。在当时的状况下,这帮垦荒者在寂寞的时候还能使自己麻木的就只有酒了。大舅却不善于饮酒,偶尔喝几口也只是应付一下。那天晚上他喝得多些,因为是团里来了人,由营里的教导员陪着来四连检查垦荒进度的,大舅是连长,想不喝都不行,上级领导来了,他这个下属单位的领导不表示一下热烈欢迎的态度是说不过去的。除非他对上级有意见。表示诚意的东西当然就是酒了。他一边痛苦地陪着喝酒,一边又不停地喝了大量的水,他想着让水冲淡酒在肠胃里的浓度,他肚子可能会舒服许多的。
那天晚上大舅喝了酒后回来睡到半夜,被尿憋醒,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胡乱抓了几件衣服,就走出自家的帐篷,跌跌撞撞地到礼堂外面去撒了一泡尿,又摸着黑乎乎的夜色回来后,一头钻进了帐篷倒头就睡。可能是起来撒了这一泡尿让他醒了一些酒,感觉又很舒畅的缘故,他大脑竟有些兴奋起来。大舅却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几次,都难入梦,这在平时是不可能的,干一天的活,累个半死,如果不是喝了酒,天黑了就睡,一睡就到天大亮了醒来,一点都不含糊。大舅这天大半夜里睡不着,他就一边闭着眼尽量睡着,一边又追究起睡不着的原因,追究到最后,终于想起来,除了一部分是喝了酒的原因外,还有就是当天晚上还没有和妻子做那件事。
年轻的夫妻大都喜好夫妻之间的那点事,何况新婚不久又身强体壮的舅舅,每天干完体力活,回到大礼堂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就坚持做夫妻之间的事,这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确实也是一件既消磨时间又能娱乐的最好方式了。大舅在半夜里找寻到了睡不着的原因,心里开始躁动,就更加睡不着,越睡不着那种念头就越发收拾不住。大舅正处在精力旺盛的时期,有了这种冲动是压不下去的,而大舅认为,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必要去压制住自己强烈的欲望。于是他就放开了自己欲念的闸门,伸手脱了身边这个人的裤子,轻车熟路进进出出很快地做了一番。再怎么说,大舅毕竟是喝多了酒的人,这个时候把酒又拿出来当道具不是帮大舅解脱什么,事实是他的大脑兴奋起来也只是相对于他醉酒时而言,神智却还是有些迷糊的。如果大舅不是还有些迷糊,他做那事时也就不会感觉不到有什么异常了。也许这时大家都猜到了,大舅进错了帐篷,然后又错把齐贤当成妻子做了一回爱。当时的居住情况不充许人们在做夫妻之事时有太大的动静,所以大舅做得很沉默,像例事一般,做完了也就累了,倒头睡着了。
后来人们都议论说,这里面定有阴谋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齐贤当时还是个姑娘,一个男人闯进她的帐篷,并且把她睡了,她都一声不吭,这是何道理?还不是看这个男个是她梦想中的男人,才故意不吭气,宁愿委身于他的。还有,就是大舅的前妻杜丽,她和大舅离婚不久,就被营教导员娶了做老婆。从教导员那猴急的样子,也可以看出是他在大舅的风流事上做了手脚,因为那天晚上是他陪着团里的工作组,和大舅一起喝的酒。但大舅偏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也怪不到别人的头上,是他喝多了水起来撒尿又钻错了帐篷的,也是他主动去脱人家齐贤的裤子,何况这种事做的都是自愿的,又不是别人强迫他去做,怎么能怪人家呢。
不管怎么说,第二天早上的事实证明,大舅这后半夜做的这一次爱注定了他的婚姻得改变方向了。
我后来对大舅说过,为什么你不用喝了酒进错了帐篷来解释这件事呢。大舅却像个蓄谋已久的色棍似地说,你现在的这个舅母也很不错的,身体强壮,无病无灾,虽说不像个女人,却能经得起折腾,还能生这么多的孩子,我早就看上她了!
谁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是真是假,有可能他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或者是这一场婚姻的失意才这么说的吧。
但大舅的选择也是最明智的,和杜丽离婚,再和齐贤结婚,这件轰动全团的风流事件也就算是有了个圆满的结果。如果大舅不这样做,他这个支边青年的典型恐怕得成为强奸妇女的罪人,谁要是背上这么一个罪名,一辈子也就完了。但大舅是多么聪明,他不找任何理由,而是选择了和齐贤结婚,了结了这件看起来很难解决的大事。当然,因为这件事,大舅的连长也当不成了,就是不算强奸妇女,也闹了个离婚。离婚的人一般被认为作风不正。作风不正的人怎么能再当连长,这样的人是服不了众的。
大舅一下子成了一个普通的农工,心高气傲的大舅倒没有因为和杜丽离婚,失去了一个漂亮的妻子而显得多么难过,其实掳去他的连长职务,是大舅心理上最最不能接受的现实,他下巴上一夜之间就胡子拉茬了,一下子就没有以前的洒脱风度了。或许大舅的初衷就是为了要保住连长职务,才心甘情愿地承担着对齐贤的责任,和刚结婚不久又女人味十足的漂亮妻子离婚,而娶了这个像男人一样没有一丝女人味的女人。但他娶了这个女人却还是没有保住连长的职务,这个后果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打击也是相当大。失算的他也只能面对这样的现实了。所以,后来的大舅一下子就变了,变得和以前绝然不同,不那么假了,很现实地活着。他自从学校出来,支边到新疆,一直好像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身份中似的,做着一个离他本人很远的另外一个人,根本没有实实在在的生活过,包括他和杜丽的结合到离婚,都像演戏似的,没有一点踏实感。只有这一切结束了,他才从梦中醒了过来,回到了真实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