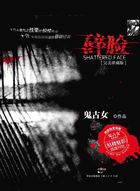跟李素梅赌气出来,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不像在市里,家里不行去办公室,办公室不行去会议室,总是有个落脚的地方,现在好了,只有那间屋属于他们两口子的自由空间,其他地方都不方便去,除非你去守灵。侯大川真是烦心透了。老父亲突然病故就够让他心痛的了,前后四天一家人又连续吵了两架,把侯大刚打得跟花脸刘备一样,侯大银的媳妇还传出来绯闻,你说这叫什么事!侯大川就像无头的苍蝇,往西走几步拐弯向南,往南走几步又拐弯向东,反正是哪里没有人就往哪里去。人说喜怒哀乐不行于色,那得需要城府,需要涵养,也得是在人场里。现在侯大川是自己溜达,那就可以尽情地表现了,忧愁、愤怒、伤心、无奈等都刻在了脸上。
他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的掠影里,叼着烟卷,两手掐腰,目视远方。这个时候他最希望能下点儿雨,不是暴雨,是小雨,滴滴都能打在他身上,凉在他心里,再来点儿不大的风,吹吹他那涨热的脸,吹吹他那懵懵的头,可就是没有,太阳尽管西斜了,仍还是那么毒辣,像火一样烤着他的身躯。
忽然一辆轿车停在了他身边,一位小伙子下了车,冲他道:“表大爷,你怎么一个人站这里,叫我好找。”侯大川认识他,是大舅的孙子自己的表侄,一脸狐疑地问道:“金贵,你怎么来了?”“俺爷爷在车里,他找你有事商量,你上车吧。”
侯大川拉开车门进去坐到了后座上,跟身边的薛健康打招呼道:“大舅,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嘛?”薛健康没有看他,两眼瞅着前面,面无表情地说道:“我看到处都是人,咱们还是在车里说话吧。”“您不去家里喝茶了?”“还是不去吧,我也不渴。再说,眼多嘴杂,还是这里方便。”“您有什么事?”“也没有大事。这不是俺姐夫老了嘛,我听说明天就要火化。”“是呀,那天晚上咱不是一块商量的吗?”“能不能改改?”“怎么改?”“改成土葬,不用火化了。”“这怎么行!现在都是火化。”“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农村凡是当官的、有钱的都是给老人土葬了,只有平白老百姓还是火化。”“怎么会是这样?”“这不是很正常嘛。”“怎么能是正常,这是搞特权。”“你说的不对。当官干什么,如果一点儿特权没有,那还当什么官!”“别人怎么做官我管不着,反正我不能做,影响太坏了。”“乖乖,我看你是当官当憨了,有什么影响?这里离你们徐淮二百多里路,能影响到你哪里!话又说回来,也不会有影响的,事情很简单……”“怎么简单?”“你不知道,我跟你说说。咱还是下车说吧,老坐在车里闷得慌,也窝憋得难受……金贵,你上车。”
坐在树凉影歇着的金贵起身拍拍屁股走过来上了车,问道:“爷爷,什么事?”薛健康道:“你把车开离村里远些。”“咱到前面那个河岔行不?”“行。只要离村远些没有人看见就行。”
金贵发动车,开着车去了河岔。
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侯大川先下了车,然后扶着薛健康下来。他们找个比较干净的树荫,跟金贵要了两张旧报纸坐下来说话。
薛健康接过侯大川递过来的香烟,凑火点上,深深抽了一口,说道:“现在当官的当老板的脑子可好使了,想的办法真是天衣无缝。”侯大川虽然没有改变主意的念头,但还是想听听详细情况,说道:“您具体说说。”薛健康道:“表面看也是去火葬场火化的,其实做了手脚。比方说俺村的葛万才死了,他儿子葛有理就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把他给土葬了。具体是这样的,葛有理先买了一副松木棺材,个是最大的,人工根本抬不动,这就是他的借口。先把棺材拉到坟地,放进墓穴里,四周搭个棚,派自己人看着,然后演的跟真的似的,自己找辆去除了座的面包车拉着葛万才的尸体去火化了,也吹喇叭放炮,围观的老百姓肯定相信了,其实他们是兵分两路,这一路开着面包车绕了几十里路一大圈,拐回来去了坟地,把葛万才下葬埋了,那一路去了火葬场,买了个骨灰盒空着抱了回来……”侯大川没有明白,问道:“那一路怎么去的火葬场?”薛健康继续道:“事先安排一辆面包车在外面路口等着了。这边安葬完了,那边也买好骨灰盒回来了,然后还是在那个路口见面接头。”侯大川道:“我明白了,葛有理抱着骨灰盒坐原来的车回来,后一辆车开走了。”薛健康笑道:“说你当官当憨了,其实你不憨,聪明着呢。”“那后来呢?”“后来是这样。丧事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只是故意拖延时间,待客的时候也是有意上菜慢些。眼看天黑了,客人熬不住都走了,看热闹的也回家吃饭看电视了,这时候他们才发丧。”“那不是还有吹喇叭放炮的外人吗?”“这你又不懂了。吹喇叭放炮的根本不去坟地,出了村口人家拿了钱就回去了。最后去坟地的都是他葛家的人。”“骨灰盒怎么办?”“骨灰盒还不是拣最便宜的买!随便扔河沟里埋地里不都无所谓嘛。”“原来是这样……那葛有理是干什么的?”“这你都不知道?”“不知道。”“他不是咱们梧桐县的副县长嘛。”“他们做得那么秘密,您是怎么知道的?”“乖乖,你大舅我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也是走过南闯过北的,我眼睫毛都是空心的,想瞒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呵呵呵,说笑话了,其实我是闲着没有事偷看的。葛家的坟地不远,离俺村最多有四里地。”“你看清楚了?”“当然了。这不是金贵去黑龙江旅游嘛,买回来一个俄罗斯高倍望远镜,我也想玩玩,那天还真派上用场了。”“你们村就他一家这样做的?”“哪能。自从葛家开了头,俺们村里凡是当头有钱的都那样了,还学得一模一样,也都立了碑。当然,葛万才的碑最大最高,几里路远都能看见,气派得很呐!老百姓别说买不起松木棺材,也找不着两辆面包车呀!就是找着了,人家也不愿意让你那么铺排。”“哦,我知道了。”“什么你知道了,俺姐夫土葬的事怎么说?”“大舅,您老人家也别生气,俺爸肯定不能土葬,必须火化。不是说我怕影响,而是我不能带这个坏头!你像你们村,您老人家都知道了,肯定还有人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让上级有关部门知道了,肯定要追查到底的。那个葛有理那么做影响太坏了,根本不配叫有理,应该叫他无理才对。大道理我不想跟您老人家多说,还请您理解我,原谅我。”“我也只是提醒你,没有逼迫你那么做。你真不愿意我也不能硬来。虽然说舅舅大如天,那是旧社会,现在不论舅舅外甥,谁说的对就听谁的。你应该记得,舅舅不是不讲理,胡搅蛮缠的人。”“谢谢您了大舅!您这样说我最高兴了。”
送走了薛健康,侯大川没有回去,依然坐在那里想着什么。他感觉薛健康反映的情况不是一个小问题,恰恰相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于公于私都不能隐瞒,应该反映给民政主管部门。按公理说,现在农村在搞新农村建设,有的地方还提倡集中墓地,平掉坟头,扩大土地耕种面积,而葛有理身为一个领导干部或许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竟然带头违反原则搞土葬,这是绝不能迁就原谅的。按私理说,一个副县长都敢搞土葬,你堂堂正县长级别的人事局长却不敢,也太窝囊了。当然了,通情达理的老百姓不会说什么,甚至会伸出大拇指夸奖你表扬你,但不通情达理的就难说了,也许会讽刺你笑话你,说你是二分的毛硌不当钱用,说你是年初二买回来的兔子有你没你都过年了,说你是脱裤子尿尿娘们家家的,反正是什么难听说什么。这些农民虽然是少数,但少数也不可忽视,农民的吐沫星子厉害呢,一条臭鱼能搅得满锅里都是醒味。如果葛有理的做法得到纠正,把葛万才等的遗体挖出来重新火化,那侯大川在农民们的心目中就不是一般人物了,他们会说你站的高看得远,于是侯大川掏出手机,打通了电话:“喂,市民政局顾局长吗?我是人事局侯大川……你好你好,我跟你反映一个问题,梧桐县李庄镇葛家庄村有人竟公然搞土葬,带头的就是葛有理,现任梧桐县副县长……”
侯大川刚打完电话,李素梅走来了,“怎么,还生气哪?”侯大川把手机装口袋里,愣愣地道:“我生什么气,如果这点儿事也生气,那我早就被你气死了。”“嘻嘻,我就说嘛,男子汉大丈夫,你侯大川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有什么事吗?”“没有事就不能找你了,我也是在丧屋里闷得慌,走出来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你呼吸吧,我回去了。”“什么意思,厌烦我了?”“哪里话。”“不厌烦就陪我坐坐。”“坐坐就坐坐。”“你现在心情好吗?”“不错。”“能跟你说私房话吗?”“当然。”“说了你别生气好吗?”“你想说什么?”“我刚才看见……还是不说了吧,免得你又不高兴。”“有话就说出来吧,搁在肚子里也难受。不是有句俗话嘛,有疮就想摸,有话就想说。”“这不是刚才大金跟那个周庆祝在给棺椁刷沥青吗,樱桃过来了,我看见樱桃看周庆祝的眼神就不对……”“这事啊,你还是别说了,你们女人就是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太擅于联想推理。”“你不信拉倒,反正我看出问题了,大银是你弟弟,你不问我更懒得管闲事。”
他们正说话儿,侯大川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拿起电话看了看银屏,显示“侯大刚”三个字,念叨道:“是大刚打来的。”李素梅催促道:“你快接听啊,别有什么急事。”侯大川接听电话:“喂,大刚,有什么事?……是吗?那让大利去办就是了,他不是矿上的组织人事科长嘛……嗯,就这样吧。”李素梅问道:“什么事?”“时间太长了,咱爸的遗体有些腐烂了,大刚说丧屋里有异味,需要用冰冻一下。”“你这样说我还真想起来了,今天我在灵堂里就感觉不舒服,说不出什么味。那哪里有冰啊?”“矿上就有冰。大利不是在矿上工作吗,让他去弄几块就够了,明天上午就去火化。”“到矿上有多远?”“不远,大概有二十公里吧。让思源去,来回也就个把小时。”“说普通话好不好,什么个把小时。”“也就一个多小时。你这人就是毛病,在人场里我说什么话都可以,我们单独在一块你就逼着我说普通话。”“我那是顾及你的面子。”“顾及我的面子不错,但弄得我家乡话不会说更听不懂了,让我大舅对我很有意见。”
得到侯大川的批准,侯大刚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安排侯大利出力干活。以前因为侯大刚怕老婆,弟兄几个都不待见他,更不听他招呼,凡事也不跟他商量,能自己做主的就自己做主,不能做主的也是找别人出主意拿意见。这几天侯大利不怎么出门,要么去丧屋里守灵,要么回屋睡觉。人跟人的秉性脾气都不一样,有的人没有事喜欢闲逛,打听个东传话个西,惹出事来躲旮旯里看热闹看笑话,有的人不是这样,不喜欢打听事,不喜欢添枝加叶乱传话,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尽量不掺和别人的事,两袖清风,来去无牵挂。见丧屋里没有侯大利,侯大刚便去他家里找了。
侯大利家与侯大刚家一墙之隔,但侯大利家的房子跟其他弟兄四个比较最孬,就三间堂屋,另有一间厨房,院子也不大,虽然宽度跟大刚、大金家的一样,长度起码比他们两家少一半。院子里没有菜没有花也没有草,就一棵歪把子黑槐树,也是多年无人修剪,长得没有一点儿模样。侯大利在矿上当个组织人事科长,也是清水衙门,比起基建科长、后勤科长、供应科长,那差别大了,没有外快,奖金也少,顶多也就有办调动转关系的送两条烟两瓶酒什么的,就这侯大利还不要,说话也不好听,头拧得跟烧鸡一样,“快拿走,别脏了我的手。”你听听,这叫人话吗,哪个送礼的听了喜欢他。媳妇马爱花倒是贤惠,跟他在矿上食堂里干临时工,说是临时,都干了十多年了,也没有人撵她。两个孩子在矿中学上学,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听话都上进,总是拿他们的大爷当榜样,说将来一定考上一类二类的大学。侯大利的孩子之所以比侯大金的孩子小,是他按照上级晚婚晚育要求做的。他这人就那样,什么都是按规定来,不敢越雷池一步。
侯大刚猜的没有错,侯大利正在家里光膀子睡觉呢。侯大刚走过去照屁股拍了一巴掌,道:“大利,你快起来。”侯大利坐起来,揉了揉眼睛,问道:“啥事?”“都怪天太热,也是搁得时间太长,咱爸的遗体都有味了,你赶紧去你们矿上弄几块冰来。”“这附近没有卖冰的?”“要是有就不找你了。”“不是有卖冰棍的嘛。”“冰多大,冰棍多大,你真憨了你。”“要几块?”“二百斤的两块就够。明天上午就去火化,也就十几个小时的事。”“咋去?”“你跟思源的车去。思源开车在门口等着呢。”“好吧。”侯大利穿上褂子跟侯大刚出了家门。
侯思源不认识路,侯大利只好坐副驾位置给他指引。爷儿俩还没有这样单独坐一辆车里,侯思源显得有些兴奋,主动跟侯大利说话,问道:“三叔,你在矿上干什么科长?”侯大利几乎是从喉咙里发出声音,“跟你爸一样。”“一样?奥,你是人事科长。”“还有组织。”“你们矿上经济效益还好吧?”“还行。”“有奖金吗?”“有,不多。”“你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三千。”“俺三婶呢?”“一千啦。”“一千啦是多少?”“一千二三。”“俺弟弟妹妹学习成绩好吧?”“那可是好,在班级里都是前三名,在学校里也是前十名。老师说了,他们俩考北大清华有点儿难,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应该把里攥。你不知道,他们俩学习可用功了,电视不看,电脑也不玩儿,一门心思学习。呵呵呵,你三婶子心疼得没有法,想周末带他们去你们那里玩两天他们都不去,怕耽误学习。看两个孩子那么辛苦,我也是可怜得没笛吹。”
听侯大利说话,侯思源感觉特别好玩。看吧,都说三叔懒语,其实他话还不少,只是说话没有对他的心思,对了心思,他话真稠密,让你插不上嘴。自己说自己笑,美着呢。
没有多大会儿,侯思源就远远地看到了煤矿。煤矿还真不小,老大的院子,老高的院墙,煤矸石堆成了一座山,塔楼耸入云端,厚实的履带跟随着粗壮的轮子不停地转动着,把一堆堆的煤炭从地下运上来。到了矿门口,门卫看见侯大利坐在车里,扬扬手点点头放车子进了院子。
侯思源把车子停在办公楼前的停车场里,让侯大利下来。侯大利问道:“思源,你还去我办公室坐会不?”侯思源道:“不去了,我在车里等你吧。”“你不渴?到我办公室里喝口水吧。”“不渴。车后备箱里有水。”“那行,我去一会儿就来。”
侯大利知道,矿上的冰是不对外销售的,除非有矿办主任的批条。于是他走进了矿办主任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年龄不大,也就三十多岁,瘦长脸,白生的,头发向后梳得油亮,苍蝇到上面都会站不住劈大叉。侯大利走进去坐到主任对面,问候道:“单主任你忙了。”单主任正玩电脑呢,看见侯大利,惊讶地问道:“侯科长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忙老父亲的丧事的吗?”“这不是需要两块冰嘛。”“怎么,还没有火化?”“没有,明天上午火化。”“几天出殡?”“七天。”“你们弟兄真行,俺爹死,三天就埋了。搁那么多天干什么,人遭罪,还花钱多。”“你说的是,可我不当家。”“对对对,你是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别说闲话了,你快给我批个条吧。”“两块?”“两块。”“多重的?”“二百斤的就行。”
单主任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便签纸,拿签字笔迅速写好了批条,并盖上公章,交到侯大利手上,道:“矿长安排了,你老父亲出殡那天,我们去吊孝。现在提倡喜事丧事从简,我看烧纸钱就免了吧,花圈还是要送的。”侯大利接过批条,道:“谢谢你了。你忙吧,我走了。”
侯大利拿着批条到开票室交了钱开了票,就直接去制冰车间提货了。
发货的是个平头胖脸小伙子,接过侯大利给的提货单,仔细看了看,问道:“侯科长,你买冰干什么用?”侯大利道:“这不是我父亲病故了嘛,天气太热……”“啊!您父亲病故了?”没有等侯大利把话说完,小伙子就大惊失色地问道:“什么时候病故的,我们怎么不知道?”转过身对里面的人喊道:“你们知道不,侯科长的父亲病故了。头,你知道不?”
车间里正干活的人听他这么一喊,都跑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道:“不知道。”“没有听说。”“上边真差劲,这么大的事怎么不通知一声。”“就是。咱上班,不好请假,人场帮不上,钱场得帮不是。”“……”
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方脸大汉把年轻人拨开,走到侯大利跟前,埋怨道:“侯科长你也真是,老父亲老了,打个手机说一声就是了。需要两块冰还花钱开票,真拿你没治。这样吧,冰照拉,钱不要,你把票退回去。”侯大利固执地道:“那不行。冰虽然不值钱,但它是公家的,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方脸大汉道:“我是这里的主任我说了算,不就是两块冰嘛,零售价也值不了一百块钱。就算我送你侯科长的好不好。”“你送我的我也不能要。”“你这人就这样不好,总是丁丁卯卯,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都像你这样,共产主义早实现了。那好吧,我们就公事公办,照单发货。”“谢谢你,杜主任。”“自己人,客气啥。你怎么来的?”“开轿车来的。”“那不行,轿车没有办法拉。四百斤的冰块没有面包车不行。这样吧,你回去,我让经常来拉冰的那个那个独立岗用他的面包车给你送去。”“需要多少运费?”“什么运费不运费的,都是自己哥们。顶多以后多给他两块冰有了。”
看侯大利要走,平头小伙子叫住了他,喊道:“侯科长你别着急走,等两分钟。”
侯大利站着没有动,平头小伙子拿着一叠百元钞票跑过来,把钱交到他手上,道:“您老父亲病故,我们不能去了,这是我们制冰车间十二个人给您老父亲的烧纸钱,一人二百,一共两千四,您点点。名单来不及写了,反正您都熟悉。”侯大利想推辞不要,但看小伙子很恳切,也就收下了。
侯大利与侯思源刚到家没有多大会儿,一位留着长发满脸胡须的中年人开着面包车就到了,问了侯大金,知道没有走错,忙着把冰块卸下车。侯大利没有走远,正在侯大刚院子里跟厨师聊天,听见汽车停车的声音,慌忙跑过来,跟中年人客气了几句话,知道他就是独立岗,就想帮着抬冰块。独立岗道:“侯科长,你不用帮忙了,赶紧找个大洗衣裳盆,把冰块放进去,也好抬也好放。”正在院门口看棺材的秦爱民听他说,忙道:“不用找,俺家就有,平时洗被子的,够大的。”
不一会儿,秦爱民拿着洗衣盆走来,问道:“这个盆行不?”独立岗道:“正好。”
侯大利与侯大金、独立岗还有周庆祝几个人把一块冰抬着放进盆里,抬到了丧屋。
独立岗道:“一个盆不够,还得需要一个。”
马爱花道:“俺家好像有一个,多年不用了,也不知道放哪里了,我回家找找。”
张心月道:“还回家找啥,俺家就有现成的,兴许比二嫂家的还大呢,我回去拿。”
张心月出去的空,独立岗叫秦爱民找一块大塑料布,把冰块包好,又拿被子再包一层,放到灵床下面,跟在场的人说道:“擎好吧,那块冰化完,再用这块冰,保准能撑到明天上午十点。”
独立岗话音刚落,张心月就拿着盆来了,问道:“这个盆怎么样?”
独立岗欣喜地道:“你这个盆太好了,把冰装进去正好。”
于是几个人不敢怠慢,赶紧地去抬那块冰。把冰放进洗衣盆里抬来,直接放到灵床的下面,正好搁在侯继续遗体的脚下。侯继续的遗体是头在外,冲着大门,脚在里,蹬着砖墙。这正好与中央领导遗体的安放颠个个。没有办法,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当地就时兴这样,龙天老爷也改变不了。
独立岗安排好,抽了一支侯大利递过来的香烟,稍微喘了口气,就开车回去了。侯大利想给运费的,独立岗说什么都不要,“你再给钱等于是骂我祖宗。”
秦爱民、马爱花、张心月她们感觉丧屋里凉快多了,也没有了异味,便不出门溜达了,坐在一块聊天。马爱花道:“你望望,今年天真热,才刚立夏有的男人就光脊梁了。”张心月道:“可不是,再不下雨,天就旱了。”“正是麦开花的时候,最好来场雨,不要大也不要小,能下透地就行。”“听说思想和思卿学习成绩都好,你是没有心事了。”思想、思卿是马爱花的两个孩子,男孩叫思想,女孩叫思卿。听张心月说她两个孩子的事,马爱花脸都笑成弥勒佛,道:“两个孩子没有说的,都争气。俺两口子没有本事,说不定孩子有本事,能考上清华北大的。”“看你说的,三哥都当上科长了,还不算本事,你眼眶也太高了。”“你说也是,就他那样,不会说个话,不会讲个理,更不会巴结个人,怎么就当上科长了。”“肯定是沾老大的光呗。”“你那是胡扯,就他那熊脾气,谁的光都不想沾,全靠他自己。哎,对了,听说你们家的鸭子今年生意特别好,南京的商贩都抢着要,是真的吗?”“那可不。去年禽流感,今年养鸭子的少了,自然就贵呗。”“你们家可发大了,钱没处花了,也赞助俺几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你说的,你真是钱打不开点儿,上俺家里拿去就是了。”
马爱花与张心月这样没完没了地闲聊,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自吹自擂,互相抬举,秦爱民肺都要气炸了,忽一声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回头一句道:“闲着没事,吃饱撑的!”
马爱花与张心月挤眼捂嘴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