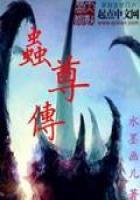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海弦捡了好些干净的雪块盛放在大叶子里,嚷嚷着要煮雪水茶给甫翟喝。自从海弦来了军营,为将军烧饭生火的事倒是不用朱启操心了。海弦每日乐此不疲,总是变着花样为甫翟做菜肴,到最后就连伙头营都不愿去了,干脆搭了一个小灶在大帐里,想要吃什么随时都可以煮。
往常闲来无事,她还会把伙头营里的红辣椒都搜罗过来,然后窝在大帐里埋头熬煮辣椒酱。辛辣的气味飘得满帐子都是,甫翟不爱吃辣,实在被呛得难受,便把脑袋埋进被子里不肯出来。海弦一面擦着眼泪,一面夹起一块年糕,在辣椒酱里滚得红彤彤的,拉开被子往他嘴里塞:“天气冷,吃些辣的祛祛湿气。”
甫翟被辣得从床上坐起来,囫囵吞下辣年糕,抓起一碗茶就往嘴里灌。
海弦笑不可遏,慢悠悠嚼着辣年糕,说道:“你连冰冻都不怕,一块辣年糕就把你辣成这样了。这一锅辣椒酱是我特地熬的,虽然你那法子能练身子骨,可是这里潮湿,里子伤了是怎么练都无法补救的。这些辣椒酱我打算分下去给将士们去湿气,你也必须吃一些才行。”
甫翟心疼道:“我让大夫配一些驱湿的药就好,这些就让朱启分下去吧,你何必亲自去做。为我操劳了这些日子,你也该好好歇息上几日才是。”
“那不行,将军该带头才是。”又不由分说抓起一块凑上来。
这次甫翟变警觉了,还没等她的“毒爪”靠近,他已经迅速躲开了。她扑了个空,跌在床榻上。甫翟连忙拿被子捂住她,只露出一双眼睛和额头,恶狠狠说道:“这里是我的营地,你想造反了不成。”
她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盯住他,忽然伸出一双手来,甫翟以为她还不肯罢休,忙扭了扭脖子准备躲开。她出声道:“别动!”然后一只手碰到他的脸,手指顺着他脸颊的轮廓,慢慢滑到下巴处,又从下巴处往另一侧脸颊慢慢滑到额头,“我突然发现你有胡子了,脸也黑了,不过,比以前更俊俏了。”
甫翟被她的无意举动调拨得心头一软,不由自主俯下来将她的额头吻住,然后掀开被子……海弦的心口怦怦跳着,伸手去推他的手臂,想要拒绝,却又没有一丝力气。
见海弦眼底满是紧张的神色,他忽地手指一顿,停下了动作,快速地坐直身子,帮她把扣子重新扣回去:“我不该这样心急,我该顾全你的感受才是。”
海弦跟着坐起来,双手环过他的后背,侧头靠在他肩上,说道:“我没有不情愿,不过毕竟这里是军营,我不想你因此落人口实。”
甫翟拉着她走下榻,为她整理好衣衫,说道:“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在乎你的名节。罢了,我何必急于一时,反正多早晚再过一年,你就是我的凌夫人了。”说着就撑着床沿下来,海弦忙扶了一把,他却推开她的手道:“疯丫头,给我乖乖坐在那里。”他手指着床沿,表情严肃。
海弦只当他要去茅房,只好听话地在床沿坐下来。
未多时甫翟端着一个铜盆进来,弯下腰将铜盆放到海弦的脚边,说道:“这些日子衣不解带,怕是连脚丫子都要臭了。”
海弦佯装生气道:“你的脚丫子才臭呢。”
甫翟又顺势帮她脱下鞋袜,只见她的脚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冻疮,有些地方已经破了口子,暗色的血迹沾在袜子上。双脚被冻成这副样子,难道这个疯丫头不曾察觉吗?甫翟心疼地将她的两只脚放进水盆里。触到一丝温热,海弦竟疼得吸了一口气。
甫翟用责备的口气道:“总是这般冒冒失失,不顾惜自己的身子。若是把双脚冻僵了,将来要我被你一辈子不成。从今天起,每晚都给我乖乖地泡脚,一日上三次药,切不可忘了。”
海弦乖顺地点了点头,双脚浸在铜盆里,一股久违的温热从脚底慢慢汇入心田。相濡以沫,大抵说的就是她和甫翟吧。她微笑着到:“若是真能背我一辈子,即便伤了双脚又何妨。”
甫翟往她额头上扣了一个响栗子,呵斥道:“再让你胡说八道!”见她眼睛里满是委屈,又急忙柔声道:“只要你愿意,我被你一世也是甘愿的。”
海弦红着眼,正要说话,有人在外头唤了声“凌将军”,甫翟忙应声让人进来。
朱启带了三四个掌管粮仓的将士打着帘子走进来,面上堆着一脸恼苦,手里捧着厚厚一沓册子。甫翟坐下来大口喝茶,问道:“出什么事了?”
朱启领着一个人走上前,把册子一本本摊开在他面前:“我们刚才点算了一下,军营里的粮草已经不多了,满打满算,也只够再吃一个多月了。”
甫翟点点头:“在我醒来以后就已经把信呈给朝廷。”甫翟从枕头下拿过一本深蓝色的簿子,打开来看了看,说道,“算算时间,信应该已经到陛下手里了,大家暂且忍耐些时日,半个月后应该会有人送粮草过来。”
朱启道:“将军不觉得奇怪吗?这些天将军时常递折子去宫里,却从不见陛下答复。”
经他一说,甫翟倒也不禁感到奇怪,论说信到了袁霍手里,无论批或不批,也该给个答复才是。况且粮草干系军心,袁霍不可能连军饷都不批。甫翟想了一会儿,问道:“近一个月两军都不可能出兵,一日三餐可以稍稍减一些,若是这样,大概还能撑多久?”
“草料倒还够用,只是米粮已经不多,如果不行年宴,大概还能再撑四十余日。”
甫翟微叹了口气,说道:“那就先这样吧,我再多发几封信去朝廷。”
等朱启走后,海弦把锅子里的辣年糕全都盛出来装在瓦罐子里。她从中衣袋子里摸出了一枚鸽子蛋大小的玉扳指,放到甫翟手里:“这是我出宫前带出来的,本想着路上要是有个紧急事,就把它当了。你拿去让人当了,悄悄地在附近的村名家里买些米粮吧,这一枚鸽子蛋至少也能多撑四五日了。”
甫翟推还给她:“不行,莫说附近的村名都是大巫人,哪怕是宁国人也不可以。向百姓购买军粮,岂不是等同于告诉别人宁国的将士连饱饭也吃不得。被人笑话是小,乱了军心是大。”
海弦想想也对,只得把玉扳指收回去,忽地摸到一块坚硬的牌子,从中衣口袋里掏出来一看,豁地脸色一变,慌忙将帐帘放下来。甫翟疑惑道:“怎么慌里慌张的?”
她走回来,把手里的虎符拿给他看:“你可认得这东西?”
甫翟看了一眼,说道:“这不是兵符吗?这是从哪儿来的?”
“父皇悄悄养了十万精兵,朱启知晓精兵营在何处。我临走前父皇将虎符给了我,说是哪一日汝明礼造反,便让朱启带着十万精兵去接应。”
甫翟把兵符接过来,沉甸甸的虎符落在掌心里,像是承载着宁国的万里江山。海弦盯着他的掌心看了一会儿,说道:“我们暂且收着吧,但愿这一日永远都不要来。”
他点点头,又把虎符放回到海弦掌心里:“你先继续保管着,我行军打仗不便带在身上。”
海弦紧紧握着那一枚虎符,心中惴惴难安,从接下它的那一刻起,她肩上的担子便又重了一分。
但愿宁国永远风平浪静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边境日趋变冷,夜里寒风大作的时候,常扑得营帐嘎吱摇晃。起先海弦会因此感到害怕,久而久之,也就慢慢习惯了。到了一月中,军营里储备的粮草将尽,京师的军饷依旧迟迟没有发来,甫翟为此犯了不少愁。接二连三上折子请求粮草支援,得来的批复都是“军饷告急,静等”。
眼看着粮草一日日少下去,将士们时常吃不饱,有时候为了省下一些军粮,常把米饭熬成一锅锅浓粥。大巫国多半也得了消息,近日一场战役,吉那突袭而来,轻而易举便令宁国退兵十里。此后的几场仗,靠着众人的意志,才勉强持胜。
甫翟一面同几个郎将围在篝火前削着竹篾子,一面道:“倘若再无粮草支援,我们连打仗的力气也没有,如今能躲一场仗是一场。这些竹篾子都削尖了,到了夜间埋在军帐周围,好歹也能避免突袭。”
朱启无奈地叹了口气,自甫翟来这里后同大巫国的第一场战役开始,俱是无往不胜,从来都只有令吉那节节败退的份,而如今却因为粮草短缺,弄到如此狼狈的地步。他飞快地削着手里的竹篾子,视线里出现一双小小的黑靴。
海弦蹲下来,把一个篮子放到众人面前,篮子里放着几时枚鸟蛋,各色各样,各种大小的都有。甫翟抓起一枚鸟蛋,问道:“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带人在军营里头的树上摸来的。”海弦得意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