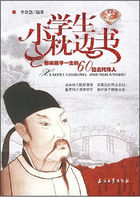恻恻寒风宛茹利刀拂面,甫翟紧紧拉着海弦的手,只一味地往林中跑。后面吉那带着部下疾奔而追,海弦心口直跳,她未料自己的任性竟会换来这一场生死逃亡。
跑进里宁军领地不远的矮山恰好一刻钟,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便有渐行渐近的马声和人语声传来:“分头去找!”
有沁冷的雪花落下来,星星点点般贴上肌肤,新年后的第一场雪偏生赶在这个节骨眼上。马蹄踢着草丛的声音尤为清晰,海弦回头隔着枝桠缝往远处观望,有三四个蛮子跟着吉那正往这里过来。甫翟连忙带海弦闪向一侧,拐进一片枯草丛。靴子踩在沃草上那面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每一声都令人不由感到紧张。为防惊动吉那,甫翟干脆脱了靴子,双足涉在沃草上。他将靴子交给海弦,轻声道:“我背你。”
海弦摇了摇头,说道:“天寒地冻的,你哪里受得了。”为了不被吉那的人追上,她也迅速脱了靴子,只穿着袜子与甫翟一道走在草面上。甫翟心疼地看了她一眼,她笑着回了一个表情,示意她不怕冷。
雪飘得密,未多时,枯草已被铺上薄薄一层白皑。身后传来吉那的怨骂声:“这样的鬼天气,就算能躲过也早晚冻死!算了,撤兵!”
凝息听了一阵,发觉吉那等人确实已经退走了,海弦终于舒一口气,说道:“他们走了,我们快回营吧。”
“先不忙走,虽然吉那不像是装着花花肠子的人,可保不准他身边的人会耍诈,指不定正藏匿在某处等我们自己送上门呢。”眼极处,矮山环抱林木,到处都是黑黢黢的山洞。两人穿回靴子,甫翟选了一处最近的,带着海弦猫腰进去,说道:“雪下大了,咱们先在这儿躲着吧。”
洞口极浅,两人坐在洞口,后背几乎已经可以贴住石壁。石壁凉得慑人,后背刚贴上去,不由激灵灵一阵,海弦冷得打了个哆嗦。甫翟深处右手臂,将她箍在臂弯里,把石壁同她的后背阻隔开。
吉那离开未多时,果然又折了回来,在周围四处找寻着,最后不知是上了山头还是往别处去了,马蹄声渐渐低缓起来。
海弦暗松了一口气,愧疚般看着甫翟。
甫翟刮了刮她的鼻子,喘着大气笑道:“疯丫头,等一会儿回了军营,我一定拿军法处置你。”
她大义凛然般说道:“这次的确是末将的错,末将甘愿领将军责罚。”
晃眼的工夫,大雪已纷纷扬扬如鹅毛一般。北方的雪厚重,落在地上长久不化,片刻间,洞口已积起了厚厚一层,足足有一尺的深度。海弦急得差点跳起来:“糟糕,雪那么大,恐怕他们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来找我们了。”本想着宁军可能会找来,现在因大雪封道,等到宁军找来这里怕是要几个时辰之后了。如果大雪一直不停,他们在这里只有等死的机会。而这一场雪密集,只怕两日之内能够停住已是万幸。
说话的功夫,雪越下越紧。
须臾间,积雪已没到洞口一半高,两人蜷着身子,挤在狭小的空间内。呼出的气息瞬间凝结成水珠,冰雪散出的冷气兜头兜脸。海弦几乎快要支持不住了,渐渐往他身上靠去。铠甲坚硬生凉,与外头的寒雪无甚差别。她靠着他的肩头越发觉得冷,于是只得打足精神坐起来。
甫翟抽回放在她后背的手臂,去解自己的铠甲。海弦一把按住他的手,斥道:“你疯了,会冻死的!其实我不怕冷,这些日子多亏你带我上山,这点冷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他噙着笑,说道:“这点冷对我来说也算不得什么。”
“就算不怕冷也不许脱,听到没有!”海弦强行动手为他扣着扣子。甫翟咯咯而笑,她嗔道:“你笑什么?”
他将扣子扣回去,掰过她的头,让她靠在自己肩上,说道:“我笑那个霸道不讲理的疯丫头实在太可爱,你知不知道刚才你呵斥我不许脱下铁铠的时候多霸道,我就喜欢看你霸道的样子。”
有部分凝雪化为冻冰,冷意一丝丝钻入,像是要直渗透到骨髓里去。海弦冷得打颤,紧咬着牙从身上摸出一个火折子,旋即伸手去够一边的枯树枝,甫翟将她的手拽回来,紧紧裹在自己的掌心里,说道:“枯枝都被雪沾湿了,根本点不起来。”话犹未罗,已将她的脑袋埋进自己胸前。
两人相偎着取暖,海弦冻得浑身麻木,眼皮沉沉,渐渐想要合拢。甫翟时不时地推她一下,口中道:“坚持住,千万不许睡,你要是睡过去了只怕会一辈子醒不过来。听话,千万不许睡。”
她迫使自己打气精神,说道:“阿翟,你同我讲故事吧,你讲得生动,我或许就不会想睡了。”
甫翟点点头,却没有说话。
海弦道:“你怎么不说,我可还等着呢。”
甫翟笑道:“你平白无故让我说,我哪里说得出来。”
团团白色的气息从口中呼出,越发显得山洞清冷无比。海弦想了想,说道:“就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吧,说说你的父母亲。”
他微微颔首,思索道:“我父亲曾是瞿国的将领,陛下同我师父杀入皇城之时,我父亲因目睹瞿国国主的惨无人道,甘愿带兵归降宁国。因我母亲是瞿国的世家女子,极力劝说父亲不得归降宁军。但父亲一心为百姓生计着想,母亲被迫与他和离。她也因此被贬为庶民,我和她在瞿国流离了半年,无奈找去宁国投奔父亲,却被告知父亲阵亡的消息。我师父念及我们孤儿寡母可怜,因此将我们收留在了一座宅子里。父亲离世后,母亲渐渐变得抑郁恍惚……”
她只当自己过去的岁月最是难熬,却不知甫翟也是这般,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她心疼地看了甫翟一眼,他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疯丫头,都过去了,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她颔首道:“将来我们都会好的。”
甫翟又拥着她说了些年幼时候的事,说到汝明礼的时候,话题渐渐变得沉重不堪。甫翟便立即止了口,转而道:“这场雪一定不会下太久的。”
海弦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望着越积越厚的大血,只觉得冻得全身的骨头都刺疼不已。每动一下,就好像离万丈黄泉又近了一步。这场雪,究竟还要下多久?她是否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身子慢慢下滑,海弦的脚已经触在洞口的冰雪上,甫翟见她神情萎靡,忙将她扶回,尽量远离洞口的冰雪。
森森寒气附上肌肤,他打了个寒噤,又说:“说了从前的事,再说说以后。不打仗的日子,我时常想,等我们回了京师办过喜宴,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就该踏遍大江南北,踏遍十里八荒了。第一程你想要去哪里?”
她想了想,软弱无力道:“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雪透过洞口飘进来,落在两人的发上,一如绵白柳絮。甫翟将她拥紧些,把她的手执过,塞入自己的夹袄内。她震了震身子,想要抽出手,他却按得更紧些:“不许动,十指连心,只有手指热了,你身上才会热起来。”
半日滴水未进,她没有力气再挣扎,软绵绵靠在他怀里,两手在他夹袄里腾空,深怕将太多的冷意传给他。洞口的绵白在她眼里变得越来越模糊,她用力咬着自己的唇,迫使自己睁开眼。可是,她实在没有力气睁开了,眼皮越来越软,软得几乎就要粘合在一起。
甫翟望着外头出了一会儿神,忽地将她的手环在自己脖子上,旋过身将她背起,说道:“走一走吧,走一走才能热起来。”
厚厚的雪墙挡在洞口,甫翟抬脚用力踢下去,却是一动不动,只簌簌地落下几个雪球,恰好砸在海弦身上。他稍稍偏过身子,再一次踢下去,雪墙依旧不动。海弦靠在他肩上,恹恹道:“我再坚持一两个时辰没问题的,你可别再浪费力气了,等着他们来救吧。”
甫翟将她放下来,又气愤地踢了几脚,那雪墙始终纹丝不动,他无奈坐回到她身边,捋着她额前的散发,责备道:“疯丫头,都说了让你回京师去,否则就不必在这里陪我受冻了。”
如果她没记错,应该是自己连累甫翟受冻的吧。她换了一个舒服点的姿势靠着,默默把甫翟的手塞进自己的衣服里。触到一丝温暖,甫翟蓦地一怔,快速抽出手。海弦笑道:“我都不介意,你怕什么。”
甫翟面红耳赤,局促道:“我怕你冷。”停了停,又道,“你放心,我冻不死的。如果我真要死了,一定会找个地方躲起来,绝不会死在你面前,不然你会为我痛苦一辈子的。”
“呸,不许胡说,什么死不死的!”海弦轻声呵斥着。甫翟依旧将她的手紧紧握住,他的手确实比自己的要热,她不再坚持,提了提劲说道,“从现在开始,我们谁也不许闭眼睛,也不要说话,留着体温等他们找来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