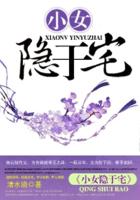汝明礼见他一脸愤怒地离开,忙招来管家,问道:“此去凌宅,可有打听到什么?”
管家道:“听凌宅的小厮说,昨日凌甫翟的确带回去一个姑娘,却是十六七岁的年纪,受着脚伤,并无身孕。”
汝明礼又道:“速去打听那姑娘的来历。”
管家一脸陪笑道:“早已打听回来了,是个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丫头,她哥哥同凌甫翟认识,犯了人命官司,凌甫翟许是见人家容貌好,动了恻隐之心,留她几日也未可知。”
甫翟向来爱助人,汝明礼同他从小相识,最是了解。如今听管家说那姑娘出自穷乡僻壤,倒也无甚可疑。揉了揉额头,只心急堂嫂了去处。
甫翟回到宅子里,就看到海弦坐在花厅里,手里拈着一块枣糕,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跨过门槛,见放桌上摆着一包枣糕,一包话梅,还有几样水果,心想着那小丫头倒也实诚,当真照着他的吩咐将吃食都送来了。
海弦见甫翟回来,忙站起来问道:“阿库那里有消息了吗?”
甫翟从汝宅出来,的确去天牢疏通了一番。因着甫翟的面子,天牢里的狱卒倒是不曾为难过阿库。他点头道:“阿库虽在天牢,倒是无人敢为难他。至于证据,我已经派下属去找了。”
海弦松了一口气,郑重地道了一声谢,倒是令甫翟有些诧异,她仿佛与自己突然生分起来了。她想了想,说道:“我只怕住在这里打扰了你一家,所以打算去外头找个住处。”她虽说得诚恳,面上却有些失落。
甫翟微微一怔,顿时有些不快。想了想,莫非是海弦吃醋了,不觉露出笑容:“我实话说与你,住在你隔壁屋里的妇人,其实是我的一位堂姐。她与夫家闹了矛盾,才无奈来投奔我。不过这件事关乎她的名声,你听过倒也罢了。”
堵在心口的大石因他一句话瞬间落去,她顿觉豁然开朗,脸上微微一红,笑道:“原来竟是你的堂姐,差一点就唐突了她。”
甫翟见她的神情,愈发确信是海弦在为此事吃醋,只觉得心头十分舒畅,不禁问道:“倘若我已娶亲,你心里会作何想?”
她一张脸愈发绯红,却是支支吾吾地不知如何作答。甫翟对她的心思已然猜到了一半,委实不忍心为难她,便笑道:“明天是探视日,我带你去牢里看阿库。不过只有一刻钟的探视时间,倘若你有什么话要说,可得事先想好了才是。”
海弦终于露出几分松快之色,这几日心系阿库,是在无甚胃口。甫翟忙趁机将两块枣糕塞到海弦手里,板着面孔命令道:“把它们统统吃完,否则明天的探视取消。”她微微一笑,飞快地把枣糕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地。甫翟忍俊不禁,笑道:“疯丫头,吃慢点。”
次日天未大亮,海弦便已经早早地起来了。隔壁屋里的小婴孩也醒得早,此时正由甫翟抱着在前厅里。海弦匆忙梳洗了一番,抱过甫翟手中的孩子,说道:“吃过早膳,我们就出发吧。”
甫翟不由笑道:“姑娘,此时方五更天,只怕狱卒还在与周公相会。我们这么早过去,岂不白白在门外等上一个时辰。”
海弦原是想早些见着阿库,或许还能求狱卒给个通融,同阿库多说一会儿话。如今听到才不过五更天,不禁吃吃一笑。甫翟只怕她这一个时辰等得辛苦,想了想,说道:“不如我们去看日出,也好打发辰光。”
简单收拾了一番,朱启准备了一辆马车,将几样点心装在食盒里让海弦带上。甫翟带了一张弓,又捧上了几把箭,竟是将马车塞得满满当当。海弦道:“看日出,怎么还带着弓箭?”
甫翟笑道:“一会儿你便知道了。”
海弦迅速上了马车,甫翟亲自来驾车,并没有带上朱启。两人出门的时候,天上还挂着一轮弯月,浅浅淡淡的月光,照得人昏昏欲睡。海弦想着马上就能够见到阿库,倒是精神尚好,正掀开车帘四处张望着。甫翟因起得早,一副恹恹欲睡的样子,然而山林里多是窄路,只得强打起精神来驱车。
甫翟在一处山坡前停了车,扶着海弦下了马车。海弦望了望那座山,黑黢黢一片,竟是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树。甫翟深怕沿途出了意外,说道:“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看日出吧,树虽密,倒也不高。”
海弦觉得有些饿了,忙把食盒打开来,见里面放着几样精致的糕点,还有一小笼蒸馒头。甫翟看了一眼食盒,笑道:“你且等一等,我再给你添一道菜。”他神秘兮兮地一笑,从马车里取出弓箭,又对海弦道,“这里蛇蚁多,你就坐在马车里等我。”说完便往树丛里走去。
山林里蛇虫鼠蚁不可怕,可怕的是豺狼野兽。海弦深怕甫翟遇着猛兽,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然而害怕他因自己而分心,到底还是依言上了马车,一只手紧紧拽着车帘子,手心里微微沁出汗来。
借着昏暗的月光,海弦看到甫翟正追赶着一只野兔子。那兔子跑得极快,在树林里兜兜转转着同甫翟玩捉迷藏。甫翟也跑得极快,好几次搭箭对准了野兔子,却还是被它逃脱了。甫翟越跑越远,海弦终于看不到了。她顿时有些着急,再往前去是一座高山,那里有狼群也未可知。她忙跳下马车,随手从马车里抓了一把箭,循着甫翟走过的路找去。
一路往前走,竟是一个草坡。沿着草坡一路往下,沃草渐渐稀疏,俨然是块荒地。坡下的荒地上篝火噼噼啪啪地舞着,火堆上架着一只烤鸡,隐隐透着肉香。火堆旁躺着一人,两只手枕在后脑勺上,正仰头看着稀稀朗朗的星子,神情悠闲自在,一看便知是甫翟。
海弦见到他,提起的心迅速落定,却是一脸的不高兴。甫翟听到脚步声,微笑着侧过头,见她神情不悦,只装作不曾发觉,笑道:“你鼻子倒是灵敏,烤鸡还没好呢,也能闻着味儿。”说着打了个呼哨,就听到笃笃的马蹄声,大宛驹拉着马车晃晃悠悠地向这里跑来。
海弦见他平安无事,也不想说些扫兴的话,便微微一笑道:“这就是你给我添的菜?方才那只野兔子呢?”
甫翟笑道:“我两条腿跑不过人家四条腿,让人家溜走了。本想等烤好了再把你喊过来,免得你流口水。”
海弦把脚一跺,说道:“胡说八道,我哪里就这样馋嘴了!”
他第一次见她娇嗔,竟是别有一番韵致。脸不禁红了红,忙拍了拍身侧道:“你先坐一会儿,我去把食盒提过来,咱们也做一回酒肉莽夫。”
海弦道:“那食盒不如就留给阿库吧。”
甫翟笑道:“朱启早预备了一份在马车里。”
她这才放心,挨着他坐下去,抬头望了望乌沉沉的天。恐怕是要下雨了,天际只挂了几颗星星,似黯淡的烛苗嵌在黑幕间,忽明忽暗,并不好看。她张了张嘴,又犹豫了一瞬,才说:“宁国的皇帝会杀瞿太子吗?”她知道此时提起这些并不合时宜,然而这件事就如一块大石,在心中积压了许久。她杀不得瞿国的太子,便也不能令他有机会苟活着。
“暂时不会,毕竟瞿国太子的势力未除尽,陛下还要将他留作人质,不过早晚有一天他是会死的。”他扭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眼神里似乎有怜悯,有探究,更多的是警觉。
海弦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起来,连忙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白玉瓶子,放在手心里伸到甫翟面前,说道:“这里面装的是我娘的骨灰,我娘死在瞿国的军帐里,是被太子活活逼死的。我娘生前受尽屈辱,死后也没能留有全尸,这点骨灰还是我从焚我娘尸身的瞿国人手里夺下来的。”
拿白玉瓶装骨粉乃是宁国的习俗,玉不朽,尸骨不腐。甫翟不料她竟承受了这般苦楚,心中一痛,眼中尽是怜惜:“你和你的娘亲为何会沦为瞿国的……奴隶?”吐出最后两个字,他实在于心不忍。
海弦只是一笑,并不愿相告。
他见她不愿说,只得转而道:“还有一会儿才烤好,如果肚子饿,就先吃一些糕点。”
她虽然并不觉得饿,但还是拿了一块糕点塞进嘴里。甫翟问:“和你口味吗?”她笑着点了点头,举着一双乌亮的眼睛道:“我从不挑食的。”那双乌亮的瞳仁比星子还要灿烂,只是甫翟总觉得这样灿烂的眼睛里似乎还包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他忽然不敢去直视她的眼睛,低头撕了一只鸡腿递给她:“我的绝活,快尝尝。”
海弦吃了几口,抬头忽见那弯月渐渐藏匿进云层里,一道霞光从浮云里慢慢透出来,仿佛将她一张脸亦晕染得微红。甫翟又撕了一只鸡翅准备递给她,侧头见她正抬头望向空中,羽睫如墨,是难得的宁静。甫翟不由看得有些痴怔,就连衣摆被吹进了火堆里,也不曾发觉。
反倒是海弦先反应过来,见他衣摆上燃着一簇小火苗,忙跳起来朝他衣摆处狠狠踩去。甫翟亦是一惊,本能地站了起来。幸而小火苗已经被海弦踩灭,然而她的脚却因为用力过猛,伤口再一次崩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