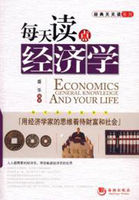次日一早,海弦才刚洗漱完,院子里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响,三个木匠正蹲在院子里做妆台,满地的木穴被风卷起,像是一场春雪,和着正值凋零的金黄草叶,分外好看。她掸了掸落在裙子上的木屑,问甫翟:“这是给谁做的?”
“你说呢,还能有谁。”甫翟见她已经起来,便让小斯抬着一张妆台进来。海弦怔怔地退到一边,看着两人忙活,自己却是插不上手。
“我想着你房里还缺了不少东西,只能想起一件便让人做一件。”甫翟将妆台拼接好,扶她坐到妆台前。
妆台的镜子很亮,亮得能够照出她发丝间的枯黄,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卑微的鸭子,琨黄而毛躁的头发随意梳成了髻子,并无美丽可言。她想起那位妇人,虽比甫翟年长几岁,却是风姿卓越,气质温婉,又岂是自己能比的。
然而甫翟看到的镜中人却是一个脸型小巧,眉眼精致的灵秀女子。海弦虽没有大家小姐的婉约气质,却独有一番勃勃英姿。甫翟并不喜爱娇滴滴的姑娘,他独爱海弦这样不带一丝娇气的女孩子。若是她能够细细打扮一回,自然不输于那些闺秀千金。
他微微笑道:“疯丫头,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个女人,就连梳妆打扮这样家常的事也不会吗?”他从袖子里拉出一根簪子,那簪子很细,是用青竹雕刻的,簪身是镂空的细花,顶端刻着一只蜻蜓,栩栩如生,十分精致,似是要腾空飞起来一般。
甫翟本想问一问是否见到了那张字条,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打算将自己的心意说清楚。然而想着倘若海弦当真对自己无意,无非徒增尴尬,便按耐下了性子。阿库现今身在监狱,即便能够出狱,没有三两个月也是不可能的。想着来日方长,只要海弦对自己有一点好感,他必然是要努力争取的。如今要是将两人推向尴尬的境地,只怕连朋友也做不得。
正犹疑间,却听海弦道:“我的确不会打扮,比不得别人又如何,我自己不嫌弃自己便是了。”说完这一句已是面红耳赤。她只当甫翟是在嫌弃自己。
这个疯丫头可真会破坏气氛,他笑一笑,只得讪讪解释道:“你误会了,我并未取笑你。我只是觉得,你打扮一下必定更好看。”
海弦亦是讪讪的,正待开口,就听朱启在门口道:“公子,汝宅管家亲自派了马车过来,说是汝首领请公子过去叙旧。”
甫翟面色骤变,点点头对海弦道:“你便留在宅子里,哪儿都不要去。我出去办一趟差事,顺便去为阿库打点一番。”他急匆匆步出海弦的屋子,停了停又走向那妇人的房前,隔着门对那妇人道:“汝首领请我去一趟府邸,我去去就回。”
妇人开了门,对他轻声说了几句,面上透着几分紧张和担忧。
甫翟道:“家中还有一位客人,堂姐若是闷了,可以请她过来做个伴。”说完便出门了。
海弦扶着墙站起来,颤巍巍走向门口,恰好看到那妇人立在自己的房门口,正满脸担忧地望着甫翟的背影。海弦与她面对面,那妇人微微瞥眼便看到了她。海弦见她神情一怔,似乎是很意外。海弦朝她微微一笑,算是打过招呼。此时屋子里响起婴孩的哭声,那妇人忙转身进门。未多时便见那妇人又迅速走出来,对海弦道:“新近请的奶娘不知何时过来,可否请姑娘搭把手?”
她忙点了点头,跟随妇人进了屋子里。只见一个脸蛋红红的小婴孩躺在摇篮里,正哭得声嘶力竭。妇人将一只小勺子递给海弦,指着桌上的米汤柔声道:“可否将米汤逼出来,盛到那碗里。”又指着一只空碗。
那妇人拿了另一把小勺子,就着海弦逼出的米汤,一点点舀了送进婴孩的嘴里。海弦问:“凌夫人先前已经足月,为何不早点把奶娘预备好?”
她微微一愣,对于“凌夫人”这个称呼似乎有些诧异。然而心想着自己在娘家的确姓凌,甫翟竟然连此事都肯告诉她,必然是可信之人,便笑道:“甫翟忙于公务,没来得及请奶娘。”
海弦心想着甫翟倘若真正爱惜这对母子,即便再忙,请个奶娘的时间总是有的。甫翟这般对待她,倒是令海弦为她感到不值。妇人将那婴孩喂饱,终于止了哭声,嘟着一张粉嫩的小嘴看着海弦。
“我能抱一抱吗?”海弦实在喜爱眼前的奶娃娃,不禁问那妇人。
妇人笑道:“当然可以。”说着就把孩子递过来,微笑着哄他,“来,给姨抱一抱。”一面将孩子抱给海弦,一面抬头打量她。在看清海弦的面孔后,却是不由怔住。
海弦只管逗弄着婴孩,倒是没察觉到妇人的神情。妇人问道:“不知姑娘芳名?”
“我叫慕海弦,姐姐叫我海弦便是了。”
又问道:“可否再唐突问一句姑娘的年岁?”
海弦笑道:“等过完年,我便十七了。”那小婴孩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将海弦望住,胖嘟嘟的小手露在外头,雪白可爱。海弦因问道,“他的名字起好了吗?”
妇人点头道:“起好了,凌昊。”
那“凌昊”二字,就像是两块顽石重重击在她心口。凌昊,凌昊,他姓凌,可不就是凌甫翟的儿子吗?她连最后的一丝期盼也无了。
京师已经渐渐步入深秋,甫翟出门时匆忙,来不及添一件衣裳,此刻吹了凉风,不觉有些冷了。他往马车壁上靠了靠,双手抱在胸前,想要添一丝暖意。汝家的管家只当他是心虚,笑道:“凌统领何必紧张,不过是我家主人请你去喝一杯茶罢了。这般诚惶诚恐,叫人看了岂不笑话。”
汝家老爷汝伯渊曾随宁国国主袁霍出生入死,一同攻打瞿国三载,战功赫赫。若非他无心战争,向袁霍要了一座寺庙来休养生息,只怕如今的宁国地域再扩上一倍也不止。
幸而汝伯渊之子汝明礼亦是个排兵布阵的能将,然而到底汝伯渊如今只有一子,袁霍不忍将他送去沙场,便暂时安排在身边,做了御林军首领。虽不过是个首领,然而宁国无人不知,他将来必定是当朝驸马,未来前途自然无可估量。
因他嚣张跋扈,从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朝堂众人虽颇有微词,却是敢怒不敢言。甫翟最见不惯汝明礼的嚣张模样,如今见一区区管家就敢对他冷嘲热讽,便说道:“旁人见了将军家的狗尚且要客气三分,何况是汝首领的管家亲自来迎接,凌某岂能不诚惶诚恐。”
汝家管家气得咬牙,一时却无话可反驳,只将他这一番言语暗暗记在了心里。
说完这一句,甫翟便别开头去看着窗外的景象。彼时正值早市,路边站着三两个卖枣糕的女孩子,一头粗辫子拿红绳绑着,高扯着喉咙叫卖,一声盖过一声。甫翟心想着海弦必定喜欢这些零嘴,便对那管家道:“麻烦车夫停一停。”
那管家虽看不起甫翟,但好歹人家是统领,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便半眯着眼朝车夫道了一声“停”,随后又佯装睡去。甫翟刚跳下车,那管家便扭过头眯着眼将他牢牢看住,深怕他有什么动作。谁知甫翟却是走到一个卖枣糕的小女孩面前,笑着说了几句,又给了那小女孩一块碎银子,很快便上了马车。
管家不安地打量了那小女孩几眼,似乎并无异常之处,却终究不放心。
马车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前停下,早有小厮上来扶管家下车。甫翟自己跳下了马车,也不等管家通报,便自己进了宅子。管家给小厮递了个眼神,那小厮忙追上去引着甫翟往园子里去,一面走一面道:“请凌统领等候片刻,我这就去请我家主子。”
早有丫鬟沏了热茶上来,甫翟微笑着接过茶,见那丫鬟已经退走,便细细将汝家花园打量了一番。甫翟曾经倒是来过几次汝宅,不过那是年幼时候的事了。自从汝伯渊剃度为僧后,汝明礼显然成了汝宅真正的主人,听说几年前他将汝宅翻新了一回,大肆动工,拆除了几所屋子,耗巨资建了一座花园。
在旁人看来,汝家盛极一时,这般铺张实属正常。然而在甫翟看来,汝明礼此举定有猫腻。
他走上小木桥,只见桥下池子里只有零星的几尾鲤鱼,那池水有些污浊,池水虽不深,然而黑黢黢的竟是望不到池子底。甫翟正待细看,便听到一个小厮跑上木桥,对甫翟道:“凌统领,我家主人就在西面的亭子里。”
甫翟见那小厮神色有异,不由又往池子里看了看,才跟他走去西面的亭子。甫翟朝汝明礼拱了拱手坐下来,丫鬟重新换上热茶。汝明礼挥了挥手,命众人都退走,对凌甫翟道:“凌兄莫怪我找得这样急,只因堂嫂几日前失踪,找了数日都无果,才惊动了凌兄。凌兄到底与我堂嫂亲厚,想来凌兄知晓她去向也未可知。”
话音刚落,只闻得“砰”一声,甫翟手里的杯盏稳稳地砸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他有些震惊:“我堂姐即将临盆,怎会在这时候离家出走!若非汝大人与我堂姐生了嫌隙,她只身在外,若是出了意外如何是好!”
汝明礼本是刻意试探,想要探一探其堂嫂的去处。凌甫翟遇事向来沉稳,待人接物平和有礼。若是凌甫翟藏起了堂嫂,自然也不会如实相告,然而言语间必定有破绽可循。可如今见他这般激动,倒有些拿捏不准了。
甫翟气得面红耳赤,强迫自己平静下心情来:“我堂姐贤惠知礼,若非汝大人做了什么令我堂姐不满之事,她又哪里肯在这时候离开。我自会派下属去找,但是倘若找见我堂姐,还请汝大人亲自来接。”说着起身朝汝明礼拱了拱手,“事务繁忙,改日再陪汝兄饮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