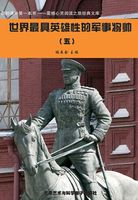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柳箫的师傅,向来和我气场不和,我不想解释,也不削解释。
我不说话,众人便当我默认了,屋中所有人都愤怒地看着我,那眼神恨不得把我当场生吞活剥,大卸八块。直觉告诉我不是好事,我偷偷瞥了眼柳箫,他却无动于衷,好似一尊僵硬的雕像,站立的角落刚好打下一片阴影,藏住了全部神色。
“柳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明晃晃的宫灯烛火,燃遍了屋中各个角落,恍若白昼。透过层层人影,柳箫拧眉朝我走来,视线锐利地落在我的脸庞上,我迎上了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彼此注视着,好半天,他垂下睫毛,犹豫了下,用所有人都听得到的声音清晰问道:“东西……不是你拿的?”
好啊,原来是丢东西了,我瞪了柳箫的师傅一眼,这个古代老封建,居然怀疑老娘是贼?你以为你藏着电脑手机电视机啊,要是有那东西还值得本小姐惦记一番,纵是黄金美人,老娘现在有吃有喝,要那些干嘛?送我,我还嫌重呢……我挑了挑眉,释然地望着柳箫,笑道:“什么东西?”这家伙也忒老实了点,迫于自己师傅的淫威,就摆这么一副脸孔,简直比川剧变脸还内容丰富。
我的故作轻松引起周围人群的不满,柳箫的表情也透出薄怒,我的心咯噔一下,看来这事远没有我想象中简单,这情形……我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死死盯住柳箫。他还没有开口,只听旁边一声冷笑:
“事到如今,苏姑娘还能脸不变色,小小年纪就已深藏不露,苏戚海那老匹夫教得真好,不愧是苏家的人,让老夫佩服。”说完,师傅大叔还拍了拍手。
我只是微笑,咬紧唇角,视线始终落在柳箫身上,这里,我只相信你一个,也只……在乎你的看法,柳箫,你……会相信我么?
他被我看得不自然,转身走到了屋侧的桌几旁,胡乱抓了把壶,闷闷地灌了几口茶。
四周很静,静得柳箫灌茶咽水的声音都清晰得突兀。
终于,一声歇斯底里的哭喊打破了沉寂。
“殿下,不管姐姐做错了什么,求你放过她,这世上,翩翩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不能再失去……”
苏翩翩拽着我的衣服,抓起我的手,啜泣着隐在我身后,声泪俱下,话语哽咽:“姐姐,你快去求殿下,无论你做错了什么,和殿下说,他,他一定会保你的……”
屋内顿时哗然,众人看苏翩翩的眼神更多了几分赞誉。相反,作为反派角色,我同样得到了坏人应有的评价与咒骂。
我平静地接受着这一切,这些……就是我想要的?
我看着柳箫,忆起清冷街心中那道萧索的白影,笑得苦涩。
人群再次哗然,所有人的眼神像刀一般落在我身上,小声嘀咕着,被此起彼伏的声响笼罩着,我有点窒息,到最后,连自己也迷糊了:像我这样没心没肺恩将仇报好坏不分的妖孽,确实不适合前途光明的夜郎殿下……
“够了!”柳箫踢翻了案前的茶几,上面的鎏金紫砂茶具悉数落下,凌乱的声响,好似我那颗疲惫的心。屋里顿时安静下来,他冰冷的声音响起,“你们都出去!”
夜郎士兵们不甘地走了。兴许没见过柳箫发怒,苏翩翩紧紧地抓着我,此时,我们真像一对共患难的姐妹!她本来还想继续说点什么,却被柳箫一记眼刀,吓得闭了嘴,松开我,头也不回地出了屋。
屋子里只剩下三个人。柳箫转个身,恭敬地对着他的师父一拜,低声道:
“师傅……也请您回避一下。”
师傅大叔哼了一声,拂了拂袖子,迈出了门槛。
我舒了口气,口中已经尝到了甜腥。
屋里只剩下我俩,柳箫还是不说话,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
我找了把椅子,大半夜被杜花眠劫去,刚又经历担惊受怕,真是累了。
两人各怀心思地僵持着,诡异地各自选择沉默。
半晌,柳箫终于忍不住开口:“你去见了白寒衣?”
我点了点头,并不感到意外,他这么聪明,既然已选择了他,就没打算瞒着他,更没想过要骗他,只是这场合……
“果然!”他怒吼一声,同时拍碎了身边的花架。
我惊愕地抬头看柳箫,“什么果然?”
“你把那东西给他了?”他赤红着一双眼逼近了我,凝声质问,高大的身影把我笼罩。
“什么东西?”脑中轰然,胸口沉闷,压得我喘不过来,原来他还在在意那个东西,他怀疑我……“你,你怀疑我为了白寒衣……假意……投靠于你?”
他没有吭声,我失望地望着他,为这心灵相通而悲哀,他的确这样认为了。
口中的血腥涌了上来,强硬咽下,颤着声:“柳箫……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回来干什么,选择和白寒衣远走高飞也好,狼狈为奸也罢,何苦还低声下气向你苦苦解释?”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自己的确在乎他,在乎他的信任,在乎他的情绪,在乎他的一切。
他死死地盯着我,没有开口的意思。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一句接一句,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最后终于失去信心,像所有电视剧没用软弱女主一般嚎啕大哭:
“真的不是我……柳箫你信我啊……”
我恨自己没有尊严,真是风水轮流转,从前鄙视的万恶桥段也会落到自己头上。
难道这真是所谓的爱,爱到把自己降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柳箫冷眼看着我,最后终是叹了口气,帮我拭去眼泪,声音带了一丝柔和:“白寒衣现在在哪里?”
他?我呆立在那,不知应该怎么开口,嘴角抽搐。
我的犹豫刺激了柳箫,他苦笑一声:“事到如今,你还想……保护他。”话语夹着伤痛,语气却很肯定。
什么东西瞬间破碎。
“你还是……不相信我。”
“白寒衣已经死了。他,他是被我杀死的。”我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像发疯一般。
记得白寒衣曾经说过,十二年前的他第一次杀人,而第一个杀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另一个自己——白衣衣。如果说暝水宫的暴乱让潜伏在暗处的白寒衣泯灭了自己的美好选择了残酷冷血;那现在……我可不可以自恋地认为:则……是因为我?世人闻之色变的光华公子不在,又选择做回了本不存在的白衣衣?
白寒衣,白衣衣,白寒衣,白衣衣,白寒……
我终是对不起你啊……
胸腔一阵闷痛,剧烈地咳嗽起来,脚步不稳,向前倒地。柳箫好像被吓到了,立即扶住我,一边拍着我的背帮我顺气,一边焦急地大吼:“军医,快,叫军医来!”
我努力笑了笑,柳箫的脸色愈发难看……本来想缓和缓和的,看来,苏飘飘这张很倾国的脸此时被我用错了地方。
前方响起凌乱的脚步声,窗外的风声合着冬日的雪声,纷纷扬扬——离开白地雪山,第一次遇到了雪。可惜……
终于,强大的晕眩感袭来,意识渐渐脱离,黑暗来临。
也好。
我陷入了一场甜美的梦魇。梦中,没有柳箫,没有白寒衣,没有这里的一切。我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礼服,带着华丽的假面,徘徊在同样身着华服的男女之中。这个场景,好似十八世纪的宫廷舞会,也好像快乐的社交派对。
小提琴曲流畅地流淌着,钢琴声愉快地叮咚跳跃着,周围的人脚尖垫起,合着温暖的音乐,一个华丽的旋转,裙裾如同绽放的朵朵百合。
徘徊在期间,我茫然地左右张望,我不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唐突出现。然周围人却像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一般,依旧热情对望,翩翩起舞。
突然,灯光重新打下,形成个个圆圈,柔和的音乐响起,热恋中的男女对对滑入舞池。
我站在边角,有些无措。
突然,前方伸出一只手,带着洁白的手套,宝蓝色的礼服上镶着红宝石的袖扣。他带着一个威尼斯描金边面具,朝我微笑。
这一刻,犹如月野兔遇到了夜礼服假面;犹如祝英台遇到了梁山伯;犹如白娘子遇到了许仙;犹如八仙聚首……呃,好吧,原谅我的词穷。我鬼使神差地把手伸出,和他一同旋转。
乐曲变得炙热,他托着我的腰,感受带他手心停留的真实温度,我有点兴奋。受蛊惑般,大胆地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那里折射出来的是深邃的迷色,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深深把我吸引沉醉。我读出了他眼神中的深情,因为柳箫这样望过我,甚至白寒衣偶尔也……
悠扬的乐曲,今夜本就属于这样的缠绵。好像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等这么一个人,来邀你同跳一曲小步舞曲。
彼此吸引,一起沉浮,共同沉沦。
这一切,那么陌生,但……又似乎本应如此,好熟悉的感觉。
好像过了一辈子。
直到……曲终人散,心却依旧温暖。
睁眼,熟悉的床榻,告诉我没有被柳箫那小子扔到野外,或者像以前网上看的虐恋情深小说上惯常有的,被残暴的男主丢到军营中某种帐篷中过生不如死的生活。
幸好,我开始庆幸,柳箫同学虽然成长环境压力过大,但是毕竟心智正常,心理比较健康。还是大好有为青年一枚,断不会拿我等无知小民出气。
屋子中没有别人,我试着坐起来,一看顿时无法冷静。靠,哪个不长眼的帮老娘换的衣服,而且还没有系好,白花花地露了一片。难道是柳箫,不对不对,此人那么害羞,那就是军营中唯一的女性——苏翩翩?对了话说此女现在去哪里了。不放心啊,想起她的缠人功夫,再耍点小手段,万一柳箫把持不住,被霸王了,那以后咱岂不是要两女侍一夫?
啊啊啊啊,我不要啊。
胡思乱想间有人进来了,装睡明显已来不急,我赶紧换上一个严肃的表情,气势汹汹双手叉腰站在床前。进来的却是师傅大人,他有些惊愕地瞟了我一眼,之后便恢复往常。我尴尬地赔笑,赶紧卷起被子重新躺下。死柳箫,丑柳箫,靠,害老娘的无处发挥。还有这大叔,现在进来准没好事!我缩在床脚,打起精神,准备与师傅老人家大战五百个会合。
“苏姑娘,醒了?”
“嗯!”您这不明显废话么,不然是见鬼了还是,虽然老娘明显就是一鬼,我偷笑。
他清了清嗓子,大概对我目无尊长感到不满,话语也恢复了冷冽地工作状:“老夫看姑娘此时昏倒,和上次受白寒衣那掌有关。伤口已经结痂,等疤掉了……就……”
“什么?”听到此,我弹跳起来,龇牙咧嘴颤着声大叫起来,“你,你看了我,我的胸口?”死柳箫,我抓紧衣襟,想着一会见到柳箫怎么让他给个说法。
没想到师傅大叔笑了起来,“医者目中本无男女,苏姑娘言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