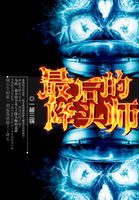陈建对此评案说:“此皆陆学养神要诀。此即佛氏以事为障之旨。”“所谓只自完养,不逐物,谓别事不管,只理会我,即管归无事,安坐闭目养神一路。”“此数条只是要得闲旷虚静,恬淡退寂,意念皆忘,丝毫无累,任其自然自在,以为完养精神之地。”(《学蔀通辨》后编中)并引《庄子》“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与佛教《息心铭》“人法双静,善恶两忘,自心真实,菩提道场”等语相对照,以证陆学类禅道。但陈建据此证明陆学类禅,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因为,爱养精神,保持心的恬静与清明,非佛道独有,儒学中本有此类内容。把儒学归结为尚动的、向外的、入世的,把佛道归结为尚静的、向内的、出世的,此虽有一定道理,但这种二分法尚嫌简单化、绝对化。如果以这种二分法论宋明以前的儒释尚勉强可说,若论宋代以后的儒释道,则大不可。即以宋以前论,儒释道三家就已在不断互相吸收、融合,不断改造、创新,你中有我,互益互利。孔子向往“浴沂风雩”之乐,叹“吾与点也”,不正是万缘放下,沉浸于自然之纯净清新中陶养精神吗?“君子泰而不骄”,不正是要人们去涵养安详舒泰的心境吗?“刚毅木讷近仁”,不正是要人们谨于言语,爱养精神吗?孟子之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之“虚一而静”,《中庸》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等等,皆此类话头。虽然先秦儒家尚无宋明理学那样极端的说法,但爱养精神,恬淡舒泰,抛弃杂事牵累,却是儒家思想中本有的。儒家思想是一种较为中庸平和的学说。它在动静、理欲、天人、损益诸方面,不陷于一偏,故并不排斥恬淡、静穆的一面。不能一见此类稍极端的说法,就说其为佛道。就宋明理学来说,它之所以广大精微,就是因为它吸纳了佛道的思想内容,把中国文化中尽可能多的东西熔为一炉。宋明理学的这种吸纳、融合,正是中华文化动静兼备、外内并举、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入世中求超脱诸种性格的根本条件。尽管历代都有正统文化的卫道者对于异端的攻伐和统治者出于种种目的对于异端的整肃,但总的说,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理学在保持它的重视道德教化、重视个人精神修养、重视人群的互济互利、重视恬淡中和的人生旨趣的基本特征下,吸收各家的思想。有的理学家吸收得多些(如陆学对禅,周敦颐对道家),并有极端一些的言行,应当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去对待,大可不必张挞伐之军。至于出于卫门户、争意气、挟私怨而有的过甚其辞的评说,更不可取。
站在同情理解的立场,陆九渊要人“只自完养,不逐物”,“剥落物欲”,要人不要时时被外事牵扰,“一切荡涤,莫留一些”等等,皆是保持本心清明,不受障蔽的必要前提。并且陆学的功夫论也并非仅此一途,不过他主要强调“打叠田地洁净”而已。陆九渊所要纠正的,是人心陷溺于书册,独立精神斫丧,人被外事牵累,于事不能自做主宰种种弊病。他倡导的是一种精神昂扬、生气淋漓、尊己信己、勇于承当的精神。陈建对此视而不见,他对陆学的批评多属过甚其词,如他说:
愚尝究陆学自谓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为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陆氏则养神为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渊之别,若何而同也。
《孟子》七篇,说心始详,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对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对事而言。一主于寡欲存心,一主于弃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释毫厘千里之判。(《学蔀通辨》后编中第6页)
其偏激之处一望而知。故《学蔀通辨》引起心学学者的反击亦属当然。《学蔀通辨》对王阳明“致良知”也进行攻击,它摘引了阳明书信及《传习录》中的一些话,说阳明学术根源尽在禅学,如: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妍媸之来随物现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物而无情也。无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答陆原静书》,《传习录》中)
王阳明这些话,虽涉及佛教而实旨则是儒学。王阳明有“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等重要命题,而其宗旨归于“致良知”。一切论说,皆围绕此三字。他所谓良知,其中重要的含义就是天理、天性在人心中的自觉,这一点继承了孟子所谓“四端”,陆九渊所谓“本心”,王阳明称它为本来面目。王阳明功夫比陆九渊细密者,陆九渊多讲“先立其大”,先立其大之后的功夫节目提揭不明。王阳明揭“致良知”之教,致良知的主要意思是:“推致吾心良知所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大学问》)将心中的善良意志推致于具体事物,在善良意志的主宰与指导下完成具体行为,这里不但有“头脑”,即良知指导,还有“细目”,即完成具体行为所需要的知识参与。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是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结合。“致”字即是行字。即功夫即本体,即内即外。本来面目即良知,常惺惺即良知常醒觉,不昏昧。这里借用了佛家语,功夫实旨全在儒学。而借佛教言语,是当时佛书为一般读书人诵习的风气之下便于学者领会的一种手段。这正显示王阳明的善教。王阳明对儒释之异的关键处,提揭得十分明白:佛氏本觉,其心体没有伦理内容;儒者本良知,其内容为天理。良知虽时时显发,但它并非时时可感的形下心念。故说它无事时皦如明镜,有事时随物现形,此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王阳明吸纳了佛教的某些思想,特别是其修养方法,借鉴佛教处甚多。而这种借鉴吸纳正所以成阳明学之广大精微。
《学蔀通辨》对王阳明吸收道家之处也进行抨击。他列举《传习录》下面二段话并加以评案:“问仙家元气元精元神,阳明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后世儒者之说与养生之说各滞于一偏,是以不相为用。”陈建的案语说:
阳明良知之学本于佛氏之本来面目,而合于仙家之元精元气元神,据阳明所自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辨矣。奈何犹强称为圣学,妄合于儒书以惑人哉!愚谓阳明良知之说其为杂为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阳明为真圣学,尊信传授而随声以诋朱子者,亦独何哉!(《学蔀通辨》续编下第2~3页)
阳明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学术界研究已多,本书阳明章也已涉及,这里不详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阳明对佛道绝非随声附和,他是用佛道的思想资料发挥自己的学说。如“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的说法,正表现了阳明重综合甚于重分析,重整体甚于重部分的思维趋向。阳明哲学宗旨为致良知,致良知是他的本体论,也是他的功夫论。阳明学说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伦理学说,他对世间万物,既注重它本身的性质,又注重这些物上表现出的伦理意味,后者更是他着眼命意所在。在阳明看来,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是气。气流行充满,运动不已。气的凝聚为精,此精为气之精华,而非精灵、精怪之类。妙用为神,此神类似张载所谓“鬼神者二气之良能”,指气的神妙不测的作用,非精神性的存在。阳明之“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实际上是一种理在气中的思想。气为物质性存在。理为气运动中表现出的规律、法则。规律、法则以气为依托,为运用,气以规律、法则为统帅,为主宰,二者是统一的按一定法则运动着的气的不同方面。这一思想借道家的概念表达出来是十分贴切的。一个思想学说是不是有价值,不在于他的思想中汲取、借鉴了当时人们认为的异端学说,而在于它为人类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多少新的创造因素。阳明以其博大的气魄,在旧有心学的基础上,把儒学往前推进了一步,对当时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关系,道德提升与知识进步的关系,理与欲的关系,内圣和外王
的关系,道德修养的根据和理想人格塑造的途径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回答。而他在事功上的建树,正是他这些理论的注脚。阳明当时,他的学说虽遭到压制,但他的学说中包含的创造因素,他的理论对当时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以及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他的学说在明中叶以后迅速传播开来,成为理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学说,王学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阳明思想的形成,佛道学说是重要助缘,任何出于门户之见对它的贬低、任何以它吸收接纳了“佛道异端”为理由对它的攻击都是眼光浅陋的表现。
《学蔀通辨》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陈建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把被心学、禅学占领了的地盘夺回来,恢复朱子学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对陆九渊、王阳明、程敏政等的心学观点,采取直率攻击的态度。《学蔀通辨》问世之初并不显赫,后因东林顾宪成及后来顾炎武、张履祥、陆陇其等的称许方渐渐为人所知。此书之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张烈诸人,皆有尊朱排陆王之作。而陆王派学者亦群起反驳,程朱派和陆王派各挟门户之见,争持不下,成为清代前期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当代学者钱穆尝说:“今于学术大范围内,单划出理学一小圈,又于理学一小圈内,专钩出朱陆异同一线,乃于此一条线上进退争持。治陆王学者,谓朱子晚年思想转同于陆,此犹足为陆学张目。治朱子学者,反证得朱子晚年思想并无折从于陆之痕迹,岂朱子学之价值固即在是乎?……此诚是学术界一大可骇怪之事。”(《朱子新学案》第159页)此真一语道破清代前期义理学者的固陋和狭隘。
陈建以一史学家著《学蔀通辨》,在对陆王的批评中表明了他的哲学观点。这些观点大都出于朱熹。《学蔀通辨》因它的门户之见,所可称述者不多,但它代表了明代后期一种学术趋向:即在王学风靡学界的情况下,为朱学争正统。朱子学自确立为官学之后,一直是读书
人家传户诵之学,加上科举的推动,朱子学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其影响十分深广。除了它作为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朱熹思想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完备的形式、平实的文字在读书人中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虽然王阳明崛起之后,王学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具有耸动一世学风的力量,但朱学作为深入人心数百年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仍有极大的影响力。其间服膺朱子学者起而为朱学鸣,也是学术发展必然有的事。陈建的《学蔀通辨》是自晚明开始的由王学向朱子学回归的思潮的先导,这股思潮后来发展为思想
家们在明亡国耻的刺激下对王学的反省和检讨。这一思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陈建的《学蔀通辨》作为这一思潮的开端,对它后来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