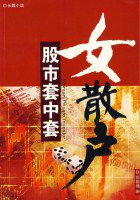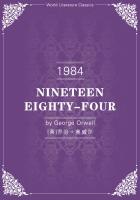那一天,枯死的白杨树叶落了一地,还有屋顶。老爹叫我爬上屋顶,把树叶扫下来。在屋顶上,我站得高高的,远远看见努克家雇的拖拉机嗤嗤嗤地碾了一地的尘土,正朝我家的这个方向开了过来。
车斗里的家什堆得高高的,司机的驾驶室里坐着努克家的女人和两个正朝我挤眉弄眼的小孩。
我有些羡慕地看着车子远去。
老爹看我久久在房顶上不下来,什么也不说,只管把木槌子在荡料池中捣得嗵嗵响。
自从二弟走了之后,每天,老爹除了干活,变得更加少言寡语了。
那天,我小心翼翼地对老爹说起搬迁的事情,可是,老爹很干脆,说他不搬,不打算从红柳的泥屋子里搬出去,他说自己用红柳和苇秆搭建的院子在这里算是建得早的,住的时间长了,离不开。
老爹还说了,红柳的泥屋子会呼吸,会吸汗。人在这样的房子里走动,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失去古丽后,古在和田待了下来。
九月的一天中午,我躺在垫子上,假装在睡,听见有人在说话,声音很闷,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呛住了,就像是在漫长的憋闷之后,水管子里终于喷出来水的声音。
是古。
他和老爹在屋子里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还有笑声,瓷声瓷气的。
古好像是在说,他以前租住的买买提江家里的房子昨天已经搬迁了,房子要拆,自己没地方可去,要来我的家里,与老爹同住一段时间。好像,他还说起了要给老爹交房租的事,话没说完,就被老爹制止了。
这些声音透过门缝传了过来,让我愈发感到不安,我想到要去树林里砍些桑树枝回来,也许,这样一直忙个不停,会多少掩盖一些内心的不安。
这种感觉就像爱一样,过分的不安也有自己的情调。
门开了,古走了进来,皱着眉头看着我手中的那把短柄小斧:“你要去树林里砍桑树枝吗?”
我说是。
“还是我去吧。你是小孩子,我担心你会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
古的声音好像从另一个陌生的地方飘过来。
我笑了一下,告诉他去树林里砍些没倒下来的枯树,不要那些枯死得太久或者腐烂的。
古在前面走着,我在他的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一路上,他是安静的,也是沉默的。
一枚淡淡的太阳,很怯懦地挂在角落里。
十几分钟之后,我们一起来到了河坝子上。
到了九月下旬,空气中有了一丝凉意。枯黄的树叶儿从白杨树上缓慢落下。迟钝的野蜂在向日葵衰败的花叶中安眠,似乎并不担心它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
他脱了鞋,把脚伸到了河水里。
“你下来吗?”
他回过头问我。
我摇摇头:“不。”
河滩上没有人。太阳明晃晃的,恍然让我想起去年那个我熟悉的场景,还有古丽落水的那个夜晚。我没有告诉他,似乎从那以后,我开始怕水。害怕水,好像是我从小的恶习。
可现在,他却要让我征服这可怕的东西。
他说,你先盯着水面看,水面很平静。我迟疑着,不能肯定这一点对我来讲是否有用。对于这一点,他却没能察觉出来。
我突然感到有些恐惧。古丽的命运有可能落在我身上。
“我不到河里去。”
那是我的声音。他不会不认得。他吃了一惊,抬头就撞上了我的眼睛。目光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没有要挪开的意思。
“我不到河里去。我不到河里去。”
待他走得很远了,身后,我的声音也在慢慢减弱。
古在我家过了最初的几夜后,天,彻底凉下来了。
院子里的梭梭柴全都烧了御寒。那些柴禾都是我从河边的小树林里捡来的。
我有时在夜里醒来,会看见清冷的月光打在土质的矮墙上,白白的。我总穿着一条旧裙子睡觉。烧了火以后,屋子暖和多了,所以我可以这样睡觉。
我回想起古的脸以及脸的下颌处的沙褐色坑迹。
现在,这张脸,没有任何表情,隔着一大堵墙,已经沉睡了。
隔日的晚上,因为房子搬迁的事,古和老爹去找了和田房屋搬迁处的负责人艾力。
艾力在说明、解释关于房屋整体搬迁那件事情的时候,细节颇为繁琐,没有发现古正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一轮残缺的月亮正浮在云层里,自在漂浮,无拘无束,漂浮在人间种种争执的俗事之上,漂浮在无止境的土地买卖的事物之上。
古似乎对于眼前的事反应迟钝,正凝神窗外的杨树在微风中轻轻颤动的模样。淡淡的月晕在弥漫,有如神示。
此时,他的心思在心里盘算,还有多少天,月亮才会丰盈,并因此带来今年的第一场霜冻。对他而言,则是宣布他的梦境再次开始。
整个九月,古每晚都在白水河下游的河滩上击打水面,且动作越来越急切,眼睛睁得好大,他深深吸气,嗅闻河水的味道,追寻那带着盐味的飘忽浓烈的水汽。
他谨守自己的迷信:只有在月圆之夜,河流的秘密才会交换秘密。如此,正对着向晚的月亮前行,走向可能带来吉兆的水域,他才可以得到充足的浪花,而不会留下影子。
一天,从河滩回来的这天晚上,古睡得很死,很沉。他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甚至什么也没有想到——
月亮升高了。
水渐渐浑浊,似乎要转入另一个支流。
刚才响在耳边的私语声一下子消失了,可此时他的心被一个美好的预感带动着,继续向前溯游。这时,倾斜的水流突然变得平缓。
这时,奇迹真的出现了:
是一群裸体的年轻女子。
是在凌晨四点多的时候,也许是夜最静,月亮撑得最圆、爬得最高的时候,风吹弯了她的手臂。她的赤脚已经碰到河水。河水的波浪一层层卷起幻想的波纹。她的头顶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秋夜——村庄里的鸽子飞回了屋檐下。
柔软的月光里叽叽咕咕的声音在夜风中弯曲。
尽管这梦境其实不过短短数十分钟,但却有其完整、独立的空间。但那是一种注定不能持久,不知何时出现的,无以把握的又一次重逢。
水渐浊,似乎转入一密闭的腔内。水下依稀有脚步阵阵,节奏如心脏。就在这个时候,水流突然变得湍急,像是快速地被抽吸向某处:
“有人。”
水面上,一个女子柔细的惊叹,之后,什么也听不见了。
只剩下眼前的这个人,这个女子。
她的容貌酷似古丽。
她坐在河岸边上,赤裸着脚踩在一块黑褐色的、粗糙的石头上,并把脚伸到河水里去。现在,她背着光,单腿稍稍举起,动作近乎凝滞。月光微亮处,她的眼睫毛卷曲、修长,一如阿拉伯花饰,对慢慢朝她走近的古,还有逐渐粗重的喘息声恍若未闻。耳中只有那激荡的白色浪花轰隆奔涌。
她的嘴唇微微开启。
她把她的裙子撩到膝盖以上。
她的身体圆润而厚实。
他想与她说几句话,可她转过身就朝另一个方向去了,可就在她转过身去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她的身子几乎是透明的,但是她的如拳头大小的心脏,是白色的,也不全白,在右下侧有一抹红色,其颜色是那种刺眼的石榴红,活跃,热烈,像是要滴下血来。
“来,靠近一点,我有话要对你说。”是古丽的声音。
在做梦的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
为什么古偏偏只看见她的这颗心脏呢?
“古丽。”他轻声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两个字的音节后,猛地深深吸进一口气。
“古丽。”
他又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风像一下子静止不动了。好像这两个字的形状以及给这个名字以生命的人,都被这嗡嗡的风声凝结住了。
他的嗓音降为维吾尔族式的低语。
其结果可想而知。待古终于附身在她之上,深深进入了她,去碰触那“距离”的深处,只听见她的急促轻叹,在他之下,与他迎合。先前河流里那震耳欲聋的水声却霎时变得寂然无声,复活在他眼前的古丽的影像,在此刻却完全沉默了。然后,她的身体好像是被抽空了一样,只剩下单薄的影像、气味和最表面的轮廓。
早晨醒来之后,他的大腿根处一片濡湿。不久,古不得不承认,他抱着的,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肖像,一个虚假的替身而已。这经验虽然刺激,却是彻底失败。
从那以后的很多天里,古再没有梦见古丽的任何影像。
5
由于无视搬迁的通知,两个星期后,我们这儿一大片破残的红柳泥屋的村庄就全部停水了。
不过,断水好像并没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老爹和古更不用说。我们继续每日的作息,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每天不过就是到村口的井里汲水,途中水桶水花四溅。
古每隔几日还是那样,在河滩上寻寻觅觅,而我,则每天到桑树林里给老爹采集细嫩的树枝。我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跟桑树说话。这种语言不是他给我说话的那种。
当我回到家中,看一条条的桑树枝被老爹敲击时发出 “嘎嘎”声,然后削成薄的,还有长的枝条,它们像绿色的蛇一样蜷伏在老爹的脚下,心里就很安静。
老爹的手背多皱,关节粗大,他每天发出的只有干活的声音。那些被剥完了树皮的枝条由湿润的淡绿色变成灰白,最后是干涩的白色,然后,老爹生火熬煮它们,捣浆,挂浆,一点都不觉得累。
整个院落里充满了桑树汁生涩的味道。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家里的电也停了。
某夜,老爹的屋子突然陷入了黑暗。电源被切断了。
到了夜晚,老爹点起了蜡烛。在黑暗中,他弯下腰来,影子也跟着折叠下来。奇怪的是,这件事对于老爹和古,还有我而言,似乎有些无关紧要。
我们三人点着油灯一起吃晚饭,饭是抓饭。一如在那次沙尘侵袭的当晚,我和老爹两个人端着药草茶,走到冒着热气的火炉旁。
周围的人家都搬空了。
院子里很是寂静,墙角不知什么时候起长满了杂草。一排排桑皮纸的架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任凭发白的月光把冷冷的光投射在上面。
这是少有的情景。
在那些没水没电的日子里,我和老爹还有古就这么一一摆脱现代发明,开始过着没水、没电的生活。
半夜里,我睁开酸胀的眼睛,透过窗户的裂隙看一缕缕的月光,屋子里的那盏闹钟细微的滴答声在我的耳畔响了好久,穿插着临屋入梦者古的平缓的呼吸。
院子里,一东一西是两棵上了岁数的枣树,像两个始终孤单的人形。东边的粗大枝条上有一个破残的鸟巢,里面有一颗在白天和夜里都睁着的深渊似的泥眼睛。天晴的夜里,会从树的间隙落下一条线似的月光。
风吹动树叶的细碎声响,在此时弥漫上来,慢慢灌满这院子里每一处积落物质和时间灰尘的隐秘空间:梁柱、暗角,还有浮动在其中的人的平静呼吸。
在这个有风的夜晚,不确定的方向远远地传来几声狗吠,夜鸟、昆虫的族类,像被巫术定了似的,全都停止了叫声,又——在瞬间动了起来。
6
二弟走后,再没回到这里。
可我还一直记得那天老爹病倒前在石槽里捣浆的姿势。
那天,他赤裸着枯瘦如柴的身体,将砸粘了的桑树韧皮装进木桶,一边用长柄的捣浆板上下嘭嘭地捣动。他大口喘着气,嘴里一边骂咧着,不一会儿,老爹的身躯就不见了,可他粗重的呼吸还在。
醒来以后,老爹已经不大会说笑了,只知道干活。他在这种养病的清闲的日子里也没显出几分清闲来,整天都待在院子里,手里拎着铁锤,牙齿上咬着几枚钉子,对着靠墙的一排木模子敲敲打打,忙个不停。捶树浆,捣浆,在石槽子里荡料,每日去河滩树林子剥桑树皮的事情就交给了我。
老爹将砸黏的桑树嫩皮浆放在木桶里,埋到土里五六天后,浆就“熟了”。
该“荡料”了。
老爹绕过几口荡料的水坑,半蹲在木桶边的水坑边上,身子俯向前,把纸帘的模子平放在上面,将一张张纸帘平稳地托起。
老爹就这样从早上开始起,连续好几个钟头,把搅好的木浆涂在帘布上,然后,再端到有阳光照射的空地上等着晒干。老爹的生活只有这每日带着凉意的阳光。
没多久,树底下存放的桑树皮已成了黑糊糊的一堆,上面的一层皮全腐烂了。一眼望去,和一堆烂草皮没什么两样。屈指一算,老爹从病了开始,竟有五个月没有做桑皮纸了。
老爹病好以后开始做桑皮纸是在某个春夏之交的一天,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杯水,我记不起这杯水是什么时候放的,想不起来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这时,半开的窗户外边传来老爹“噔噔噔”捣浆的声音。
老爹将喂过蚕的桑树枝丢进了大锅里,却忘了在水里拌上胡杨灰碱,最后,晒出的纸满是结疤——当然,这个场景融入了我的想象。
我朝坡下的河滩望去,晚秋的风中夹杂了牛群的铃铛声,隐隐约约,含义模糊。我好像又回到了白水河里寻觅,感受着混浊水流的变化,以及它流过拐弯处卵石的强劲和迅猛。河水涨得恰到好处的时刻,我无数次地在这条河里消磨,还记得很清楚:我没有一次捡到过玉石。
直到有一天,我打开一卷黄褐色的桑皮纸,在纸页中,无意中发现其中一张纸页的一角嵌入了一枚金黄色的落叶。大概是在晾晒纸张时,无意中被风刮上去的。
蜜蜂嗡嗡。
桑树皮含着一股浓重的植物清甜味道在我的周围形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独特氛围。
不过,令我难过的是,才不过数十年后,这种手工制作的桑皮纸已无人问津,让人不禁黯然想起那个逐渐消亡中的世界。这种桑皮纸以它粗糙的,带着泥土和植物气息的质感,让人的感觉接近更加清晰敏锐的世界。
我想起今年入秋以来,以往那几个定期来我家收购桑皮纸的汉子,竟也不来我家了。在街上遇见他们其中的一个,语气竟也躲闪、模糊,说是自己不做这生意了,桑皮纸不好卖了,现在没人再用这样的纸了。
老爹听了,比他更紧张,声音都发抖了,一个劲儿地说没关系、没关系。
一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以前相熟的收纸人。当老爹蹲在院子的一角,正在清洗捣浆的工具,听见院子的门突然有了响动,看见那顶卷了毛边儿的、黑得冒油的羔皮帽子贴在了门框上,他立刻激动地站了起来。
“啊哈,你好啊。”老爹冲他笑了起来,“好久没来了,进去喝杯茶吧。”
收纸人绕过我,同老爹进屋去了。
房子里很暗,收纸人的脸始终向着墙壁,所以我一直没看清他的表情。奇怪的是,他和老爹并不谈起卖纸的事情,而是在说“阿拉玛斯玉矿”、“羊皮图纸”、“失踪”等这些古怪的词。
他好像还说到了“像老爹你,当年做了这么多年的向导,熟悉阿拉玛斯矿的矿脉,什么都见过了”,话说得断断续续的。
最后,这个卖纸人还提到了钱,说是“事成之后,你会得到补偿的,会是一大笔钱”。
老爹在一旁只是“嗯嗯”地应和着,好像并不与他多说什么,也不发表什么意见。
最后,老爹拖长声音“哦”了一声,就再也不说话了。
收纸人走后,我总是找机会拐弯抹角地同老爹谈起收纸人来访的事,而老爹总是显得不耐烦,说我不懂。
真让我灰心。
有那么几天,我很难集中精力跟着老爹学做桑皮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