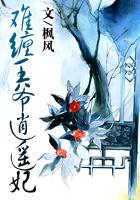十一点钟,船靠了岸,一上岸便是安江镇。安江镇是黔阳县所在地,一条主街非常热闹,有点小城市的味道。当地人曾称它为“小南京”。据说它曾经是黔阳地区的州府。它之所以没得到发展,是它没挨近铁路。倘若它挨近铁路,也许怀化市就叫黔阳市了。两人一上岸,迎接他们的是一辆辆改装的三轮摩托车,那些车主都用拉客的眼神瞧着他们,问他们要不要车。两人上了一辆摩托,驾驶摩托的男人便问他们去哪里。史斌说:去一家好点的宾馆,安江有宾馆吗?
有,有白云宾馆。开摩托的男人说。
从河里上岸,感觉较热。汉林问骑摩托的男人:宾馆里有空调吗?
有空调。
所谓白云宾馆也就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挨着黔阳县电影院,也许此前它不过是电影院的一部分。外墙贴着土黄色瓷砖,有几处地方的瓷砖已掉了;门窗是茶色铝合金玻璃门窗;白云宾馆是四个大红色的方块字,镶在正面墙上。两人提着旅行袋走进去时,感觉不到空调的凉气,感觉到的是一种闷热。汉林走上去开房,问服务员道:房间有空调吗?我们要住有空调的房间。
有窗式空调,服务员回答。
一问双人间的房价,只要六十元。汉林吃了一惊,居然这么便宜。一步入房间,汉林就不觉奇怪了,因为室内很简陋,除了窗户上安着一台空调,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可以入眼。汉林放下包,服务员把空调打开,嗡嗡嗡的强有力的噪声便在窗户上振荡开来。将就点吧,史斌瞥一眼汉林说,也就是六十元住一晚的场合。
空调的噪声嗡嗡嗡地响着,好像故意跟他们过不去。汉林皱了皱眉头,心想要换地方又担心史斌说他什么,史斌把他看成了一个吃不了苦的大少爷。汉林宁可不当少爷,就躺到铺上,伸了伸懒腰。史斌到卫生间小便,强有力的撒尿声冲进了他的耳鼓。史斌这小子实在太生猛了,真的是一个土匪,他想。史斌小便完走出来,嘴里叼着烟,边系着裤拉链。走吧,出去看看吧?他对汉林说。
歇下吧,又不是来救火的。汉林说。
史斌就坐到铺上,接着又躺下,习惯性质地骂了句痞话。男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朋友,就会很寂寞。史斌说,我就最怕寂寞了。
史斌跷着二郎腿,抽着烟,一张宽脸上就烟雾缭绕。空调在窗户上滋滋滋地响着,那是压缩机和窗玻璃共振的声音。街上,一首儿歌传来,不知是谁家店铺有意把音响开到最大的程度,以此吸引顾客。史斌偏过头来望着汉林,继续他的理论:我觉得人年纪越大,思想就越坏。童年是无邪的,既没野心,也不会去害人。但人一长大了,权力啊利益啊欲望啊就都有了。
人人都想活得好一点,都想占有更多的物质。人的需求心理总是向上走,一个目标实现了,新的目标就诞生了。汉林说。我们公司有一个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姓马,他原来住着两室一厅,后来住上了四室两厅两卫房。早一向他对我说,四室两厅的房子还是小了,儿子住一间,保姆住一间,一间书房和一间他和他老婆睡的主卧室,而他的父母来了,就得睡书房,而他的大部分东西都丢在书房里,因此他晚上做不得事。所以他觉得四室两厅还是小了。你要晓得马副董原来住的两室一厅,使用面积只有四十个平方,而他在两室一厅里住了十年。现在他住的四室两厅两卫,建筑面积有一百六十多个平方,马副董只是住了不到两年就嫌小了,就想别墅了。人都是这样,上了一个台阶就想上更高的台阶。欲望是无止尽的。人永远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
就是。史斌说。
人最好的是需要一个好身体,身体好比什么都好。汉林说。我老爹有个朋友,也很有钱,也是房地产老板。他虽然没我老爹有钱,但至少有六七千万资产。他想破脑壳地挣钱,点子很多,然而当他很得意的时候他得了脑癌,没救了,上个月死的。所以挣了钱有什么用?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说什么都是假的,身体才是真的。史斌这么觉得说。看来第一件事是把身体搞好,第二件事才是赚钱,很多人因赚钱而不要命,结果白赚了。
两人走出房间,走到了街上。安江镇街上比巫江镇街上多了几栋漂亮宾馆,比如长城宾馆、黔阳宾馆、邮电宾馆和青山宾馆。这些宾馆都是新建的,在县城街上很打眼,给这条主要街道增色不少。感觉上,安江比巫江镇要繁华一点。两人在街上走了一圈,沿路看了看,新鲜感觉满足后,这才走进街头的一家饭店。饭店一旁很热闹,有音响和电视机摆在街上,还有一张张折叠椅和小圆桌摆在人行道上,一些年轻人正在街上唱卡拉OK。这又和巫江镇差不多。汉林从饭店里走出来,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冲着电视机唱《万水千山总是情》,居然用粤语唱,听上去还有点那么回事。汉林禁不住多打量了她一眼,这一打量,汉林暗暗一惊,这姑娘挺漂亮的,有点像去年他在深圳见到的那个姑娘。当然,这姑娘并不是他在深圳见到的那个女人。这个世界说穿了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世界。汉林想,你可以说我不要女人,但那只是说说罢了,内心里你却被女人吸引着。理智总是在抵制女人,但情感却总是向女人呼啸着奔去。
女人穿着白短袖夏衫和一条白短裙,胸脯很高傲地凸起,把绣着荷叶边领子的衬衣撑得老高,屁股极为圆润好看,因而很有线条;脚上一双白高跟凉鞋,一双肉色丝袜裹着她很美的腿。汉林惊诧了,盯着她,想这样的小县城竟有这么靓丽的姑娘,太浪费了。她唱得很投入,声音也相当好听。汉林真的觉得她很美。与冯丽分手五年了,他第二次感到了另一个女人的魅力。冯丽在他心里占据的地盘太大了,以致他这几年不思女人就像病人不思茶饭样,甚至对张红约他晚上喝茶他都用借口拒绝。这个姑娘唱得不错,史斌对他说,长相也不错。
女人唱完歌,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旁边坐着另一个姑娘,那个姑娘脸上的妆化得太艳了,以致你觉得她身上有太多的妖气。女人感觉到了汉林和史斌在打量她,偏过头来看了他俩一眼,又扭开脸一笑,对那个姑娘说:你的歌出来了,快唱。
姑娘唱歌时,饭店的小姑娘走上来说:菜上桌了,你们喝酒吗?
汉林表示不喝酒,史斌也说不喝酒,两人走入店堂,看到有苍蝇围绕着桌子飞舞,汉林伸手赶了赶苍蝇,坐下。这个妹子长得有味,啊。史斌又说。
是的。汉林说,夹了点腊肉放到嘴里噍着。
我觉得男人不要过多地把感情投放在女人身上,那是很不值的。在我们湘西,甚至就是早几年,女人是不能上桌的。男人在堂屋里吃饭,女人在厨房里吃饭,区别很大。哪里像你们长沙,女人比男人还有脾气。你不能跟女人讲交情,女人身上是没有义气二字的。我的一个朋友曾说女人是政治的化身,变幻莫测的,而且很无情。
汉林望史斌一眼,觉得把政治和女人连接起来是很形象的。汉林说:你的朋友说得对,政治是女性化的,是阴柔的,以柔克刚。政治绝对不能阳刚,它一阳刚立即就会制造混乱,制造对立面,从而导致战争。
战争是男人制造的,史斌对这个世界充满征服欲地说,男人都有征服欲。
一个男人如果要从政,他必须首先女性化。必须打太极拳。如果他打的是少林拳,硬碰硬,他会遭至很多反对。他会感到他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试想想,如果你想一步登天,有人会把你绊倒,让你跌得鼻青脸肿。如果你像女人一样,缓缓朝前走,不急着达到目的,别人就会赏识你。认为你“稳”。稳是极女性化的。
史斌说:我有个高中同学跟他的女友好了四年,不短吧?但最近被他的女朋友抛弃了。他的女朋友比他混得好就嫌弃他了,他痛苦得要死。
汉林继续着自己的话题说:你要从政,你就得丢掉男人的特征。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雌,阴柔也。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这些句子中就包容着女性哲学,这对从政的人太重要了。
我讨厌从政,政客都像女人一样冷酷无情,自己没混出地位来时就像三陪小姐样低三下四,一旦出人头地了就把老朋友抛弃了。史斌说。
史斌的话让汉林联想到了冯丽,是啊,女人比男人更狠心。
我那个男同学开始并不比他的女朋友差,史斌说,他其实对他女朋友很好,什么都依他女朋友的。他女朋友要这样他绝不那样,他生怕他的女朋友生气,生怕他的女朋友不高兴。去年他的女友调到我们怀化电视台工作,当记者,今年又改做了节目主持,工资高了,见的男人多了,就开始疏远我同学了。我同学痛苦得要死。
汉林想起冯丽抛弃他时,他也痛苦得要死。这种感情我最能体会了。
史斌不屑道:她对我同学说她其实一点也不爱他,她从来就没爱过他。这是讲什么话?不爱他,她会同他睡觉?他们同居了几年,只是现在有了差别,假如是我同学混好了,而她没混好,我相信她会说她一直很爱他。
地位变了,爱就转换了。汉林说,脑海里既出现了冯丽,又出现了美国人罗伯特。她一定爱上了比她男朋友更强的男人。女人么,不是个个都本分的,不然就不会有水性杨花这样的词语诞生。冯丽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史斌听汉林提到冯丽,脸上就冒酸气,冯丽骚不骚?
汉林说:骚得不行,超骚。
史斌遗憾的模样叹口气,可惜她被美国人弄走了,不然……
不然什么?汉林说,摇下头,我可以告诉你,冯丽那样的女人,就算不跟我好,你也是睡不到的,她很势利,是长沙这座城市里长大的小市民,又长得漂亮,那还不狗眼看人低?当年我之所以吸引她,是她知道我家里有钱。这一点我比你清楚。
那个美国人家里有钱吗?史斌感兴趣地问。
汉林说:这我不知道,我没问她。吸引她的除了罗伯特,我想还有美国本身。
吃过饭,两人走出饭店,那个唱歌的女人已离开了此地。汉林有一种丢失了什么东西的感觉,就有点小遗憾似的,两人在街上缓缓地转了圈,还是不见那女人的踪影,于是两人折回白云宾馆休息。空调像一台机床在窗房上工作,那种噪音很让人烦躁。汉林点上支烟,躺到铺上等待睡眠降临。在等待睡眠控制大脑的那片刻里,他居然在这个陌生的县城里想起了张红,想起了她那张力求要把他从疲遢中拯救出来的脸。才出来几天啊?怎么她就钻进了我脑海?而且于这一刻突然就变得很亲切了,一张脸竟然清晰可见似的。他想,懵然觉得这张脸很占据他的脑海,使他平静的脑海涨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