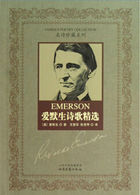我岳父李雁城自从和那个蔡先生相识后,脑袋就出问题了。他对安徽兵炸门抢劫有他的看法,认为中国太无政府主义了,什么人拉了支军队就可以为患百姓,明打明抢,这样的国家是不是烂到骨头里了?次日,他于晨曦中对李雁军说:“哥,我们中国难道要这么乱一世?”李雁军恰好相反,他是个不关心时局的人,他没有堂弟那么大的心,目光也没堂弟那么刁钻,他满足于习武、吃饭、做事和睡觉,这种简单明了的生活让他安宁。他淡淡地说:“这我怎么晓得?”我岳父把蔡先生的话传给李雁军听:“我们中国人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这是最要不得的,这也是军阀们可以任意欺压老百姓的原因。”他看一眼一旁的开得红灿灿的美人蕉,又说:“哥,有一位蔡先生对我说,只有把贫穷、落后的中国砸烂,重铸一个新中国,中国才有救。”李雁军揉揉站桩站酸了的腿说:“你不要信这些话。”我岳父瞟一眼睡眼惺忪的我大叔,我大叔刚起床,一屁股坐到葡萄藤下,一双大脚伸到我岳父的眼皮下,我岳父说:“蔡先生说如今的中国,谁手上有枪谁就是王,你看张敬尧,当了我们湖南的最高长官,不但不安抚老百姓,还纵容他的官兵公开抢老百姓的财物和打老百姓,这老百姓能生活下去?”
我大叔很瘦,一张脸很白净,太阳可以把这个人晒黑,把那个人的脸晒成锅粑色,太阳却没法把我大叔何金江的脸晒黑,尽管他每天上学都来来回回地在太阳下闲逛。我大叔的脑海里装着许多中国的未来,这都是肖先生在教室里宣讲的。他听我岳父这么说,就觉得太对了而嘿嘿嘿笑,边望着我岳父说:“我们老师要我们把书读好,长大了好报效国家。”早晨的太阳有点耀眼,我岳父把目光投到我大叔的脚上,心里嘀咕“二少爷的脚真大”,却表扬我大叔说:“你们老师说得好。”我大叔正要说什么,忽然有枪声传来,一片激烈的枪声,不知哪里又在打仗!奶奶慌忙从厨房跑来,警告大家:“今天都不要出门。”
一家人就坐在堂屋里,眼睛盯着葡萄架上的葡萄,还盯着含有火药味的阳光,那阳光黄中带红,以致墙角的美人蕉开得都笑了,不断地摇晃。李雁军坐在一隅不说话,爷爷也锁着眉头不说话,我岳父却说个不停,把他从蔡先生那里获得的与时局相关的信息,用蔡先生那种忧国忧民的语气说出来:“北平现在很乱,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军阀,谁都不听谁的。东北有个张作霖,手中有十几万军队就我行我素。孙中山的国民党在广东搞自己的一套,中国现在四分五裂呢。”我大叔耳朵奇大,听力和分辨是非的能力也强,他一听这些话就心潮澎湃地攥着拳头问我岳父:“雁城哥,你说现在中国该怎么办?”我岳父说:“要变,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岳父说着,一拳击在自己腿上。街上还有枪声,一会儿激烈,一会儿又变成零零星星的,一会儿又大作起来。过了中午,街上安静了,只有苍白的阳光涂在墙壁上。
奶奶叫上李雁军,想去菜市场打个转身。路上,只见街上到处是军人,一个个横端着枪,目光都跟恶狗样不信任地瞪着人。奶奶的腿软了,又和李雁军折回家。奶奶对爷爷说:“到处都是端枪的军人,长沙怕是要打大仗了。”傍晚,我岳父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在饭桌上宣布说:“中国又换总统了,新总统叫徐世昌。”奶奶放下碗筷说:“不会为这个新总统又打仗吧?”我岳父说:“蔡先生说这是国会选出来的新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