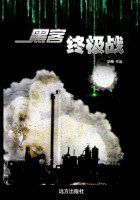李文军在《长沙晚报》上登了一则启事,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原国民党湖南新编第一军将于八月十五日上午在黄土岭交通学院大门前聚会,请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们见报后相互转告。原军长何金山。这则启事登在报缝中,原有三百多字,被报社编辑压缩成七十个字和四个标点符号。李文军看到这则启事后很气愤,三百多字被压缩成一句话,而且还是登在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的报缝中,却花了他一千块钱,他恨不得把那一千块钱要回来。他把报纸甩在地上,还不解恨地跺两脚,“我绞尽脑汁写的三百五十个字的启事,被这帮编辑剪成一句话,还要我一千块钱,真不是人。”
李文军写的稿子我看了,还替他改了三个字,没想所费的脑细胞都是多余的。我说:“要知道能让你登出来就已经是进步了,以前,这样的启事,谁敢登。”李文军说:“血战台儿庄都拍成电影公演了,这不是证明我们国民党军队抗过日么?”李文军阴着脸,嘴唇都气乌了。这一天是八月七日,是个阴天。李文军望着阴沉沉的天空,那张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变深刻变愤恨了。我知道他心里不舒服,他的眼睛里有两团火,仿佛他的心在燃烧。“为什么对我们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事就那么忌讳呢?”李文军生气道,“长沙的四次会战和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难道不是我们打的?”我说:“你经历了这么多,应该能想通一切。”李文军苦皱着脸道:“死了那么多人就白死了?他们的亡灵能安息?”他的思想在往事里飘,那是战火纷飞的往事,当时他才二十岁,正是那种甘洒热血的神勇的年龄。
八月十五日上午,很多原国民党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都冲着我爹来了。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是自己搭公共汽车来的,身体差点的就坐的士,还有的是儿子或孙子辈骑摩托车或开车送来的。爹在等李文军,李文军还没到,有人却先来了,站在青山街三号门前张望和打听,有的老人还穿着原国军黄呢军服,只是军服很旧了,估计是从箱子里翻出来,见还没被虫蛀烂,就果断地穿上了。他们看见我爹着一身青衣,就激动,握着我爹的手,望着我爹那双苍老的皱纹打裰的眼睛,尊称我爹“老军长”。爹听不见,只是咧嘴笑,同他的老部下一一握手。他们当年握枪的手,都很有力,久久地握着。我对他们解释说:“我爹听不见,耳朵聋了。”他们就握着我爹的手大声叫嚷“我叫某某某”,爹因听不见就一脸茫然和抱歉。李文军和姜小工一进来,他们就相互报姓名和师团番号、军职,热闹一番后,三十几个老兵拥着我爹出门,走到大街上,上了一辆辆的士。
我爹他们赶到时,黄土岭上,交通学院的大门前已站了一百多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很精神,穿着衬衣或体恤衫,昂首挺胸;有的委靡不顿,穿得也很随便,斜着目光浑浊的眼睛,瞪着从车上下来的我爹、李文军和姜小工。他们曾经在一起打日本鬼子,在一个连里训练、吃饭、睡觉,探讨打鬼子的心得,亲得不能再亲了,但如今老得相互都认不出了。李文军穿一件长袖黑衬衫,下身一条白裤子,染成黑色的头发打了发胶,一根根的,脸刮得很干净,看上去就精神矍烁。他向走来的老人介绍我爹说:“弟兄们,何军长来了。”那些老兵一听“何军长”来了,立即振奋地拥上来,围着我爹。有个年轻点的老人向我爹敬军礼说:“报告军长,我是湖南新编第一军二师三团三营一连一排排长,马笑天。”另一老兵见状,也不示弱地向我爹敬军礼说:“报告军长,我是一师一团二营营长刘元。”那老头见我爹只是愕然和微笑,就奇怪,李文军忙解释:“何军长耳朵不好,听不见。”那老头就哦一声。又有人向我爹报告,说他是团长某某某。李文军摇手说:“算了算了,老军长耳朵听不见,你们说什么他都不知道。”跟着又走来一些老人,他们都是看了报纸或听别人说到这事,就相邀着来的。到十一点钟,已来了两百多名原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
前师参谋长姜小工的大儿子在黄土岭上开了家粉店,取名利民粉店,就在黄土岭与金盆岭交界的路旁,五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阻击日本侵略军进犯长沙的重要阵地。那时候日军从南边包抄杀来,想攻占长沙就必须攻克黄土岭、金盆岭和雨花亭,当年这些老兵就奉命坚守在这一带,一次又一次地把日本鬼子打得哇哇大叫和绝望撤离。他们故地重游,感触颇深。今天的黄土岭、金盆岭和雨花亭当然不是五十多年前的样子,到处是工厂和学校,那时候这里是山坡和树木,还有军营、工事和被飞机大炮炸松的土堆。他们在这里练兵,出操、跑步。那些生龙活虎的喊杀声、为加强体能锻炼的跑步声和怒吼的歌声,似乎从五十多年前涌来了,潮水一般打着他们,使他们无处逃遁而感慨万千。那时他们真年轻,与日本侵略军寸土必争地拚杀,勇猛如豹,端着枪冲下山坡跟箭一样快,刺刀直插入日军的心脏。如今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连多走几步都喘不赢气了。一老兵对我爹和李文军说:“我们这代人该入土了。”爹笑,李文军却说:“我们要好好活着。”另一老兵说:“师长,我这个原国民党营长的身份,害得我一直抬不起头,刚刚觉得日子好过一点,老伴又死了。”又一老兵说:“我倒无所谓,我这国民党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把我女儿害惨了,一九六四年她被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到江永当知青,如今还留在那里。”姜小工问:“还在那里?”那老兵答:“死在那里啊。”走在李文军一旁的瘦老头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身份确实把我们的子女害得抬不起头。”姜小工说:“是啊,我儿子那时候连街办工厂都进不了。”另一当过营长的老兵点点头,“别的都无所谓,我们最对不起的是我们的儿女,他们因我们吃了很多苦。”
李文军没有儿女,感受不到这种深层次的痛,见大家一谈到儿女,那种热烈的气氛顿时冷却下来,个个一脸负罪感,忙大声说:“我们都要这样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总算过去了。”一个瘦老头情绪低落地说:“永远也不会过去,我们的儿女们背着呢,他们因为我们,如今还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姜小工说:“是啊,我们是对不起我们的子女。但是老天爷让我们活到今天,是对我们的怜悯和欣赏——”他说到这里,激动了,“怜悯我们、欣赏我们,因为当年我们是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士,打日本鬼子时,我们没给中国人丢脸。”李文军对姜小工竖起大拇指,“姜小工说得好,抗日战争中,我们湖南人没丢中国人的脸。”
利民粉店容不下两百多老人,大部分老人都坐在粉店外的树荫处或路边,边等粉吃边相互诉说衷肠。利民粉店事先已准备了很多粉,下粉的师傅很勤奋地一碗碗下着。前师参谋长姜小工很兴奋地走来走去,边说:“别的我招待不起,一碗粉还是有的。”大家说:“够了,谢了。”有人要付钱给姜小工,姜小工拒绝说:“你这是不给我老脸啊。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弟兄们难得一聚,这碗粉我请了。”大家就笑,粉就吃得特香。一个老头曾经是姜参谋长当营长时的传令兵,他说:“当年我们姜营长可真是条好汉,有次他跟日本兵拚刺刀,一连捅死两个日本鬼子。”另一老兵说:“我最记得我们营长,我亲眼看见我们营长一枪一个,接连击毙七八个日本鬼子。”另一老兵猜到了,问:“你说的是何胜武营长吧?”那老兵回答:“就是何胜武营长。”姜小工说:“何胜武营长死了好几年了。”那老兵问:“他死死了?”姜小工看一眼坐在远处的我爹说:“死了。”那老兵说:“前一向我还梦见过何营长。”另一老兵回忆打日本鬼子说:“我记得我第一次瞄准日本鬼子时,总是打不中,日本鬼子都冲到面前来了,我才一枪把那家伙打倒。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怕日本鬼子了。”有个老兵把碗里最后一点汤也喝了,放下碗,手指着前面的山丘,“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攻长沙时,我就守在那里,那时候这里都是山坡和树林。”又一老兵接过粉,说:“我是一九四一年的兵,家住燕子岭,我记得我们师长叫贺新武,我当过他的警卫,他对全师的官兵训话时说:‘日本鬼子是豺狼,绝不能让狗日的豺狼踏入长沙半步。’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第二次进攻长沙,硬是没有从我们师守的阵地上过。”李文军告诉贺新武的前警卫:“贺师长五年前死了。”那老兵脸色变灰了,“我这一辈子最尊敬的人是贺师长,前一向我还跟孙子说起他。”这老人八十多岁,一九四九年湖南新编第一军接受解放军改编时,他是中校副团长。
大家边吃粉边述旧,谈得很热烈。吃过粉,已是两点多钟,然而这些老兵仍依依不舍,相互倾述,说自己的事说家里的事说过去与日本鬼子打仗的事,以致一些路人见一大群老人坐在利民粉店前叽叽咕咕,都十分吃惊,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三点多钟,一些老人才相互话别,有的老人邀请别的多年不见的老人上家里去吃晚饭和继续聊,有的要回家了,因为儿子骑着摩托车来接了。一些老人就走过来向我爹告别,握着我爹的手不放,我爹就坚持着站起身,望着他们。那些老兵对我爹大声说:“老军长,多保重。”爹听不见,只是点头,目送着一个个老部下离去。四点来钟,两百多老人走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特别敬重我爹的要等我爹走了才肯离开,他们这几个人的脸色都很坚定,表情也十分庄严,一看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爹倦了,一张槐树皮样皱巴巴的脸上就有很多疲惫,犹如屋上爬满枯藤。爹问李文军:“我们走吧?”李文军就去拦的士,一辆夏利的士驶到爹面前,姜小工老人忙扶我爹上车,爹探出头,伸手对他的老部下说:“你们回家吧。”那几个老人忙与老军长挥手告别。汽车很快驶到青山街三号,爹下车,从门外进来,稀薄的头发就凌乱,脸色也困倦,我上去搀扶。爹在躺椅上坐下,喝口碧螺春茶,闭上眼睛就睡着了,头歪着,嘴张开,一溜涎水从他那张皱纹重叠的嘴角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