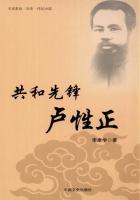含辛茹苦、辛苦的始祖母,养育精英,开拓领地,告别小种时代。
一、劳苦功高
20万年的四季寒暑,轮回氤氲了千秋万代的生灵;20万年的休生养息,积聚蕴蓄了万代千秋的活力。当时光流逝到70万年前时,古老的秦岭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北坡是40公里的陡峭。短小的沟谷,升升降降;笔直的河流,忽高忽低;天降的瀑布,飞泻直下;湍急的黑河、沣河、灞河,直灌渭河;险峻的断岩峭崖,撞进渭河平原。
南坡是100公里的舒缓。一层层的夷平面,像一道道的涟漪,越过绵延起伏的丘陵,沿着弯弯曲曲的褒河、子午河、金钱河,融进了浩荡的汉江和辽阔的汉江平原。
天地的造化实在令人震惊。但是,我们们最关心的还是在这天地重构中,那些天神的后代。他们还在南坡吗?还是黑白相间吗?特别是花耳朵家族,还是最威风最有魅力吗?
在高企的太白主峰,有雪蚀洼地,乱石流滩,高山草甸。
在海拔3000米的亚高山,有山峰林立,陡岩深谷,成片的落叶松、云杉、雪杉树林。
在海拔2500米的中山,是山峦跌宕,河谷宽阔,在针叶林和阔叶林的混合中,跑动着黑熊、狼、毛冠鹿、苏门羚……
在海拔1800米的低山,有沟谷发育,山梁起伏,遮天蔽日的阔叶树林。
顺着弯曲的河流,透过蓝色的山岚,来到平缓的山脚,就有了剑齿象、剑齿虎、金丝猴、中国犀……
啊,终于看见了,一只雌性的大熊猫,正从密林中出来。
还是黑白相间,还是庄重神奇,还是身长一米。耳朵上还是有两柄白色的竹叶,俏丽独特威风凛凛。
不过,比起当年的祖先,她的神态少了俏皮和好奇,多了凝重和庄严。她的步子少了坚定和敏捷,多了温柔和飘逸。
也难怪,这是一位刚刚分娩的母亲,而且是这座大山里最辛苦的始祖母。别的母亲一年只生两只幼仔,最多三个。她却每年都会超生。去年是六个,还没有独立,今年又是四个,正嗷嗷待哺。
或许是花耳朵家族需要更多的后代?或许是新生的种群需要迅速地壮大?不知道。既然把他们生了下来,就得尽心尽力,让他们健康成长,让他们出类拔萃,就得比别的母亲更辛苦。
秋天的秦岭,是天空的清澈透明,是山林的五彩缤纷,是果实的争奇斗艳,是飞鸟啼不完的长调,是走兽吃不完的盛宴。也正因为如此,300万年前的大熊猫始祖母,才会把分娩的时候选在秋天,并让她的后代延续到永远。
温暖的阳光,凉爽的秋风,清新的空气,赏心悦目的山林。走着走着,辛苦的始祖母就抛弃了产后的虚弱,变得精神抖擞起来。不过,她还是走得很慢,左顾右盼,寻觅着猎物。
始祖母扬起头,眯起眼睛看看阳光,她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天没出山洞,没见阳光,没吃东西了。
产前是妊娠反应,难过得昏天黑地,吃不下东西。生产是阵阵剧痛,痛苦得死去活来。产后又是欣喜,是爱抚,是哺育,是难舍难离。
如今,她终于离开了,出来了,也是因为仅仅靠她的奶水,再难维持10个孩子的发育。
一蔓缠来绕去的野大豆,绊住了始祖母的脚步,一个个狭长的豆荚,被着黄褐色的硬毛,在秋风中摇响风铃。
辛苦的始祖母坐到地上,揪下一个豆荚,放进嘴里。犬齿一碰,豆荚裂开,蹦出黑色的豆粒,舌头一卷,臼齿开合,就发出“卡崩卡崩”的咀嚼声。
分娩的辛苦,哺育的劳累,都在这一刻释放成快乐的音符,在山谷里回响。
一抬头,一棵高大的香果树,挂着满树的果实,红艳艳的,晶莹剔透,又钩住了始祖母的眼睛。她站起来,走过去,抱住树干,三下两下,就像山间浮起的云朵,转眼就坐到了树杈上。伸出手,揪下一颗果实,放进嘴里,犬齿一碰,臼齿开合,就又有了“吧嗒吧嗒”的香甜和惬意。
远处的山崖上,一只健壮的大熊猫昂首站立,耀武扬威地发出一声长啸。辛苦的始祖母举目眺望,也发出一声回应。那也是她的花耳朵后代呀,在向远方的母亲发来信息。
在这座大山里,辛苦的始祖母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后代,她只是不停地生啊养啊,孩子们长大了,离开了,独立了,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了,都是用长长的呼啸,告诉他们的母亲。
现在,山崖上的长啸还没落地,四面八方的密林里,又有了此起彼伏的交响回应。始祖母听得出,这都是她的儿女,那声音里有着花耳朵家族的健壮,威武和自信。
这就是辛苦的回报,这就是家族的壮大,这就是种群的希望。
一阵山风吹来,几片红黄色的香果树叶飘飘扬扬地落下。辛苦的始祖母也像一团云雾似地从树干上降落。显然,那些香脆的野大豆,那些香甜的红香果,都只是她的开胃甜品。她得赶紧为自己,也为山洞里那10个儿女寻找食物。
一只棕黄色的毛冠鹿从杂木林里跑出来,张着枝桠的鹿角,没头没脑地撞上了始祖母。
辛苦的始祖母被撞疼了,但没有发怒,定定地看着他,仿佛在谴责他的冒失。
毛冠鹿吓坏了,一声尖叫,两眼惊慌,夺路而逃。
但是,晚了。辛苦的始祖母像云一样腾起,像山一样压下,那只活蹦乱跳的毛冠鹿就成了一摊黄泥。
就在这时,一个庞然大物从密林中走出来,铁灰色的身体五米长三米高,像一堵墙。乳白色的长牙伸出来,足有两米,像两把剑。还有一根三米长的鼻子甩来甩去,所向披靡。这就是剑齿象,还是一只成年雄性。
剑齿象在辛苦的始祖母面前站住了,等着她让路。
辛苦的始祖母没抬头,也不理他,开始撕扯猎物。
剑齿象不耐烦了,发出低沉的威胁声。
辛苦的始祖母还是不抬头,继续撕扯她的猎物。
接下来,一场逗趣开始了。剑齿象用鼻子去甩,始祖母把脑袋一歪。剑齿象用剑齿去戳,始祖母往后一闪。最后,剑齿象把擎天柱似的腿抬起来要踏,始祖母就叼起猎物,一溜烟地上了香果树,继续享用她的美味大餐。
剑齿象恼羞成怒了,来到香果树下,用脑门撞击树干:一下,两下,三下……
香果树支撑不住了,盘根错节的树根从土壤里暴露出来,粗壮高大的树干向地面歪斜倾倒。这么一来,树杈上的始祖母也坐不稳了,不得不趴下来,用前臂抱住树枝,用牙齿叼住猎物。
在一次猛烈的撞击中,毛冠鹿被悬空吊起,晃来晃去,敲打着剑齿象的脑瓜顶。
剑齿象发出一声怒吼,更加用力地撞击。
但是,香果树倾斜到45度时,就再也不肯倒下了。辛苦的始祖母趁机挪到高处,稳稳当当地坐下,重新撕扯猎物。鲜红的血滴下来,落到剑齿象的头上、身上。
剑齿象发狂了,抬起比树干还要粗壮的腿,朝香果树踏去。
香果树撑不住了,发出一声霹雳绝响,齐根断裂。
粗壮的树干,茂密的枝叶,连同鲜红的果实,划过蔚蓝的天空,缓缓地倒下来,拉扯着身边的小树,覆盖了脚下的灌木。
尘埃落定,剑齿象仍余怒未消。走过去,寻找着发泄的对象。
红红绿绿的枝叶下,露出一个鲜血淋漓的鹿头,睁着一双僵死的眼睛。
剑齿象抬起腿,就是一阵践踏。可怜的毛冠鹿,就和绿色的叶、红色的果、黄色的泥土融在了一起。
辛苦的始祖母呢?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哪里去了?
剑齿象也在寻觅。不过,他很快就被香果树的果实诱惑了,甩动长长的鼻子,卷起一串果实送进嘴里。
他的鼻尖上有一个圆圆的小球,像一朵铁灰色的绣球花,在长鼻的甩动中,格外惹眼生动。不错,像花耳朵家族一样,剑齿象圆鼻头家族,也有着自己的特征。
就在雄象圆鼻头大快朵颐的时候,辛苦的始祖母也有了新的收获。她正叼着一头猎物,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那是一头半死的野猪,耷拉着脑袋,不时挣扎一下,哼哼一声。
在山崖边的小溪旁,辛苦的始祖母站住了,竖起耳朵听。
小溪对岸,林中的草坪上,一只黑鹿在低着头吃草。“唰唰唰”的咀嚼声,传来他的专心和满足。
辛苦的始祖母来到山崖下,放下野猪。转过头去看黑鹿。
黑鹿仍然低着头,仍然传来“唰唰唰”的吃草声。
一道黑白相间的彩虹,腾过小溪,直奔黑鹿。
黑鹿终于惊觉了,立刻腾空而起,四蹄生风,钻进了森林。
茂密的林子,高低的灌木,掩护了黑鹿的身影。但是,窸窣的响声,折断的树枝,又指引了始祖母的追踪。
突然,像崩断的琴弦,一切都静止了。没有了奔跑,没有了窸窣,也没有了黑鹿。
辛苦的始祖母也停住脚步,屏息静听,像一块黑白相间的石头。
一丛灌木中,“扑啦啦”地飞起一只五彩斑斓的野鸡。黑白相间的石头立即复活,腾空而起。消遁的黑鹿也立即显形,四蹄生风。
眼看就要抓住了,一根粗壮的藤子把始祖母绊了个跟头。爬起来时,黑鹿又一次消声匿迹,只听见落叶的簌簌声。
辛苦的始祖母原地转了一圈,看定那根可恶的藤子,扯过来,放进嘴里,“咔嚓”一声就咬下一截。然后回头,转身,悻悻地消失在密林里。
秋风乍起,秋虫鸣唱,秋草劲舞,天下太平。匍匐在灌木后边的黑鹿也走了出来,伸伸腿,摇摇颈,在一片尚未枯黄的草地上,轻快地蹦跳,尽情地欢呼:
活着真好!生命真好!
就在这时,一道无声的闪电,从天而降,攫住了黑鹿的咽喉。
弱肉强食,天真机警,在这一刻都见了分晓。
没有挣扎,没有哀鸣,黑鹿瘫倒在地,束手待毙。
没有得意,没有停留,辛苦的始祖母叼起黑鹿就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像云一样腾。在茂密的森林中,像风一样钻。
山洞里的儿女在呼唤,在期盼,在嗷嗷待哺!
回到小溪旁的密林边,始祖母突然站住了,放下黑鹿,转动头颈,目光灼灼,盯着对岸。
对岸的密林里,一只饥饿的鬣狗,钻出来,四处嗅,很快就发现了目标。直着眼,撒开腿,就找到了始祖母存放的猎物。
鬣狗得意地哼了一声,居然有这样的好运气,好大一头猎物!
山崖下的野猪一动不动,他的眼睛被鲜血糊住了,看不见生的希望,也看不见死的阴影。
饥饿的鬣狗来到野猪身后,伸出尖长的嘴,照着屁股就是一口。
“嗷--”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震撼了森林,撕裂了天空。
鬣狗屁滚尿流,滚出一丈远,惊恐地看着野猪,看着四周。 野猪一动不动,四周静寂无声,那尖叫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鬣狗吐掉一撮猪毛,在草丛里蹭了蹭嘴。仿佛要把嘴巴磨得更尖利更干净。凭个头,鬣狗比野猪略逊一筹,比拼打鬣狗更不是野猪的对手,但如果是一只死野猪,那就又当别论了。
鬣狗转动着滴溜溜的眼睛,犹豫着,琢磨着:这野猪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是活的还是死的?或者是半死半活的?摇头晃脑,鬼鬼祟祟,那样子,实在让人捧腹。
溪水在匆匆赶路,唱着欢乐的歌。树叶在慢慢摇曳,跳着轻松的舞。
野猪还是一动不动,屁股上的猪毛又粗又硬,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一条小青蛇像一根水柱,从山崖上掉下来,在野猪的身上盘桓一阵,又钻进了草丛。
一只小黄雀像一片树叶,从林子飞出来,在野猪的头上舞蹈一番,又飞上了天空。
看样子,那野猪真的是死了。
鬣狗开始行动了,蹑手蹑足,小心翼翼。在两米远,试探性地叫一声,没动静。在靠近时,伸出腿,迅速地捅一下,扭头就跑。
十米开外,是失魂落魄的鬣狗,在观察动静。
山崖下边,是棕毛倒立的野猪,还是一动不动。
树上,一只花翎山雀,一边翘动尾巴一边嘀啾,好像在嘲笑。
远山,一只剑齿虎的长吼,在山谷里回荡,似乎在催促。
鬣狗咕噜了一阵,终于下定决心,迈着坚定的步子,伸出锋利的尖嘴,照着野猪的屁股狠狠咬去。
“嗷--”
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却不再是野猪的独嚎,又掺进了鬣狗的和声。
是辛苦的始祖母,在鬣狗咬住野猪屁股的同时,她也咬住了鬣狗的屁股!
痛苦不堪的鬣狗放开野猪,一扭头,就看见两道黑色的闪电,六把雪亮的利剑。
鬣狗一阵眼晕,还想逃跑。可哪里跑得掉?除非卸掉屁股。
始祖母脑袋一甩,鬣狗的屁股就下来一半,连同一条腿。
得,这回别说逃跑,爬都爬不动了。
倒霉的鬣狗,偷食不成反成了食物。
辛苦的始祖母,一个上午,马不停蹄,竟得了三个猎物。
剩下的问题是搬运,尽管是秦岭上的庞然大物,可三个猎物加起来,还是比始祖母大得多。
要是她能直立起来,要是她能背一个抱一个叼一个,要是……
你还别说,始祖母真的直立起来了。左手拖着野猪,右手拽着鬣狗,嘴里叼着黑鹿。四头十六腿,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奇形怪状,吓飞了鸟,吓跑了兽,吓得树木直发抖,吓得溪水折跟斗。
你还别说,始祖母也在折跟斗。四个头只有一个活着,十六条腿只有两条管用,能不别扭?又是刚刚分娩身体发虚,又是崎岖山路陡峭难走。
始祖母终于停了下来,打量着三个猎物:
黑鹿个头最小,已经死了,全身瘫软;野猪个头最大,半死不活,还在哼哼;鬣狗个头不大,却掉下来一条后腿半个屁股,拖泥带水。
干脆把鬣狗吃掉!饱了肚皮,长了力气,还少了负重。
始祖母想到就做,风卷残云,痛快淋漓,转眼之间,血肉淋漓的鬣狗,就剩了一堆白骨。
这一次,始祖母只叼起野猪,腾空而起,一阵旋风,就跃上了山坡。
在看得见黑鹿的坡顶,旋风落地,野猪放下,她又掉头回来,叼起了黑鹿。
就这样,三里一回头,五里一腾跃,辛苦的始祖母,搬运着她的猎物。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含辛茹苦的始祖母,养育着她的儿女。
有时候,实在太累,她也会停下来,喘口气,她就会听见,儿女在呼唤,就会看见,那个陡峭的山崖。
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山崖,直上直下,头上矗立着千丈青松,腰间缠绕着万年云雾,脚下踏着不舍昼夜的河流。
没有谁去靠近它,谁都害怕掉下去会粉身碎骨。没有谁去窥探它,浓云迷雾,想看也看不清。所以,就谁也不知道,在山崖下不到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宽阔的平台。
平台一块巨石生成,又堆积了大大小小的石块,石块的缝隙中长着三棵松树,又老又小,歪歪扭扭。是山风多情,在这里播种了崖上青松的后代;又是山风无情,把参天大树的子孙变成了小老松。
平台的旁边有一个山洞,洞口高不过两米,里面却豁然开朗,足有上百平方米。干燥的石头地面,铺满厚厚的松针,散发着一股股的清香。三米高的洞顶,裂开一道细长的缝隙,阳光透进来,又带来一阵清风,裹着几根飘飘落下的松针。山洞深处,还有一条长长的沟槽,一道山泉从洞壁上流下来,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
隐蔽,安全,宽敞,舒适,阳光,雨露,亮堂,温暖。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这就是辛苦的始祖母和十个儿女的家。
天知道她是怎样找到的。
厚厚的松针上,四只幼仔挤在一起睡觉。既看不出黑白相间的种群特征,更见不到花耳朵家族的徽征。睡一阵,静寂无声,醒一阵,哼哼几声。小东西们都饿了大半天了,还是不见母亲的身影,就只能这么忍耐着,等待着。
六只小猫已经黑白分明,耳朵上也有了白色的竹叶图案,也正挤成一堆,但不是睡觉,而是打闹。尽管尚未成年,他们的体型已经和母亲差不了多少,只是因为没有经历风吹日晒,世事艰辛,他们的皮毛才显得鲜亮干净,他们的眼神也显得天真清澈。
四只幼仔终于忍耐不住了,发出饥饿的啼哭。
六只小猫争也不打了安静了,只听见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饥饿的滋味真难受,母亲怎么还不回来呢?在他们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去得这么久,他们也从来没有挨过饿。今天这是怎么了?真想出去看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