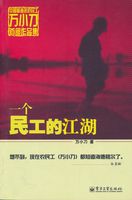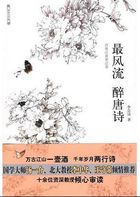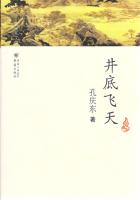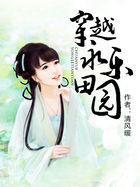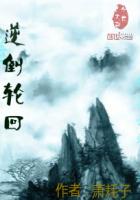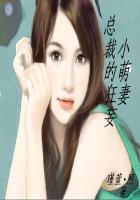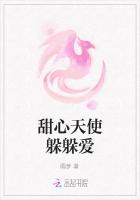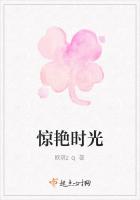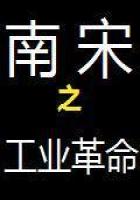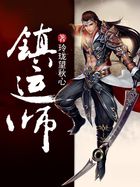(一)商品化社会的文化形态
刘:最近有一些冒险主义的主张,如一些激烈的作家在很气愤,觉得许多作家正在迅速地堕落,甚至认为是作家引导人民堕落。文化界把问题提得非常之严厉。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你像大家谈得很多的,诸如什么“媚俗”、“迎合”的问题,什么报纸上随笔流行的问题,一些很快应市的大部头著作的七拼八凑的问题,还有一些“私小说”的问题,还有为了改编电影,为国际电影节得大奖写小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作家的问题,正像水煮开了,你不能说是水本身自己就能开,而是有柴的燃烧为前提的。老实说,80年代人们还没有感到市场经济对文化有这么大的支配作用和影响,但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情形变得非常尖锐和戏剧化。
张:80年代开始的时候,市场化、消费化、社会公共空间的多元化等等都是知识分子自己倡导和追求的东西,但现在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好像是一些叶公好龙的角色,一旦这些东西真来到的时候,反而情绪很急躁,不能接受。80年代追求好的日常生活,追求一种世俗的生活空间的丰富,都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共识。我还记得你很早的作品《我爱每一片绿叶》,那个作品讲的是一个人的私生活是不应该受到压抑的,在他个人的空间里应该完全可以有他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私生活。“个性”也需要落实政策。这是一个叫魏锦星的人还在抽屉里藏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当时大概除了极少的人之外,大家对这种私生活空间的拓展都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而这种日常生活的丰富也是人们一致肯定的,而社会市场化也已是提供这种情形出现的一个保障。“新时期”文化的主要的目标恰恰是从一种禁欲主义、极端道德化的世界之中解放普通人,让他们过一种较为宽松的、平常的生活。像张炜的《古船》里的那个隋抱朴,正是发现那种斗来斗去、杀来杀去不行了,他最后才落实到村里的粉丝大厂的物质生产的发展的目标上去。
到了80年代后期,可能是感觉到这个物质生产发展、日常生活改善的目标完成得还不够快,要把一种“现代化”的总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极端化,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碰撞和冲突。那么这个碰撞造成了这种整体化的解决方式的挫折,结果挫折反而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思路下的发展。这几年的经济、社会进程也说明了一种不同的思路、不同的选择起了作用。那么现在“龙”来了,一下子知识分子自己就有许多问题逼近眼前了。一个问题是过去作家都是很了不得的,都是为人民“启蒙”和“代言”的中心。现在要通过市场的选择,而市场本身又是一个相当冷漠、犬儒的系统,它是不管你过去多么了不得,你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它是以自己的运作来选择你的。这当然是使许多原来处于文化中心的知识分子边缘化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许多作家、文化人有一种害怕面对问题的心态。市场化肯定要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像腐败、“三陪”、治安等前边我们举过的问题,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这些问题作为一种负面的结果,已经相当严重地存在。其原因也很多,我想有许多问题首先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有相当多的问题是技术化的,是社会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状况,它肯定和道德有关系,但也不应夸大道德堕落的严重性。如“三陪”、贩毒等等坏现象,有一些固然有道德上的因素,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等方面的因素,也有管理方面的问题。有加强法制和加大执法力度等解决的方法,这些东西恐怕甚至比道德上的教育还要重要,当然这也不是否认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但要有很多技术的措施才能解决问题。这往往是靠法制,也靠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而不是靠终极关怀能够奏效的。你给一个毒贩子讲终极关怀恐怕用处不会大,恐怕还是依法处置用处较大,然后教给他基本的规范才行。那么,恐怕这种很激进的思路,它针对的还不是毒贩子或是“三陪”小姐之类的人,还是知识分子内部或是作家内部的。这种很激昂的情绪一方面是市场化带来的不适、焦虑。另一方面恐怕还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很多好处开始消失,体制转轨造成了很多问题。如作家在五六十年代在稿费收入上还是可观的,比照当时一般的生活水平还是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许多作家的小院都是当时买的,现在作家能买得起小院的恐怕极少吧。当然当时的作家、知识分子的隐性收入也还是可观的,如相当好的社会地位,如担任政协委员,如免费的旅行,深入生活等等。当时情况也是很复杂的,远不像今天推想的那么简单。这恐怕也是作家、文人失落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过去作家、文人都在体制内,虽然有许多时候挨批判,但毕竟是完全依赖体制生活的,是计划经济的文化生产的运作过程的一个环节。但现在社会的转型却改变了这种情况,作家、知识分子的很大一部分需要进入市场。于是,转变中的不适就显示出来了。
刘:不过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天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提出一些最高的原则。
张:我想知识分子的确有不同的面向,在西方知识分子的面向中也是对社会、文化既有认同,又有反抗、批判,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作一种比较机械的理解。批判或是否定都是有一些前提的,都是有一些范围的,也不是绝对的。像黑格尔这样为国家提供合法性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而目前的西方,也有许多所谓政策知识分子,他们和国家的政策之间有许多联系,为国家政策服务,这也是一派。在中国,这一派知识分子90年代以后也已经出现了,且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如许多经济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等等,他们的声音也渐渐变大了。不少见解也在社会及国家运作中有所反映。但目前我们谈的是人文知识分子,是属于“百无一用是书生”一类的,和这些政策知识分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确是较强的,他也有责任提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但这些工作恐怕也是有几个前提,一是这种批判恐怕是以对人们的关切,而不是仇恨为基础的;二是这种批判乃是以对社会的精细的分析,是以学理为基础的,也是以直面社会状况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些前提,变成“为批判而批判”就收不到任何效果,因而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文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批判恐怕还是有这样的前提的。比如像你和王蒙这些作家都是对市场化有批判的,但却不是用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猛张飞式的方法来做的。而且市场本身能够容纳各式各样的声音,包括很激烈的批判的声音。像美国的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对美国的传媒批判十分激烈,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也只有靠媒体、出版业来实现。这也说明市场选择的多元性的面向。这种激烈的声音往往被市场吸纳之后变成了一种没有多少破坏力的东西。我在《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2期上分析张承志的那篇文章,其实也是探讨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进入市场的方式。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人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与德里达、福柯这样的思想家批判社会的同时也批判自己是不同的。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唯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
刘:比如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是很少了。像我们提到的福柯、德里达这样一些思想家首先批判自身,然后怀着一种痛苦来认知世界。
张:我们的张承志等人先是确定自己不受这个世界的制约,站在这个世界之外,来批判这个世界。但福柯他们却不是如此选择,他们是在世界之中进行反思的。
刘: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人文知识分子可以在市场化之外存在?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例子是《红楼梦》,这部著作是一个不求闻达、没有任何影响、非常贫困潦倒的人写作的。到现在曹雪芹的家世也还是一个谜,引起了那么多红学家的研究。但这部书在他死后,经过传抄和印刷才成为一部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这个例子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和当时的文化打交道就能创造出一种经典呢?最近以此为例的文章也有不少。
张:这里面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前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状况,曹雪芹不是说他要不要稿费的问题,而是他根本无处去要稿费:根本就没有一个市场存在。而且当时对于作者的概念也是很不在意的。福柯就有一篇极为有名的文章《何谓作者》,讲目前这种有版权稿费、有作者权益的机制,有这样一种署名的制度,都是资本主义运作的结果。
刘:当时对署名很不重视,像《金瓶梅》根本没有署名,兰陵笑笑生还是后来加上去的。有了文化市场,才有稿费,才有职业作家。
张:由此看来,曹雪芹的写作可以说是一个爱好者的业余活动。这种状况似乎只有农业时代才可能有。有人用这个例子来说作家不应要钱,不应有经济利益,恐怕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张中行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有个开玩笑的说法,说曹雪芹的“举家食粥酒常赊”乃是文人的夸张。曹雪芹恐怕还是食粥之余,也能吃点炒肉丝之类。这当然是一种幽默,但也反映出某种事实。写“穷”其实也是中国的一种文学传统。
刘:你这个意见会不会导致一种看法,就是说写名著一定要在古典时代,要在农业社会里才行。而目前市场化、消费化、商品化的时代不可能有名著出来。那么,是不是说在市场经济下,甚至比较计较稿酬、版税收入的作家,就不可能出现大作家、大作品呢?
张: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问题,这些在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困惑又开始在目前的中国重演。这个问题就很典型。在西方资本社会中,很早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也就是黑格尔感兴趣的“艺术死亡”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这么提出来,恰恰说明了这个时代本身发展变化到了一个关口。恰恰艺术在不同的时代要有不同的追求,要有不同的写作,它们是不可替代地去表达自己时代的文化和精神的要求。我们只能要求我们的作家写出此时此地要写的作品。
刘: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相当世俗的问题。在市场化的时代,你要获得一个作家的名声,一定要依靠市场。但在中国内地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变成了许多作家的一个很大的困扰,不少人认为作家怎么能依靠市场呢?有人认为王朔说作家和木匠之类没有什么不同,或是叫“码字儿的”,是一种极大的堕落。我的说法与王朔不同,但我也认为作家写作当然是一种职业。这职业当然要有职业的一些道德标准,也可能这种职业的道德标准比别的职业更严格一些。如外科医生的道德标准的确可能要比街上卖白菜的要严格一些,因为他从事的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作家也许要求也应严格一些,因为他从事的毕竟是一种精神生产,会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些都不能否认他从事的也是一种职业。这些职业都是由市场决定的,要求作家或文人这个群体为计划体制“守节”,不许它进入市场,这种心态现在流露得很多,不知你怎么看?
张:我觉得只有回到一个计划体制之中,他们的想法才得以实现,纯洁而不受市场影响的作家大概才可以生存下去。这种想法是相当奇怪的。市场本身有它的毛病,但因为有这些毛病就说它坏,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而且这个时代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种文学。
刘:这恐怕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张:这种情况与资本主义最初在欧洲发展时有一点相似性。那也是原本由贵族养的文人突然脱离出去,导致经济地位下降。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使知识分子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当然是对文化发展不利的局面。于是马克思这样的伟大的思想家才会批判资本主义对艺术发展不利,因为马克思不可能知道今天的跨国资本时代的问题,今天西方资本对高雅艺术的支持既通过国家投入又通过基金会等,把税收和一部分利润转化为高雅文化所需的投资。
刘:这些基金和投资会用在欣赏的人很少,但却是人类精神的瑰奇的花朵上。我们这种机制恐怕还未建立,文学上也就更谈不到。像一位诗人,受到了出国的邀请,想弄几万元出国,也没有可能,还受到大款的冷遇,这真是令人感到悲凉。其实这样的有名望的作家若在国外,的确很容易从一些基金会申请到一些基金,像飞机票这样的事是很容易解决的。这种事的确是文化转型时期里的矛盾和问题。引起一些心理的、文化的撞击是很自然的事。但由此引发出有关人们都在堕落的概括却又太过于简单了。
现在似乎有很多这种概括恐怕都是从这样一些事情引出来的。但这么一种情绪、这么一种思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怎么会文化界、文学界只剩下几个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其他人都堕落,都无理想呢?这从何说起呢?不知你怎么看。
张:这些说法反映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发展中的社会,像中国这样的社会,贫困仍然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不仅仅艺术家或者知识分子有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其他的社群所面对的这方面的不足也很严重。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家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在文化工业之中,来完成国家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一旦转化为市场化,国家的管理机制由完全的介入和支配,变成了一种协商、对话及依靠法律管理的方式,这些都使国家的资源不可能直接大量地投入文化产业之中,而是依靠社会及市场的自我循环和调节。这使得某些得不到市场支持的文化部门处于一种困境之中,而它们中的一部分又不能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这里产生一种失落感也是不可避免的。王跃生曾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讨论俄罗斯文化的文章,他认为俄罗斯经过转型,实在养不起这么多文化产业。因为过去是依赖计划强制维持的虚假的繁荣,一旦这种强制维护不再维持了,问题也就明朗了,该萎缩的部门也萎缩了,没有效益、只投入不产出的部门受冲击,几乎也难以避免。原有的文化产业的兴盛,是以国家削减了一些其他资源,拆东墙补西墙的结果。繁荣也不免于畸形。现在看起来,目前这种情况也有一定合理性。看看俄罗斯、东欧这种彻底西方化了的地方,文人、艺术家、高雅文化的惨状是让人长太息的。像索尔仁尼琴这样被放逐的作家,认为这种自由化的局面的出现,乃是他自己的胜利之日,他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没想到他的书被随意出版后,反而没有了读者,国内是一片骂声。
刘:官方甚至可以公布那些有关当时苏联政治的材料,比索尔仁尼琴写的翔实具体得多。许多当时的档案都公布了。
张:那个转型恐怕比中国残酷得多了。苏联电影原来是世界电影的一颗明珠。在世界上有它独到的风格,也有它的光辉的历史,而且是获奖频频。但现在大量的俄罗斯电影变成了三级片。这么看的话,中国转型的运作由于比较温和,比较缓慢,所以还是比较好的。中国艺术家还能愤怒,还能发出骂声,说明了中国的转型还是不错的。说句笑话,连饭都没得吃时,骂都没法骂了。国家与社会起了相当大的良性作用。目前看来中国的文化所受的经济的冲击虽然有,但已被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了,比起苏联、东欧那种原始积累的、赤裸裸的冲击来,要好得多。当然问题仍很严重,但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反而论证了中国市场转型的合理性。
(二)文人在市场中
刘:我们不管如何讨论这个问题,但在像我这样的作家的认知中,我觉得目前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多元格局当然还有许多的问题,但还是五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来难得的。经过胡风事件、反右斗争、十年“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多元格局的确是来之不易。无论有什么“泡沫文学”、“大花猫文学”,我觉得毕竟是没有出现那种一提“主观战斗精神”便一伙人关进监狱,或是一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没提浪漫主义或是“现代主义”之类,就被打成右派,比起仅仅主张写“中间人物”便要惨死监狱,那要好得太多了。也许“大花猫”之类的东西你觉得不够伟大,不够永恒,但你也不必去横扫,你可以提供,还可以自己去写“非”大花猫的文学。或者你看到有的是写永恒名著的胚子,你可以培养他,发现他,但也不必这么愤愤不平。
张:我看不少人这种愤愤不平是一种对自由的恐惧,就像曹禺《北京人》里面的曾文清,要给他自由,他都不敢要。这种情况,我认为是来自于一个“现代性”的焦虑。这个焦虑是基于“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的矛盾。现代的追求的东西实际上相当具体,相当实在,日常生活的改善实际上是极为世俗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实现的过程极为伟大。像当年一些写理想实现的戏,诸如田汉老前辈的戏《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除了又有钱又舒适的东西,体现了“理想”的物质条件一下子到来的情景,这种畅想其实还是很乏味的。而上海有个作家陈继光,这个人专写一些高技术对人生活影响的科幻式的小说,但似乎也不太成功。由此看来,写满足、享受或成功的作品也不甚有趣。这说明写作者追求很终极的目标,但弄出来却是种相当平庸的想象。如果看到人类追求的目标的世俗性,那许多人是会失望的。一句话,“现代”就是以伟大崇高来追求平凡。目前,中国的社会正是在一种世俗氛围中走向生活的进一步的改善,这造成的失落与反抗也的确厉害。
刘:你看这些崇高、理想的诉求,可以说是针尖,另一些可能是针鼻,针尖是刺破,针鼻拖着欲望的长线在扯动。针尖不断刺破,针鼻不断缝合,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关系。但也不排除有相当的危险性在里面,这种危险我们还是不能不正视的。当然文化人中有这种文化冒险的冲动,但只要不为政治力量所利用,就尚不至造成很大的威胁。但一旦它否定中国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甚至主张回到某种“专制”之中,如某种禁欲主义,这我认为是很可怕的,我要坚决反对的。如“三陪”现象,我当然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坏现象,这的确败坏了社会风气。但解决这种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却也为我所不取,就是让妇女一律不许到公众场所去,否则就严厉处置。这的确可以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但这恐怕是最坏的解决办法,最坏的思路。
张:我看市场经济中面对的问题,只能依靠法制,当然也需要道德上的制约。但道德化、道德主义恐怕不能搞成神学,不能搞成一种道德专制。一句话,应该有一些界限,道德宣传不应以强制的、极端的方式进行。同时还有一个身体力行的原则。提倡道德的人首先得自己言行一致,要身体力行,否则就弄成“假道学”了,变成对自己的一种嘲弄,就更滑稽了。宣传道德的人首先你要有一个道德上的承诺,你必须恪守你倡导的道德准则。钱钟书先生在《谈教训》一文里讲,假道学是把道德变成了一种艺术,真道学只好死后进天堂,假道学则生前就上讲堂。这当然是幽默,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如果你都不信你宣传的东西,那你宣传它不就成了欺骗,成了最大的不道德了吗?比如有人猛批商业的炒作之类是堕落,但他反对商业炒作的大著却又要通过这种炒作来推向市场,这恐怕就极为无聊了。批判别人的时候,如果不批判自己的话,那就是一种“假道学”的生活方式。
刘:商品化、消费化的冲击带来了许多文化上的新现象。像《渴望》开始的这种电视剧的制作,像流行歌曲之类的现象,确实提供了一个相当丰富的“俗世”的景观,这要引起思考。而不是回避或自己躲在家里生气。敢不敢直面俗世,其实是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工作。恐怕很激愤、很恼火、很不痛快用处也不大。我觉得还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为好,太急太躁,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出事。
张:你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恐怕加强社会分裂,最后会自食其果。对于我们共有的这个社群不但无助益,还会引发出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的确不能坐视这种激进主义浪潮随意泛滥,那是会让文化冒险主义肆意横行的。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还是要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
刘:对商品化、消费化带来的问题自然应该尽一个文化人的责任,进行反思、批判,但这应该是有理智的,是要进行分析和思考的。离开了这些前提,批判有可能变成盲动,最后导向文化冒险主义的极端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