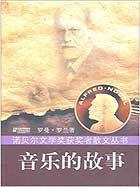中国方面,《长春文史资料》刊载了一系列“满映”中国职员对“满映”和“满映”生活的回忆。其中,演员张奕张奕:《我所知道的“满映”》,载《长春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总第12辑,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演员转摄影的王启民、放映转摄影的李光惠、美术师刘学尧和配角演员贺汝瑜的回忆和受访记录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总第17辑—长影部分电影艺术家小传专辑》,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发行,1987年。具有相对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阶段,全面综合研究的新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中日双方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动机和研究兴趣而导致对同一批材料的认识和处理方式迥异,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两国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甚至共享宝贵的材料,在互动中完成各自不同的历史书写。这一时期,日本方面“满映”研究代表人物是自由撰稿人山口猛,但同时学院体制之内也有些许零散的研究论述,以池川玲子《滿映女性監督坂根田鹤子》一文最有特色;而中国方面“满映”研究力量主要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档案馆、中国电影资料馆“满映”资料管理部门等,以胡昶、朱天纬和张学智为代表。就研究立场而言,日本方面或持中立或左或右;而中国方面对“满映”或“李香兰”的研究是作为“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一个分支研究。
(一)中国方面:以《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为代表
该书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者胡昶和古泉在迎“满洲事变(九·一八)”六十周年之际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委托而写成的。这是中国方面关于“满映”第一本也是最全面的一本著作。序言中讲到整理“满映”历史的目的是,使各国人民看到“日伪统治者如何利用电影这种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宣传殖民主义文化,为强化其统治服务”,从而使各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伪满傀儡政权的反动性质”,“并了解伪满电影同伪满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序言。
该书将“满映”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建立、初期活动、发展期、后期生产和解体),并在此框架下条理清楚地罗列大量事实性材料和概括诸多影片内容,评价性内容较少,即使有,也多借鉴坪井舆《回想》中的观点。总的来说,对“国策片”谈“用心险恶”或者“反动”等,对娱乐片尤其是中国编导组独立制作的娱乐电影或持保留意见或直接褒扬或温柔批判。
该书撰写过程中,著者得到日本人士森川和代、持永只仁和山口猛的帮助,在东北三省查找了大量报刊资料和档案资料,采访了许多当时健在的“满映”中国职员,还有很多长影同事协助搜集资料,相关史学专家都参与了该书的创作。所以,可以说它是一本里程碑著作。
不过,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该书序言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著者认为,“满映”电影活动“属于中国现代电影史的一部分,是我国(中国)现代电影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尽管这是在外来侵略势力操纵下所进行的,但毕竟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电影活动”。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序言。笔者认为,“满映”的电影活动是极为复杂的综合体,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为中国电影、日本电影。比较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满映”电影活动是在日本外力作用下的不具合法性的“满洲国”的垄断性的电影传播过程。“满映”电影活动可清晰地划分为中国人的活动和日本人的活动。历史资料证明,“满映”中国编导所拍摄的作品具有他们自己的内涵。只要是中国人的思想所控制的“满映”出品的电影是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电影史的一部分的;而大量的日本编导拍摄的电影,不管是典型的国策片、模仿日本片或他国片的影片,都应该视为日本电影史的一部分。
不管怎样,《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依然有其重要意义,影响力波及日本。1999年,横地剛和間ふさ子将该书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国内发行,而这也促生了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日本现代史专业的大場さやか以《満州映画協会の役割とその影響》为题的毕业论文的诞生。另外,笔者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学习期间的硕士毕业论文《20世纪40年代日据东北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的考察——以“满映”时期李香兰出演的作品为中心》(2003)也把该书作为中国方面第一参考文献。
除《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一书之外,中国方面还有朱天纬的《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的“李香兰”谎言》(1994)、张学智的《满映——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铁证》(2003)和张奕在占有大量相关材料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发表的《满映始末》(2005)。张奕在新书中或评或述或引地揭露了当时演员养成所学员的心理状态。对张奕为代表的“满映”中国员工而言,他们对“满映”的感情都很复杂。拥有不同的背景的他们,在被利用的过程中也成就了自我。张奕在书中忏悔、反思、揭露,但也提及“满映培养出一大批为艺术勇于牺牲勇于献身的演出人才,而且都是中国人”。张奕:《满映始末》,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2005年,第51页。
(二)日本方面:以山口猛为代表
有意思的是,在《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的撰写积极进行的时候,作为协助人士之一的日本自由撰稿人山口猛也同时开始了个人化的“满映研究”。
山口猛于1989年出版了《幻のキネマ“满映”——甘粕正彦と活动屋群像(梦幻的电影“满映”)》(平凡社),至1995年该书也重印了两次。该书与长影撰写有着明显的差异:一、从取材来看,山口猛的取材来源主要来自了解“满映”的日本人,在中国这边得到了王锦文、王启民、胡昶和吴代尧的帮助;二、从学术规范来看,山口猛在书后列出了上百本参考图书和近三十种报纸杂志年鉴;三、从行文来看,山口猛将满洲称作“母亲的国家”,整本书从对“满洲”的曾有的个人体验开始娓娓道来,将满映的历史置于日本历史和满洲历史之中,重点突出各种人物(根岸宽一、李香兰、牧野满男、甘粕正彦、王则、八木保太郎、内田吐梦等)的活动,以此种方式把握历史脉络;四、山口猛更加关注“满映”的延伸——东北电影公司的具体情况,而同样的主题下,长影的撰写公布了东北电影公司日本工作人员名单和返日前这批工作人员联名写给中国政府的感谢信。
1993年,山口猛又发表《擬制の王国としての満映》。这是一篇较为严谨的学术论文,研究视野更为开阔。集中探讨了“满映”中斡旋的种种矛盾,比方说,甘粕的立场和矛盾给“满映”带去的“变化”,电影制作人根岸宽一和牧野光男的艺术追求给“满映”带去的“变化”,屈服于“满映”的中国编导给“满映”带去的变化——使“满映”“非满洲化”等等;尝试种种“满映”相关的横向比较,如将“满映”和中华电影公司、华北电影公司比较,将甘粕正彦和川喜多长政比较,将满洲和上海比较等等。
2000年,山口猛出版了《哀愁の满洲映画——満州国に咲いた活动屋たちの世界(哀愁的满洲电影)》。很显然,“满映”影像资料的重新面世和大量其他相关新材料的出现(如王则问题)以及作者多年对“满映”的累积性思考是第二本著述诞生的直接原因。和1989年的写作相比,第二本书只关注“满映”问题,对内田吐梦、芥川光藏、王则、李香兰、甘粕正彦、“满映”真实影像资料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除了山口猛以外,日本电影评论家松田政男等也对“满映”有所关注。松田政男《満映「虛構」のラビリンス》一文,受日本著名历史民俗学家山口昌男《「挫折」の昭和史》启发,在山口猛的“满映”先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用系谱学的方法来诠释“甘粕传说”。
另外,横地剛和間ふさ子的《満映国策映画の諸相》译后记、池川玲子的《满映女性監督坂根田鹤子》、大場さやか的《満州映画協会の役割とその影響》和笔者硕士论文在内的四篇文章也为进一步认知“满映”提供了新鲜的材料、观点和研究方法。
横地剛和間ふさ子的译后记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他们认为,在“满映”生产的娱民电影中可以看到中国编导和日本编导对满洲国殖民地人民的认识或理想的差异,认为应该重新探讨中国编导在极限环境下创造出来的进步作品,而且应该把“满映”研究范围从中国内地和日本扩散到中国台湾、朝鲜和韩国,因为“满映”出身者也活跃在那些地区或国家的电影界中。
池川玲子从女性视角感知和分析了被喻为“日本最早的女性导演”、“共荣圈唯一的女性导演”坂根田鹤子的“满映时代”。在占有大量先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池川玲子的问题意识贯穿全篇,探究何以作为女性的坂根成为导演并成为“满映”导演,支配者女性是怎样用影像表述被支配者女性的生活,女性导演在拍摄女性题材的纪录片的过程中如何完成对男性导演支配银幕的对抗,并且用电影本体分析的方式细致解读了坂根的代表作《开拓的花嫁》,另外,日本启民映画和“满映”启民映画的使命也在坂根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大場さやか的论文使用了当时的电影杂志《映画旬報》、《満洲映画》上的文章来理解“满映”是如何利用和普及电影以及中国民众有何反应。而笔者的硕士论文是在掌握与李香兰相关的影像和文字资料的前提下,分析李香兰形象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探讨李香兰的功和罪,并以李香兰的电影作品为中心考察“满映”的成就与失败。
我的研究立场
在进入具体的研究之前,需要表明笔者的研究立场。对于笔者而言,首先是将20世纪30年代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活动当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来看待的。笔者的创新观念主要来自对“满映”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读解,并在这种读解中试图改变以往研究所秉持的历史观、文化观和电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