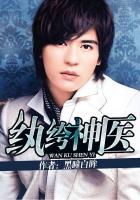上学之前,同村大一点的小伙伴们渐渐没时间带我们玩了,像大我一岁的小满,每到休息日就喜形于色地跟我们讲学校里怎么怎么好玩,怎么怎么有意思,每当我们不明白他说的话时,他就眉飞色舞,更加得意地说个没完。弄得我们艳羡不已,很想体会一把他所谓的“上课”、“做作业”之类好玩的事情。
过了不久,学校开学了。中午,小满遇到我找他玩,他笑着说:“我要上学去,要不你跟我到学校去玩吧!”我们便一同来到学校附近,远远望去,大群的孩子们在操场上三五成群,或跑或跳,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小满满脸欢喜地跑向操场,一刹那间淹没在喧闹的人群中。陡然间我胸中涌起难以压抑的冲动,我要溶入这些孩子们当中,和他们一起玩!这可比屯子里的小孩多多了。原来上学这么好玩呀!我也要上学!
可眼下好像没人要我呢,现在我也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后来有消息说,新学期开始了,学校要在各村招收学生,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来“号”学生。适龄的孩子有不少,包括我在内,那阵势也算不小了。许多家长领着各自的孩子前来参加测试,我隐约记得几个老师在教室前摆上桌椅,一个个地让孩子过来问这问那。考核的主要项目是数数。轮到我时,老师笑着说:“你过来。”妈妈陪着笑也跟着我过去。
“你多大了”?她问我。眼睛睁得很大,盯着我的眼睛。
“我八岁,”我怯怯地说。
妈妈忙在一旁补充说:“虚岁八岁,周岁七岁。”
老师冲妈妈笑了笑,又严肃地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
“小牛,”我又惴惴地回答。
她当时就绷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农村孩子的小名都很不正规,像外号。据说名字越贱越好养活。有个叔辈的太爷,原名帮旭,大家却叫他“瞎帮旭”,其实他不瞎;还有个爷爷辈的,原名国选,身体精壮,力大无穷,大伙提到他时只说“灯笼选子”;我大伯的大名是庆戈,大伙都叫他“拉锅子”。原因就是奶奶当年生了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大伯生下不久,为了讨个吉利,把大伯用锅底灰蹭了一下,因而得名“拉锅子”。平素见面都叫小名,大名反而没人叫。我小名叫“小牛”,我弟弟也不能幸免叫“小羊”。大一点的小伙伴们常常取笑我们,当着大伙的面大声笑唱,“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亲人解放军!”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弄得我和弟弟十分尴尬,只能讪讪地陪着笑。但心里却有点羞辱的感觉,总之很不舒服。
现在老师也笑成这样,我顿时有点自卑,接着她又让我从1数到100,本来我会数,但是我就不张嘴。老师和妈妈都在旁边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等着我开口。我局促不安地红着脸,木讷地看着老师,时间像是僵住了,一切都停滞了,直到老师无奈地说:“好吧,下一个。”我如释重负,难为情地扯着妈妈的手,听着妈妈的数落,快步走出人群,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钻进去。
身后的人群时而发出哄笑。后来我们村里的半大的孩子们在说笑中总结了这次招生活动中的很多经典对白,一致认为吴国锐的表现最有创意。憨憨的国锐长了个大脑袋,平日里总是笑呵呵的,咧着嘴,露出白白的长牙齿。当天老师让他数数,他大大咧咧地唱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千一万,一嘟噜一串,还有还有..”当场笑翻了所有在场的人,那个女老师居然笑得岔气了,眼泪都喷出来了,登记的笔也找不到了。国锐看着大家笑成这样,不明就里,也跟着傻笑。
当然也有很多小孩表现很好,像王立见和王美丽就很顺利地过关。王美丽是姐姐,我从不跟她玩,但我喜欢王立见,精瘦的体格,个子很小,很可爱。我经常拿小人书给他看,向他炫耀自己有很多故事。他也是唯一一个我到现在还经常联系的伙伴。你很难想像他现在居然长得向鲁智深一样粗犷雄壮。
那次招生后,妈妈总说我可能得再等一年才能上学,因为我表现不好。但没过多久我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上学了。
对我来讲,上学就是为了找更多的伙伴一起玩,一切都是为了寻找新奇的经历和故事,没有了这些,一切将变得枯燥而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