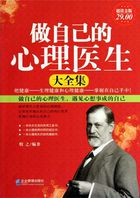疏锦看着越走越远的云夕,突然感觉眼皮跳了跳。
“难道......”她低低的没有说出来,只一笑了之,任他千般诡计,我自视为浮云。
自云夕来后嵇江脸色一直不太好,有些心不在焉,陈烈和疏锦也就没了再赏下去的意思,只得悻悻回去了。在回去的马车上陈烈眼神一撇:“刚刚还算你反应快,有点小聪明。”
疏锦不屑地翻个白眼:“红衣公子以为人人都如你一般么?”
陈烈愤然:“我怎么了?我哪点不好了?”
“那你说说你哪里好了?”疏锦不大在意,悠然的靠在轿壁上,眼神一直看着郊外的神色,微微带着点笑意。
“我长得好看!”
“嵇公子就坐在你旁边,你怎么有脸说这句话?”
“我身材好!”
“你得了吧,那是肾气亏损了。”
“......那你也没什么优点,自视清高嘴巴恶毒目中无人......”
眼看着陈烈正滔滔不绝的数落疏锦,疏锦脸色越发难看起来,最后终于转过头:“我嘴巴恶毒红衣公子口下也没留情面。再说我目中无人,红衣公子你是什么物种?”
“我是什么物种绯瓷姑娘自然也是一样。不然你怎么同我交流?”陈烈眼珠一转,痞痞的笑起来,却依旧不减风流。
疏锦正要反驳,嵇江忽然开口,眼神有些凌厉:“希望绯瓷姑娘以后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如若不然,镇国侯府也容不下姑娘了。”
疏锦旋即眉头一皱。
看来嵇江真是爱云夕至深了。
陈烈看了看疏锦,难得解释道:“你不要怪她,这也是我授意的,毕竟都是为了你好。”
“红衣你也越发不懂事了!”嵇江此时温和气度全无,浑身的冷气震得人不敢随意放肆,颇符合他世子的身份。
陈烈沉默了一会儿,忽而冷笑:“我若不是你的朋友,我也不会做出这等不懂事的举动。既然世子不悦,那我往后便不会如此放肆了。”
嵇江皱眉,良久语气也松下来:“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罢了,随你们,只别真伤了她就好。”
陈烈终于爽朗地大笑起来。豪气地拍拍嵇江的肩膀,嵇江也不恼,随他施为。
疏锦神情一直淡淡的,任陈烈如何招惹她也不再言语。
下马车时,嵇江很自然的伸手去扶疏锦,疏锦避开他的手,直接撑着陈烈的肩跳下来,看也不看他,眼神冷冽:“不敢烦劳世子大驾。”
“绯瓷姑娘......”不等嵇江说完,疏锦直接回了客房。
被惹怒的美女脾气是十分恐怖的,更何况疏锦本就是一个狠厉的人。
陈烈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双手负于背后,摇着头进了侯府,口中还一直念叨:“这下有好戏看咯。”
一连几天疏锦都没再理嵇江,那冷漠的表情,陈烈也不敢去惹。嵇江终于十分大度地退一步,主动找上疏锦,满脸歉意:“绯瓷姑娘,那日是我不好,我在这里跟你赔个不是。你可否大人大量不再计较?”
疏锦从书案中抬起头来,扫了嵇江一眼,然后伸手道:“那么赔礼总该有些诚意吧。拿来。”
“什么?”嵇江愕然。
“你就空手来赔礼的么?”疏锦皱眉不悦,看神情似乎只要嵇江点了头,她绝对会继续生气。
嵇江支吾着,摸遍全身也找不出一点可送的东西,只好无奈道:“绯瓷姑娘,我因不知你喜欢什么,所以没敢随意准备,只等问了你,就好去买来双手奉上。”
疏锦笑了笑,眼波流转,隐隐有光芒闪烁,直射入嵇江眼底,他瞬间觉得意识模糊。
她带着蛊惑的声音响起:“我最爱收集各种各样的棋子了,听说你有一枚棋子很是独特,赠与我,就当做赔礼了。”
嵇江双眼无神,闻言缓缓从怀中摸出那枚棋子,光晕流动,疏锦看清了棋上刻的两个古字。
麒麟。
似乎下一刻麒麟印就会放到她的手中。
蓦然门外响起一声大喝:“嵇江!”
嵇江只觉石破天惊,隐隐破开混沌拯救他于迷雾,他手一顿,回身望去。
陈烈红衣飞扬,怒目而视,快步走进来将棋子塞进嵇江怀里,护在他身前:“绯瓷姑娘意欲何为?竟然连摄魂术也用上了!”
嵇江一惊,有些防备的盯着疏锦。
疏锦暗骂陈烈总坏她好事,但面上却冷冷道:“纵使红衣公子和我不对盘也不必如此毁我清誉,若我会那什么摄魂术又怎会落得这般地步?”
“这不是你故意接近世子最好的掩饰吗?”
“呵!”疏锦冷笑连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说我故意接近世子,那我可有做什么加害世子的事么?”
陈烈咄咄逼人:“你接近世子不是为了害他,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你真正的目的在于这枚棋子!”
“你以为一枚棋子是什么宝贝值得我如此费尽心机去夺取?”疏锦好笑地问,目光已经冷如冰雪,整个人氤氲在寒意中。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宝贝,但是绝对不会给你!”
疏锦笑了一下。
嘴角轻蔑,眼中薄凉。
随即挥袖便走出了房门,与两人擦肩时,陈烈听到疏锦低低的呢喃了一句。
“若不信我者,我——绝不强求。”
她走出房门时岁月安稳顷刻变为流星飒沓。
在陈烈眼中凝聚。
他如愿以偿赶走了那个让他感觉怪异的绯瓷姑娘,然而当她真的走出他的视线,他心中有些不知名的情绪在无声蔓延,然后如猛兽般淹没自己。
呼吸微微困难。
“多谢红......红衣你怎么了?脸色怎么难看成这样?”嵇江正欲道谢,却见陈烈脸色惨白如雪,与红衣相衬,显得格外动容。
陈烈皱了皱眉,勉强笑道:“我没事。”
然后和嵇江走出房间,分别时嵇江还有些不放心,嘱咐道:“若要有什么不适及时告诉我。”
陈烈看了一眼厢房前的那棵杨柳,然后肯定的点头:“我真的没事,你自己顾好自己就行。如今她走了,我也——心安了。”
我也心安了。
可是为什么脸色苍白至此,他也不知他为什么要逞强或者掩饰,他只是知道,这种情绪是他印象中所不容于世的。
那么,就应该完全扼杀。
不留一丝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