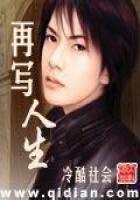聂家的这处私宅,占地面积十分广阔,汽车在门岗持枪的哨兵处验明身份后,约摸又行驶了七、八分钟,随后停在了正房门口。
下车,无视守门士兵诧异的目光,过正门,走甬道,将要踏上进入正厅的台阶时,聂瑞安突然停住身形,一侧的上等兵林森紧张地呼吸为之一窒,都已经到这个节骨眼儿上,这个大少爷可不要再什么妖蛾子啊。
聂瑞安望着正厅紧闭的大门,又抬头开了一眼高悬在天空的那枚太阳,今天是晴天,冬日的天空,干净而清爽,阳光明丽却不张扬,透过清澈的蓝天散下来,照的人的心里暖暖的。聂瑞安轻轻地念叨了一句“天气真好,希望运气也能这么好!”便一步一步踏上台阶,来到门前。
林森终于把心放回了肚子里,小跑两步,抢在聂瑞安之前来到门口,有力的三声扣门,然后立正、敬礼,“报告!”
房门很快被打开,拨开厚厚的用来挡风的棉帘子,闪出一张略有些粗犷的中年男人的脸庞。
林森再次立正、敬礼,“报告长官,九少爷已被请回,请指示。”
中年男人看看一脸忐忑的聂瑞安,小眼睛里有了几分笑意,微微眯着又打量了几眼,才对林森说道:“谢谢你上等兵,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
林森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纪律性,敬礼,然后向九少爷和中年男子道别。
中年男子撩起帘子,“想什么呢六九,快进来吧,外面天儿干冷干冷的。”
聂瑞安神色有些复杂地看了中年男子一眼,半晌还是什么都没说,迈步走了进去。
屋子里的火墙烧的正旺,聂瑞安一走进来,便觉得热气扑面而来,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
“六九,冻着了吧,快过来暖和暖和。”迎上来的是一个中年妇人,一派珠圆玉润的富态相,她是聂瑞安的生母沈秀梅,武溪沈家的幺女,聂德远的正房太太。
感受到母亲的关怀,从来到此间一直处于压抑和紧张状态的聂瑞安终于不再控制自己的情绪,鼻子一酸,伤心、恐惧、委屈、难过,种种感觉一齐涌了上来,聂瑞安拉着沈秀梅的手,就站在客厅是间,像个女孩子一样扭扭捏捏地哭起来。一开始还哭得很小声,哭得沈秀梅原本武装起来的坚硬瞬间崩塌。
沈秀梅伸出一只手摸摸儿子的脸,凉凉的,还有点湿,忍不住笑着冲一边的中年男子说道:“长得比我都要高一头了,还像个小孩子似的。”那口气,满满的感慨与宠爱。
中年男子也笑,“可不是,六九上一次像这样哭,还是十二岁那年被何家那个小子带着打架,让砖头拍着了,回来也是扑三婶身上好一顿哭,”余光看到从里间走出来的身影在听到这话时脚步明显顿了一顿,于是继续笑着说,“六九就是生的好,每回惹三叔生气,最后都是大事化小了。”他明明是在夸聂瑞安的命好,但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心思,实在是太过险恶。
聂瑞安眼皮子跳了几跳,这位远房堂兄,实在是没安什么好心眼儿啊。
“聂瑞安,收起你的眼泪,过来,跪下!”聂德远甫一出声,便有如雷霆万均,压的聂瑞安的心脏都随之一紧,他的身体更是仿佛不受控制一般,离开了母亲身边,慢慢挪到客厅正中,走到距聂德远三步的地方,膝盖一弯,便跪了下去,可见是平日里做得熟得不能再熟的运作,已经形成惯性。
聂德远看着下面双膝跪地的儿子,也是一阵阵的烦心,就是手握重兵,权倾一方,未来霸主之位炙手可热的人选之一又能如何?有且只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无数人热血打下的江山,又能维系多久呢?聂德远只觉得心灰意冷,人过五十天过午,岁月不饶人啊,几处经年的伤口,也都一起作起怪来,疼得他哼了一声。
听到哼声,沈秀梅便知道丈夫是心痛难忍,忙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别置气,孩子还小,慢慢教便是。”
聂德远点头,儿子这样,委实是老爷子惯出来的,妻子大家出身,便是盼子心切,也从来不会肆意骄纵,他自然知之甚深,不会无端迁怒。只是,十七岁还小吗?他十七岁的时候已经从少年士官学校毕业加入西北军了,便是如今的西北军中,十五、六的少年人也不在少数吧,真得还能寄希望于这个逆子吗?
“六九这也不是存心的,都是那帮坏小子撺掇的,三叔别生气,六九已经都知道错了,这回派去的人顶顺利就把六九带回来了。”中年男子,聂瑞生,一面说着一面从椅子上拿了坐垫想要递给聂瑞安。
“不要管他,”聂德远见状更是生气,“大小伙子,跪上个把小时跪不坏他。”
聂瑞生冲聂瑞安使了个无能为力的眼神,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的边角,垂手静静地站立着。
聂德远坐下,两手向下按住太师椅的扶手,示意夫人也坐下,然后语气很是平静地问道:“你,知错吗?”
聂瑞安抬起头,只注视了父亲一眼,便复又低下头去,错了吗?也许在长辈的眼中,像他们这样不管不顾地追求侠义之气确实是错的。
在他的记忆中,聂瑞安这一次“犯事”,是因为前天无意中看到发小何景元的一个小跟班向东在哭,他随口一问,才知道向东的姐姐,就读于西北大学一年级的向楠,因为有几分姿色所以在歌舞厅做舞女赚些学费,同班一个素日追求不得的男同学得知这一消息后,竟大手笔地在舞厅包场,请了全系的学生去消遣,点名要看向楠表演,其间更是动手动脚,呵斥漫骂不断,向楠被欺侮地狠了,便趁机反手扇了这个男同学一巴掌,却不料被此人伙同几个帮手对向楠一通拳打脚踢,若不是同班的几个男同学见状不忍竭力拦阻,只怕命都要没了。
聂瑞安一听便撸袖子扯了何景元拉上向东打去了西北大学,钱,聂家有的是,打架,晋西北的地面上,谁能打得过他们聂家?男同学自然是毫无防备地被一通海扁。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以聂瑞安欺上的手段,聂德远根本无从知晓,但谁知那个男同学家里也有几分势力,且又不知道打他的是何方神圣,于是招呼了家中几个保镖,在夜里堵住了何景元,双方大打出手,男同学更是趁乱一棒子打在何景元的脑袋上,如果不是向东眼尖用胳膊拦了一下,只怕何景元的小命就没了。
聂瑞安长这么大,头一回碰到打了敢还手的,这毛病哪能惯,于是今天一大早,就叫齐了几个小兄弟,堵在大学门口,他还从聂瑞生那顺了把手枪,准备让那小子尝尝血的味道……
然后,他确实是开枪了,但准头实在差太远,除了引起一群尖叫声,啥玩意都没打中。再然后,聂瑞安就换了人,被抓了回来。
估计聂德远如此生气是因为他动用枪支吧,聂瑞安想了想,这种程度的打斗,确实不值得动刀动枪,但是,枪,是受了聂瑞生的话语刺激后他才想到拿的。聂瑞安偏头瞧了一眼聂瑞生,他依然没有什么表情地站着,显得很谦卑很恭顺。
聂瑞安将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想明白了,便不再犹豫,“父亲大人,儿子,”自称儿子还是头一回,真是有一点不习惯,“儿子不应该未经允许便私碰枪支,更不应该持枪行凶,儿子知错了,请父亲大人责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