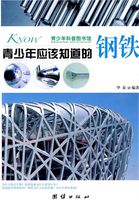我并非一个爱好写日记的人,准确地说,是厌恶日记的。按照这样的说法,我又为什么要在日记本上写下这一些话。其实,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浪费笔墨将一张张白纸涂黑,浪费一个个白本来写一些无聊的事;不知道在写些什么,却不停地动着笔。是啊,我在不知不觉间将书架塞满了整整一排的日记本。我想我是知道的,自己不停地写,不停地写,用掉一张张白纸,一个个白本。我怕时间太长,忘记我所想铭记的一切。不,又或许不是这样,我也许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淡化他留下的苦涩味道。想到这,大概这些日记还是为了让自己铭记,别再那样蠢得可怜的无条件的为他人付出。有多么地蠢?简直愚不可及。总是不停地付出,不停地去承诺。结果得到的是些什么?是进一步的索取和怀疑,也许那段话真的很对,尽管有十分老套。
每天都会收到一颗糖果,第一天你会心怀激动和感谢,第二天,你会礼貌微笑,久而久之习惯了念便也安心地接受着。只是有一天,他来见你却没有带来糖果,而你询问,不,是质问着他糖果呢?我的糖果呢?回答没有了换来的是凭什么。那年看到这段话的我,拿着手机大笑地对着他说“你看那男的好怂,没有糖再去买一包补偿给那女孩子也就不会吹了不是。”只记得当时他笑着揉了揉我的头问“如果是我呢?”“当然是一个糖果屋都给你,只换你不离开”我是这样说的。可每当再想起当初,只觉得自己的幼稚可笑。也是,一个初中生能有多成熟?他终究是离开了,没有小说情节般的理由,只有那么直白的一句话“只是性别不允许”性别比过了我这么多年付出的所有。我给过了糖果屋,遵守了我的承诺,而你却没有做到。如今,换我问自己一句凭什么?凭自己太蠢,蠢得不会去做那接受的人。也就是这样,我学会了怎样轻描淡写地无视别人给过的好意,做到了伤谁都绝对不会伤到自己。我不是圣母,做不到无私,而无私只能让我更加的自私。
今天我重返母校,遇见了一个孩子,很干净,那是学生独有的干净。这样的干净,让我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不由得自嘲地笑着摇了摇头,径自走向办公楼,那是没有少和他一起被请吃茶的地方。不外乎和以前的老师聊起过往,我曾经珍惜的过往,现在我也只是过往的过客罢了。从办公楼出来,那孩子上前拦住我,这令我有些惊讶与好奇。他微抿着唇,别扭地拉扯着自己的衣角,并不说话。换作以前,我会上前调戏他“哟,这是要告白的节奏?快说快说,小爷我组织好拒绝的语言了。”只不过如今自己也没有那么无聊。见他在那杵了半天也不吱声,我便转身走另一条楼道。手臂突然被抓住,我下意识地甩开。从那以后,我便极度厌恶他人的触碰。心情没了一开始的平淡,有一丝厌恶在心底滋生,我转过身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稳“同学,有什么事?”而他只是慌乱的语无伦次地回答你我他。我有些不耐“没事我就先…”“前辈,我喜欢你!”“……”我没有回答,也懒得回答。他也就是和以往一样的人吧,和人打赌来对我说这些话,以我的反应来决定赌博的输赢。无聊。岂料我正当准备无视他离开的时候,他再次抓住我的手臂,惶急地再次开口“我真的喜欢你,真的真的喜欢你。”第二次被抓住,再好脾气的人也会发火“放开。”我以为他会吓得立马松开手,然后就能头也不会的走掉。哪知道他紧紧的抓住我的袖子,并没有打算放手。他仰着头认真地看着我,这时我才开始打量他,身高只及我肩膀,只是那双眼睛很纯粹,充满了认真。那又怎样?拨开他的手,撩开挡路的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一路上回想着那孩子的表情,那相同的动作,语调,只是一个是对我,一个是我对他。
和往常一样,回到家,洗了澡就坐在画室开始画画。关掉手机,拿起铅笔却怎么也下不了笔。便打开手机准备着明天的日程。“叮咚”屏幕弹出一条短信。“前辈,我真的喜欢你。顾南漆。”我想也不想就把那串号码输入了黑名单。只是好像事情并不如我所愿。
写到这,桌旁的人放下笔,习惯性向后靠,用手捏了捏鼻梁,眼睛有些酸胀,便闭上眼准备打个小盹儿。暖气开得很足,没一会桌旁的人便睡着了。咔的开门声“付亦,你还在…”声音的主人推开门看见躺在椅子上睡着的人,唇微抿。拿起一旁的衣服准备给人盖上,视线却扫到桌面上摊开的本子。“…”衣服直接甩在人的脸上。“靠。”被打扰到睡眠的人不耐烦的拿下脸上的衣服,不爽的看着眼前的人不由得讽刺一句“别人给人盖衣服都是往身上盖,你老倒好直接糊脸上。你这是怕我感冒还是嫌我太聪明?”原以为会挑起那人的怒气,怎知他却倚着桌子,拿起桌上的本子翻到第一页开始朗读,声音低沉却不失磁性。“翁宇!”付亦咬牙低唤。被唤作翁宇的男人,合上本子抬头看着付亦“你给我说的作业就是这个?熬这么晚就为了这个特别重要的作业。”人语气很淡听不出喜怒,只是在“特别重要”这四个字上加了重音。付亦身子一僵,有些心虚“今儿天气不错。”“嗯,月亮挺圆的”“……”翁宇默默的看着眼前的人眼珠子咕噜噜不停地转动,计划着什么。有些无奈,立直身子拿着本子在手中晃了晃“这本小说,无聊之至。“说完便扔在桌上,转身出了房门。咔的一声,门被关上。付亦想着那人刚才的话“这本小说,无聊之至。”“无聊之至,啧,这话有点过分呢。”他垂着眸看不清眼底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