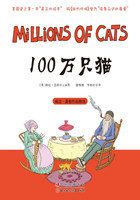“我想我能。”她说,“因为你说得这么恰如其分。”
“今儿晚上,咱们要喝点儿香槟酒,庆祝打到了这头狮子。”威尔逊说,“中午喝酒太热了。”
“噢,狮子!”玛戈特说。“我差点把狮子给忘啦!”
原来如此,罗伯特·威尔逊暗自思忖,她是要借刀杀人,借他的话讥讽自己的丈夫吧?不然,你以为她想唱戏吗?一个女人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可怜的孬种会干出什么事来?她冷酷得要死,她们全都冷酷无情。她们把一切都玩弄于股掌之中,那就不用说了,为了掌控某人,必须要冷酷无情。不过,我已经把她们那套可怕的把戏看穿了。
“再吃点儿羚羊肉。”他客气地对她说。
那天傍晚时分,威尔逊和麦康伯带着两个扛枪人,叫土著司机开着车出去了一趟。麦康伯太太待在营地里,她说,这会儿出去太热了,明天一大早再跟他们一块去。出发的时候,威尔逊看到她站在那棵大树下,她那模样儿与其说是个美人儿,倒不如说是个俏人儿。她穿着浅玫瑰红的卡其衫,一头黑发从前额往后梳,挽成一个髻,低低地垂在颈窝。她的脸蛋清新甜美,他想,仿佛在英国似的。她向他们挥着手,这当儿,汽车正驶过野草很高的洼地。车子在丛林中蜿蜒行进,穿梭在长着果林的山峦中。
他们在果丛林里发现了一群羚羊,就下了车,轻手蹑脚地走近一只老公羊,它头上那对长角叉得很开。离公羊还有足足两百码远,麦康伯就开了一枪,把那只公羊撂倒了,这枪打得很漂亮,值得表扬。那群羚羊吓得飞也似地逃窜开去,它们的腿一收一放,跳得老远,争相从其他羚羊背上跨过去,就像浮在水面上一样,看着令人难以置信,人只有在梦中才偶尔能像这样浮起来。
“这一枪打得漂亮。”威尔逊说,“目标那么小。”
“脑袋还行吗?”麦康伯问。
“很棒!”威尔逊对他说。“你枪法这么准,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你觉得咱们明天能找到野牛吗?”
“机会挺大的。它们一大早会出来吃东西;要是运气好,咱们可能会在空地上碰到它们。”
“我想摆脱猎狮那件事的影响。”麦康伯说,“让老婆看到自己那么着可不怎么好。”
威尔逊暗想,我倒认为,老婆看没看到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居然那么着了,而且过后还要再提。可是他说:“我再也不会去想这件事啦。不管是谁,头一回猎狮,可能都会慌张。这件事到此为止。”
他们在篝火旁吃罢晚饭,又喝了杯威士忌苏打才去睡觉。夜里,弗朗西斯·麦康伯躺在罩着蚊帐的帆布床上,侧耳听着夜的喧闹,到现在为止,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它既没有完全结束,也不是即将开始。它就在那儿明摆着,而且有些部分反而更加突出了;他可怜巴巴地羞惭难当。不止是羞惭,更糟的是,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寒冷、空洞的恐惧。这种恐惧盘踞在他心里,像个阴冷黏滑的洞,将他的自信一扫而尽,取而代之,让他恶心难受。这件事到现在还困扰着他。事情还要从头天夜里说起,当时,他半夜醒来听到那只狮子在沿着河边的什么地方吼。吼声低沉,尾音夹杂着咳嗽似的吭吭声,让他觉得这狮子好像就在帐篷外面似的。弗朗西斯·麦康伯深夜醒来听到这声音,吓得心惊肉跳。他能听到妻子平静的呼吸声,她睡得正酣。他没法跟谁去说自己很害怕,也没有人会跟他一起害怕,他只能独自躺在那里。他不知道,其实索马里有句谚语说,勇士总会被狮子吓倒三次:即第一次看到狮子踪迹时;第一次听到狮子吼叫时;第一次与狮子交锋时。后来,那头狮子又吼了一次,当时太阳还没升起来,他们正在餐厅的帐篷里就着提灯的亮光吃早餐。弗朗西斯以为它就在营地边上。
“听起来像头老家伙。”罗伯特·威尔逊本来正在埋头吃鲱鱼,喝咖啡,听到吼声他抬起头来。“听它吭吭。”
“离这儿很近吧?”
“河上游大概一英里远。”
“咱们会见到它吗?”
“待会儿去瞧瞧。”
“叫声传得这么远啊?听起来就像在营地似的。”
“叫声传得远得要命。”罗伯特·威尔逊说,“叫声传这么远是挺奇怪的。但愿那是头适合猎杀的家伙。听那帮杂役们说,附近还有头更大的家伙呢。”
“要是有机会举枪瞄准,我该往它哪儿打,”麦康伯问,“才能让它动不了?”
“往它肩膀中间打。”威尔逊说,“要是有机会,就打它脖子。往骨头里打!把它撂倒!”
“希望我能打好。”麦康伯说。
“你枪法很好啊。”威尔逊对他说。“别着急。要瞄准它。打中的头一颗子弹是最重要的。”
“离多远开枪?”
“不好说。得由狮子说了算。要离得特别近,瞄得十分准,否则就别开枪。”
“一百码都不到吗?”麦康伯问。
威尔逊飞快地扫了他一眼。
“一百码差不多。也有可能咱们得在更近的地方对付它。别妄想在超过一百码的地方开枪。一百码还行。想打它哪儿你就能打到它哪儿。瞧,你家太太来了。”
“早上好。”她说。“咱们要去找那头狮子吗?”
“你吃完早餐就马上动身。”威尔逊说。“你觉得怎么样?”
“超棒!”她说。“我好兴奋哦!”
“我去看看东西是不是都准备齐全了。”威尔逊走开了。他一走,狮子又吼了。
“吵人的家伙,”威尔逊说。“我们会叫你闭嘴的!”
“怎么了,弗朗西斯?”他妻子问他。
“没事儿。”麦康伯说。
“有事儿。”她说,“你干吗心烦意乱的?”
“没事儿。”他说。
“告诉我。”她看着他说,“你哪里不舒服吗?”
“都是那该死的狮吼声。”他说,“你不知道,它整整折腾了我一宿。”
“干吗不叫醒我?”她说,“我倒想听听呢。”
“我得去干掉那个该死的东西。”麦康伯嘴里说道,样子却可怜巴巴的。
“哦,你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啊。可我有点儿紧张。一听这东西吼,我就很紧张。”
“那好吧,像威尔逊说的那样,干掉它,叫它不能再吼。”
“是啊,亲爱的。”弗朗西斯·麦康伯说。“听上去很简单,是吧?”
“你不是害怕吧?”
“当然不是。可我整整一宿都在听它吼,所以有点儿紧张。”
“你会漂亮地干掉它。”她说,“我知道你会的。我恨不得马上看到你把它干掉呢。”
“快点吃,吃完咱们就走。”
“天还没亮呢。”她说,“这个钟点真荒唐。”
就在这时,那头狮子又吼了一声,像是发自胸腔深处的悲鸣,又突然变成震颤的喉音,声音越来越高亢,把空气震得都发颤了,最后它在叹息声和发自胸腔深处的、沉重的吭吭声中,结束了这声吼叫。
“听上去好像它就在这儿似的。”麦康伯的妻子说道。
“老天!”麦康伯说,“我讨厌这该死的叫声。”
“真了不得!”
“了不得!真吓人!”
这时,罗伯特·威尔逊来了,他手里抓着他那支又短又丑陋、口径大得吓人的吉布斯505,一边走一边咧着嘴笑。
“来吧!”他说,“你的扛枪人把你的斯普林菲尔德和大枪都带上了。东西都在车里了。你有实心弹吗?”
“有。”
“我准备好了。”麦康伯太太说。
“不能任它吵闹了。”威尔逊说,“你坐前面。太太可以跟我一起坐后面。”
他们爬上车,在第一缕氤氲的晨光中,穿过树林,溯河而上。麦康伯拉开枪栓,看了看他的金属子弹,然后推上枪栓,给来复枪上了保险。他看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把手伸进口袋,摸摸里面的子弹,又用手指头摸摸短上衣胸前套环里的子弹,然后扭头朝汽车后座的威尔逊望去。这辆车的车身像匣子,而且没有车门。弗朗西斯·麦康伯看到威尔逊和他妻子坐在车里兴奋得咧着嘴笑。这时,威尔逊向前探过身子,低声说:“瞧,鸟儿都飞下去了。这表示那老家伙已经丢下猎物残骸走了。”
远处河岸上,麦康伯看到几只秃鹫在树林上空或盘旋飞翔,或骤然俯冲。
“它很有可能会来这一带喝水。”威尔逊低声说,“喝完水它就倒头睡觉了。注意!”
他们沿着高高的河岸缓缓行驶,这里河床很深,铺满了圆石。车子在大树中间绕进绕出。麦康伯正望着对岸,威尔逊突然抓住他的胳膊。车子停了下来。
“它在那儿。”麦康伯听到威尔逊对他耳语,“前面,右边。快下车去打它!这可是头很棒的狮子!”
这时,麦康伯看到了那头狮子。它侧身伫立,抬起硕大的脑袋,朝他们望过来。清新的晨风迎面吹来,轻拂着它深色的鬃毛;这头狮子体型庞大,它站在岸边高地上,在氤氲的晨光里显出一个剪影:它双肩浑厚,圆鼓鼓的身躯平滑顺溜,像一只圆桶。
“它离我们多远?”麦康伯一边问,一边举起枪。
“七十五码左右吧。下车去打他。”
“干吗不在这儿开枪?”
“不能在车上打猎。”他听到威尔逊在他耳边说,“快下车!它不会一直站在那儿等你。”
麦康伯从前座旁边的半圆形缺口里跨出来,站在踏板上,然后踩到地面上。那头狮子还站在那儿,冷冷地望着这个目标,威风凛凛,这个目标在它眼里还只是个扁平的剪影。这头猛兽简直就是一头超级大犀牛。风没有把人的气息吹到它那儿去;它望着目标,时不时微微转动一下硕大的脑袋。它直盯着这个目标,并无惧意,但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站在对面,它有点儿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走下岸去饮水;过会儿,它看到一个人影儿从那个剪影中分离了出来,就扭过它硕大的脑袋,向丛林飞奔而去;与此同时,它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感觉到一颗220谷[① 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英文名称GRAINS,1谷=64.8毫克。
]①的30-06实心弹打进它的侧腹,打穿了它的胃,它胃里顿时泛起一股火烧火燎的恶心感。它迈开大爪子,步履沉重,晃荡着那受了伤的、圆鼓鼓的肚子,慢慢跑开了。它穿过丛林,朝茂密的野草丛跑去寻找避难所。就在这时,伴着又一声巨响,子弹呼啸而至,从它身旁擦过,把空气劈开。接着,又是“砰”的一响,它觉得子弹打中了它的下肋,一直穿透进去,满是泡沫的、热烘烘的鲜血顿时从它嘴里涌了出来;这次,它飞也似的向高高的野草丛蹿去,它可以蹲在那里,不被人看到,等他们带着那会爆炸的玩意儿走近,就朝拿着那玩意儿的人扑过去,把他逮住。
当时,麦康伯跨下车的时候可没想过狮子感觉怎么样,他只知道自己两只手在发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他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大腿僵住了,可他能感觉到腿上的肌肉抖个不停。他举起来复枪,瞄准狮头和肩膀中间,扣动扳机。手指头都快抠破了,可来复枪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他这才想起来保险还没打开,于是他放低枪口,拉开保险,僵直地朝前迈了一步。就在这时,狮子看到他的侧影从汽车的剪影里分离出来,于是转身小跑而去;麦康伯开了一枪,听到“嘭”的一声响,这说明子弹打中了;可狮子还在跑。麦康伯又开了一枪;每个人都看到子弹在小跑着的狮子前面掀起一阵尘土。他将准星放低,又发了一枪,这次他们都听到子弹打中了。那头狮子飞也似的跑了起来,钻进了深深的野草丛,这时,他还没来得推上枪栓。
麦康伯站在那儿,胃里直泛恶心。他端着斯普林菲尔德枪的双手僵在那里,仍发着抖,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他妻子和罗伯特·威尔逊站在他身旁。那两个扛枪人也站在他身旁,正用瓦卡姆巴语嘀咕着什么。
“我打中它了!”麦康伯说,“我打中了两枪!”
“你打中它肚子了,打得靠前了点。”威尔逊不起劲地说道。两个扛枪人脸色很难看。大家陷入沉默。
“你本来可以把它打死的。”威尔逊继续说,“现在咱们只好等会儿再进去找它了。”
“什么意思?”
“熬到它难受了再去找。”
“啊!”麦康伯叫了一声。
“这可是头超级棒的狮子。”威尔逊想活跃一下气氛:“别看它这会儿躲到一个糟糕的地方去了。”
“为什么说是糟糕的地方?”
“你不靠近就看不到它。”
“啊!”麦康伯又叫了一声。
“走吧。”威尔逊说,“太太可以留在车上。我们去查看一下血迹。”
“待在这儿,玛戈特。”麦康伯对他妻子说道。他口干舌燥,张嘴说话都很费劲。
“为什么?”她问。
“威尔逊说的。”
“我们要去瞧瞧,”威尔逊说。“你待在这儿。从这儿看能看得更清楚呢。”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