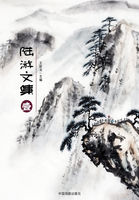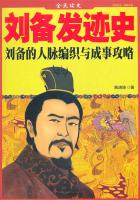午后幽暗的光线,从院子中间那棵核桃树的枝叶间漏下来,在地面上形成一团阴影。空气湿漉漉的,朽旧的雕花木房,裸露出灰色的瓦顶,一派清冷气象。外公躺在院子里的木椅上,眼神呆滞,气若游丝,疾病已将他推向冥界的边沿。早在几天前,他就开始出现幻觉——一直在自己的童年和暮年之间穿梭、徘徊。他的脸,清瘦蜡黄,表皮松弛,毫无生机。深深的皱纹里,除了沧桑,仿佛还暗藏着他一生中所有的秘密。
剃头匠戴着老花镜,目光聚焦在外公的头顶,一把锃亮的剃刀,在他手上运转如飞。外公的毛发,像枯萎的茅草,一根根落下。剃头匠不时将剃刀在自己的裤腿上蹭蹭,再用指尖在刀刃上刮刮,看够不够锋利。像木匠改料前的锉锯,他们都是敬畏生命的人。一把剃刀,见证了一个乡村的死亡史。只有经过它“剃度”的人,才能带着灵魂干净地上路。在乡村,剃头匠就是生命谢幕仪式上的司仪,他的职业充满肃穆和神圣。
外公剃光毛发的头,像一颗光滑的鹅卵石,形象十分滑稽。我和虫虫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模样酷似和尚的老头儿,会是我们血脉的源头。虫虫站在一旁望着外公,嘿嘿地笑。我蹲在地上,不停捡着那洒落一地黑白间杂的毛发,放进我自制的一个小木匣子里,以满足我的收藏兴趣。
虫虫是大舅的儿子。那时,我们都还小,不懂得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亡,更不懂得衰老对一个生命所造成的严重伤害。
母亲说,任何事情,都有个预兆。在外公病重的那些日子,她经常失眠,夜晚躺在床上,心上像放了块石头,压抑夜色般沉重。捱到后半夜,好不容易入睡,刚闭上眼,梦魇就像蛇一样缠着她。母亲的睡梦中,总是反复出现一个画面:她看见我死去的外婆,穿件蓝花布衣裳,牵着刚刚在地里干完农活儿的外公的手,慢悠悠地走在田坎上。外公的手,好像从来没有洗过,沾满泥巴。天上的太阳,明晃晃的,风吹得路两边的树叶沙沙响。外公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看,像是遗忘了什么东西,又像是舍不得离开。外婆总是埋着头,伛偻着身子朝前走。她的手,似一根绳子,拖着外公赶路。母亲说,那条田坎才叫长哟,总也望不到头——连接着冥界。母亲每次跟我复述她的梦,都泪水涟涟。我趴在凳子上写作业,她的眼泪雨滴般滚下来,落在我的本子上,把一个个歪扭的铅笔字,洇湿成斑痕。母亲用她粗糙的手,摸摸我的头,哽咽着说:你外公怕是活不长了。
风不时将核桃树的叶片吹落,在地面打着旋儿。大舅和二舅从楼板上取下干透的柏树,放到院坝中间,这些柏树是外公年轻时栽下的。二舅说,爸平生最疼这几棵树了。他将这些树,栽在院子左侧的荒坝上,就是希望它们离自己近一点。每天早晨,打开房门,看见一排树郁郁葱葱站在那里,山雀把窝筑在树冠,欢快、蹦跳个不停。爸就非常高兴,嘴上叼着旱烟,凝视好长时间。
一棵树从苗秧长成材,其间需要经历多长时间,经受怎样的风雨,外公是清楚的。树的秘密就是他的秘密。前几年,大舅建房子,想将那几棵柏树砍来做梁,遭到外公强烈反对,父子间不惜反目成仇。直到外婆去世,大舅心中的芥蒂才算消除。外婆病故前,是外公亲自将他精心培育起来的那些柏树砍倒,扛回家,去皮,晒干,为外婆打制了一口厚厚的棺材。他把那几棵树身硬挺,材质最好的树,全给了外婆,只将剩下的几棵弯曲且矮小的树,放在楼板上藏起来。那时,左邻右舍都说,戴老头子这人心肠真好!外公猛吸一口烟,回答:我这辈子欠我老婆子的太多了。
世界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我和虫虫在干透的柏树上踩来踩去,做游戏。两个木匠聚精会神地在改料,钢锯发出叹息般的钝响,锯木面筛糠一样朝下落,宛如时间堆积的尘埃。虫虫抓起地上厚厚的锯木面朝我撒来,我的鼻孔、耳朵、头发上顿时弥散出木头的气息,有一种苦涩的味道。虫虫看到我像一个裹满黄豆面的粽子,张开脱了门牙的嘴,傻傻地笑。他的笑声激发了我的愤怒,我迅速从地上抓起一把锯木面,借助风势将他的嘴塞满。虫虫的笑容瞬间僵硬,像一朵干枯的向日葵,两行清泪顺着他的脸夹滑下来。母亲拍拍我的头,伸手指指木椅上的外公,示意我们别再疯打、喧哗,以免搅扰一个老人的宁静。对一个垂死之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安静,以此来平息他内心深处涌动不止的波涛。
外公瘫在木椅上,中风使他的手和腿都失去知觉。凹瘪的嘴歪到眼角下,似一枚变形的月牙。唾液扯成丝线,浸湿他胸前的衣服,黏黏的,很像糖果融化后留下的痕迹。外公的头歪向一侧,眼睛静静地凝视着那两个手忙脚乱的木匠。多年前的某个早晨,他也是这么静静地凝视着那些向上生长的树。外公的眼神已经不聚光了,但凝视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他也许是在观察,看那几棵被木匠锯开的树,那一棵是他自己。
外公年轻时,也是个木匠。曾替不少的人修过房,造过屋,打制过棺材。把一个个痛苦或忧伤的灵魂请入灵柩,送往极乐世界。那个时候,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生命脆弱的伤感。如今,轮到别人替自己打制棺材了,不知外公心里在想些什么?是对过往人生的惋惜?对逝去时光的留恋?抑或在责怪那两个木匠的手艺差,将他的棺材造得丑陋窄小,让他躺在里面,像卧在一个岩洞里。
大舅用毛巾揩去他嘴角的唾液,二舅端着碗用勺子喂他白糖开水。水刚喂进嘴,又被他呶出来。他已经几天不吃不喝。大舅俯下身子,嘴贴着他的耳朵,像哄孩子一样喊了几声:爸,爸,爸……没有反应。他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他的内心是孤独的。从来都没有人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就像从来没有人,真正理解一棵树的生长秘密。树的年轮,只有等到树死后,才能呈现给渴望了解他的人。
现在,这个现实世界对外公来说,也是陌生的,他再也无力改变什么。
母亲从镇上买回香蜡纸烛,这是死亡的必需品。来替外公念改时经的道士先生说,一旦人落气,就得打开路,请各路神灵前来迎接亡魂归位。没有冥钱、贡品,神灵们是不会来的。即使职责所在来了,把亡魂接走,也就扔下地狱,不再过问,更不会向阎王求情,任其过赖河桥、下油锅、爬烧红的铁板……使之倍受折磨,痛苦难耐。外公活着时遭够了罪,怎么还能让他死后受苦呢?母亲买回的烛是大红蜡烛,香是长香,纸是长钱。还买回了金山、银山,金童玉女,老衣寿鞋。冥界该有的都准备齐了。剩下的便是等着外公安心上路。大家心里都清楚,外公气数已尽,他的生命即将得到解脱。
虫虫从香烛筐中拿出一张火纸,折纸飞机。他折了很多个,大的,小的,桌上摆一排。虫虫说,等我公死了,我就把这几架飞机烧给他,等他没事的时候,就开飞机耍。我没有理虫虫,爬在桌子上,抓起道士先生的毛笔,专心致志在火纸上画画。画了撕,撕了画。墨汁渗透纸背,像暗黑的血。我不知道自己在纸上画了些什么,也许,只是一个小孩意识里的感觉,或者记忆里的游丝。虫虫捡起我揉皱的纸团,展开,眼睛一亮,惊奇地问:你怎么在画我公?我一看那张纸,纸上的轮廓果然酷似外公的肖像。我双手托起纸,想重新看仔细,但很快,那张纸却被墨汁融化了、破碎了、模糊了、看不真切了……
棺材已经制好,两个木匠在做最后的工序——上漆。黑黑的油漆在棺材上刷了一层又一层。木匠屏气凝神,面对一口棺材,他们的心情也是沉重的。在木匠眼里,棺材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尽管,它更是死亡的象征。外公曾说过,制棺材的人,其实是在替阴间的人造房子,造宫殿。那两个木匠大概是理解外公的,他们是同路人。木匠尽量将外公的棺材刷出光洁度来,把木头间的小缝隙用油漆填满,把不平整的地方刮平整。这除了木匠间的相互敬重,更是木匠对自己手艺和理想的捍卫。一口棺材除材质好,漆也要上好。如此,才能使之在漫长的黑暗中经受地气的腐蚀,防止虫蚁的破坏。一口棺材,所装的不止是一个人的肉体,还有除肉体以外的其他东西,阴间的世界也是完整的。
两个木匠上完漆,站在棺材旁抽烟,蓝色的烟圈花朵般飘散,他们对自己的劳动表示满意。大舅拿出钱来塞在木匠手里,木匠点点头,收拾起地上还带着温度的工具要走。木匠转身的那刻,瘫在椅子上的外公突然清醒了。他摇摇头,目光追随着木匠走远的背影,嘴动了动,发出呜呜之声。听不清外公想说什么,像是喘息,又像是表达谢意。木匠走后,外公长久凝视着那口为他准备的黑亮亮的棺材,眼眶盛满泪水。
二舅望着外公脸上的神色说:怕是回光返照。
亲人们都来了,风一样从四面八方奔回,聚集在外公的院子里。死亡的力量是巨大的,惟有它才能将散落各地的人召回出生地。平时,他们都太忙了,要糊口,要养家,如果不是遇到自己生命的源头断流,他们的脚,恐怕是难得再踏上故乡的土地的。
这是一场关于死亡的聚会。二姑、四姑、五姑一见外公,就号啕痛哭。二姑一边哭,一边数落:爸,你的命啷个这么苦哟,一辈子没享过啥子清福……五姑流着泪,手上剥着香蕉:爸,这是你最爱吃的香蕉,你想吃的时候,没人给你买,现在我买了,你又不能吃了……哭得最凶的是四姑,她蹲在地上,将脸贴在外公僵硬的腿上,泣不成声,嘴里只知道不停地喊:爸,爸呀……悲伤河水般流淌。母亲立在一旁,看到姐妹们悲痛的模样,忍不住也跟着落泪。我和虫虫被姑姑们的哭声吓着了,躲在棺材背后,像两个木偶。
大舅气冲冲地从屋里出来,吼道:人还没死,就哭成这样了,像啥子话!大舅一吼,姑姑们像一群聒噪的麻雀,突然禁声。院子安静下来,天色忽然转阴,风把核桃树的叶子吹得飘零,时空如此虚幻。外公安静地瘫在椅子上,眼睛盯着油漆未干的棺材,脸上露出少有的慈祥和宁静。姑姑们刚才说的话,外公肯定是听到的,只是他不再开口。缄默是具有穿透力的,那是另一种深刻的语言。
姑姑们围守在外公身边,像落地的果子重新回到枝头。只可惜,那曾经孕育她们的树干,早已干了水分,正在枯朽。
天擦黑时,四姑说:咱去瞧瞧爸自己选的那块地吧。四姑说的那块地,就在后山的松坡嘴上。每年暑假,只要我到外公家,就会和虫虫到松坡嘴来玩。松坡嘴方圆一里地内种植的全是松树,一到夏天,密密的松针形成一排翠绿的伞盖,把强烈的紫外线挡在外面,松林里清凉异常。我和虫虫在里面捉迷藏,捡松籽吃。玩累了,就躺在林中睡上一觉。哪怕我们身上经常被蚊子、蚂蚁咬出小红疙瘩,也丝毫不减对松坡嘴的热爱。有时,外公挖土挖累了,也会钻进松林里来,掏出烟袋抽上一锅。外公一边抽烟,一边望着挺拔的松树说:真是块风水宝地,要是人死了,能埋在这里,那才叫“万古长青”呢。虫虫从地上爬起来,撅着小屁股说:公,那你赶快死吧,你死了,我们就把你抬来埋在这里。外公顺手给虫虫屁股上一烟锅,骂道:小东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虫虫嘿嘿笑着,老鼠一样逃跑了。
早在十天前,大舅和二舅就找人为外公打好了阴井。阴井左边是一块麦田,麦子刚刚发芽,绿油油的。阴井右边是一块草坪,上面耸立着两颗松树。外公是最喜欢树的。大舅说,这块地向山很好,天汽清朗的时候,可以看见对面的茶山像一把太师椅。好几个阴阳先生都说这地方不错,专发后人。不管是死者的儿子或女儿,都会家业兴旺的。
五姑说:这些松树长得真是茂盛,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到松坡嘴来玩。几十年过去,我们都是当妈的人了,它们还是这么青葱,好像是活在时间之外一样。二姑叹叹气:人要是活得过一棵树就好了。大家忽然又想起外公来,姑姑们都沉默着,气氛显得有些伤感。暮霭笼罩着松坡嘴,阴森森的。
舅舅、姑姑们心里都明白,外公将自己最后的归宿选在松坡嘴,除了喜欢那些松树外,还有另一个心思——离外婆近一点。外婆的坟地就在松坡嘴的垭口上,那儿风大,外公将自己的坟地选在垭口上边,是想为外婆挡挡风。他们活着时在一起,死后也应该在一起的。
夜色黑油漆般泼下来,整个村庄都像上了层漆,死气沉沉。一只十五瓦的灯炮挂在屋梁上,它所发散出的微弱光线,使屋里的一切都像处于古老的时光中。外公的椅子靠墙放着,他的脸,一半对着灯光,一半隐在黑暗中。他的精神状态跟下午比起来,更加虚脱,眼睛半闭半睁,脸像一张被岁月抽干水分的叶子——那是一张经过苦难的脸。外公的内心一定是痛苦的,只是他不表露出来,不愿意把心里的隐秘拿给死神窥破。人活到最后,总是该为自己留点什么的,尽管,留下的那点东西需要以生命来做最终的赌注。
姑姑们坐在灯光的阴影里,开始回忆往事。她们谈到外公年轻时候的事。二姑说:爸年轻时,也是个犟脾气。他当生产队队长那会儿,张福广的儿子想去当兵,体检合格了,需要爸在政审书上盖个章。可爸说那孩子有偷盗行为,经常在村子里干偷鸡摸狗的事,愣是不给人家盖。张福广递烟给他,不接,送鸡蛋、腊肉给他,不收。结果半年不到,张福广就当了队长,爸下课了。张福广记了他一辈子仇,后来二哥上学差学费,需要张福广盖章贷款,人家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父亲不但不生气,你猜他怎么说:张福广这人做事要不得,早晚会倒霉的。
五姑笑了笑说:那一年,爸去交公粮,吃了早饭就去,打着光脚板,担挑谷子走十几里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粮站,过称的人一称,谷子还差两斤。爸说,我在家装足分量的,啷个会差?过称的人说,公家称还有假!爸摸摸头,转身走了。他饿着肚皮回到家,二话不说,饭也不吃,拿个麻布口袋,装两升谷子提起就走。当爸再次走到粮站时,收粮的人已经下班。爸硬是跑到过称的那人家里,把人拉出来让其过称,说是要把上午差的两斤谷子补上。过称的人说,不用称了,把麻袋里的谷子倒出便是。爸说,那不行,我这麻袋里有两升谷子,肯定有多,你得把剩的还我。那人过完称,看着爸一晃一晃走远,朝地上啐口痰,骂一句:死老头。几天后,爸才听人说,他那天上午所交的公粮不是差两斤,而是多两斤。
……
姑姑们的回忆是一条丝线,串连起外公的一生。不晓得外公听了姑姑们的讲述,能否在心中重新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打量和确认,是否会勾连起他对往昔生活中,那些温暖抑或伤感的记忆进行梳理。他对这个生活过的世界留恋吗?当死亡的面孔在他沧桑的脸庞上露出笑靥。
也许是寂寞过于漫长,也许是回忆已经失去意义。姑姑们早已从她们的讲述中退出来,围坐在圆桌边,搓起了麻将。她们必须要借助娱乐来冲淡对死亡的恐惧。面对死亡来临,亲情也显得那样脆弱,不堪一击。
我和虫虫,两个毛屁孩,连死亡的旁观者都算不上。我们早已在姑姑们的麻将声中,沉沉睡去。
大概到了后半夜,我和虫虫被姑姑们慌乱的脚步声吵醒。我听见二姑喘着粗气说:快点,打盆水来净身,换寿衣。身体冷僵了,就穿不上了。四姑和五姑边帮忙,边呜呜地哭。二舅慌里慌张在屋中跑来跑去,六神无主。大舅在纸筐里东翻翻,西找找,颤抖着嗓音说:火炮搁在哪里,拿出去点起。寒气从窗户钻进来,在屋中转几个圈,又从房顶上的瓦缝里钻出去了。
虫虫把头缩进被窝,用他那小脚丫子碰碰我的屁股说:哥,肯定是我公死了。听说人死了会变成鬼,你怕不怕鬼。我才不怕呢,老师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说完,我的身子像被冷水冰了一下,迅速缩进被窝。虫虫和我像两只兔子,躲在被窝里,紧紧抱成团,把被子捂得严严实实。母亲一把将被子掀开,吓得我和虫虫一阵颤抖。母亲流着泪说:还不快起来,看看你外公最后的样子。我和虫虫穿衣下床,手拉手瑟缩着站在外公面前。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公赤裸的身子,他的肋骨一根根凸起,皮肤又黄又干,周身像是包了一层火纸。由于长期不进食,他的胸腹下凹,像路面上一个被太阳蒸干水气的土坑。二姑和大舅在为外公擦洗身子,暗黄的灯光照在他身上,像打了层蜡。外公身体的温度逐渐冷却,原本就无法动弹的两条腿,像两截木棒,硬硬地横在那里。大舅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的双腿分开,用毛巾揩去他下身的污垢。外公的阴茎萎缩,像一条生病的虫子,躲在黝黑的毛丛中,看上去十分丑陋。不知道大舅在看到孕育自己生命的那条来路时,会作何感想。外公的形象带给他的是一种难言的忧郁,还是一种隐痛的悸动。
姑姑们将净身后穿上寿衣的外公,平放在门板上。六件寿衣玉米壳一样层层将他裹住,好似一个扎紧的粽子。外公的儿女太多了,他必须要将儿女们最后的孝心,穿在身上带走才放心,对儿女们也才公平。尽管这份公平里隐藏着太多的沉重。
地灯点起来了,灯心草尖上跳动的火苗一闪一闪,映照着外公安静的睡眠。香也点然了,青烟在外公脚边袅绕。烛也点亮了,暖红的火光在为外公引路。
舅舅和姑姑们跪在外公脚前,哭着朝地上放着的铁锅里烧纸,一边烧一边说:爸,一路走好,走好,爸……纸钱在铁锅里忽地亮一下,就化成了黑黑的灰烬。我和虫虫跪在姑姑们身后,不停地作揖。我俩没有像姑姑和舅舅们那样,对外公的死感到悲伤。我们把这种祭祀仪式当成了一种游戏。虫虫说:他们烧这么多纸钱,我公领得到吗?我说:即使领到了,外公舍得用吗?
当虫虫和我的膝盖都跪痛的时候,我们听见笼子里的公鸡“喔喔”地打起鸣来。每天黎明,公鸡都会报晓,公鸡一叫,天就要亮了。
外公到底没有捱到天明。
灵堂在早晨才搭起来,整个村庄都被外公的死激活了。吊唁的人来了,帮忙的人来了。小孩子是牵着大人的衣襟来的,老年人是拄着拐杖来的,他们都来参加外公的葬礼。大舅、二舅又是跪迎又是递烟,招呼乡邻入座。他们尽量要使外公的丧葬搞得热闹一点,隆重一点。大舅说:咱爸苦了一辈子,拉扯我们几兄妹成人,不容易。现在爸走了,说啥,也得让他走得风光一些。二舅赶出圈里的两头猪,宰了。宴席一定要办得丰盛,不然,人家会笑话我的两个舅舅无甚能力,死人不要脸面,可活着的人还要。坐在院子里的人,有的打牌,有的嗑瓜子,外公的死成了一个乡村的节日。
但这所有的一切,外公都看不到了,也与他无关了。他平静地躺在窄窄的门板上,任时间水一样从他安详的脸上滑过。
锣鼓响起来,道士先生身穿道袍,在为外公做法事超度亡魂。伴随道士先生的诵经声,我似乎看见外公的身影从虚幻中清晰地浮现出来。他叼着个大烟袋,坐在松坡嘴的松林里,给我和虫虫讲他年轻时候的事。我突然感到空虚和哀伤,眼泪像两条虫子,在我脸上爬动。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外公不在了。从今往后,他将归于永久的黑暗,而只能活在我的记忆中了。
那天,我一个人悄悄跑到松坡嘴的松林中躲起来,任泪水哗哗往下流。
远远地,听着道士先生吹出的浑厚、低沉的海螺声,我看见外公的灵魂,变成一朵云,飘散了,从一个世界融入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