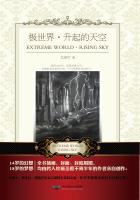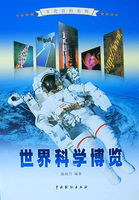纪应先生是我的远房叔叔。我很小的时候在老宅子见过他。那时,父亲还很善饮,常常在家里宴客,平常菜蔬经他调理,就变得十分可口,总能得到客人们的称赞。
纪应先生是在一个春天的上午来到我家的,他的样子很丑,黑脸,长发,一口黄牙,笑起来非常爽朗,衣衫也随着不停地抖动。他个子不高,奇瘦,眼睛小得不细看如同皱纹,鼻子却大得十分顽皮。
“二哥,您还认得我吗?”他说话的声音若空中楼阁忽来风。
父亲当然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们已经三十几年没见面了。
也就是说,从父亲少小离家到现在,这是他们仅有的一面。互叙了身世,自然十分亲热。父亲急急地叫我,让我给叔父行大礼,我扭捏地站在那里,说不清为什么哧哧傻笑。
我不否认从一见面我就很喜欢纪应先生。
他很能说,而且,他说每一句话都那么具有传奇色彩,那么引人入胜。我记得纪应先生来我家那天,父亲特意去副食店买了许多吃食,很少吃肉的他还买了一块五花三层的猪肉,一定要烹一个红烧肉给大家。说是大家其实不过就我们三个人,酒菜停当之后,父亲和纪应先生各吃了三杯“德惠大曲”。
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白酒,度数极高,入口醇香,不能言表。
酒杯放定,开始说话,于是,我,一个八岁的孩子,知道了许多人间的云长雾短、雨散风合。
说白了,纪应先生是一个大夫,但我更乐于把他想象成一个巫医。
他专治我们家乡的一种怪病,一种疯病,现代医学解释这种病是精神病的一种,而我们家乡那一带,称得这类病的人是让黄皮子给迷住了。
我在老家的一个邻居,一个很漂亮的农家女孩,因在坟包后撒了一泡尿,之后,就给黄皮子迷住了,疯疯癫癫不能自已。时好时坏,亦痴亦狂。有一次,她当街把衣服脱光了,七八个男人摁不住她。男人说,她力大无穷,拨弄他们像弹棉花一样。
这大概算一种佐证,也就是说,确有黄皮子迷人一说,不然她一个弱小女子,如何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纪应先生就是专和那些乐于迷人的黄皮子作斗争的!
他祖上几代专事此业,只要疯病未犯过三次的,他都有办法治过来。他祖上传有绝活,叫鬼门三针,即在头上、喉间、裆下三个大穴下针,针针刺要害,一有偏失,就会针到人亡,故称鬼门三针。
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中年妇女,好端端的,突然说开了胡话,声音尖细而怪异。她说,自己叫黄翠花,从远方来投亲,路过这里,腹中饥饿,想吃点高粱米水饭,吃点辣椒酱,如能满足,十分感谢。
言罢,倒在床上开始抽风,面色青黄,眼白上翻。
有明白人说遇到黄仙了。一边急急准备食品,一边悄悄差人去请纪应先生。
一小时又一刻钟,纪应先生飞马赶到,听人说,那妇女已经吃掉四碗高粱米水饭,狼吞虎咽之状态,绝非平常之态。
那妇女说:“吃饱了,我也该走了。”纪应先生却早已掐针在手,健步如飞,口中大叫:“畜生,你往哪里走!”眨眼之间已下两针,喉间一针已经颈后透出!
脱下妇女裤子,纪应先生下了第三针。之后,分开众人,衣衫猎猎生风,直奔后院,在房檐下正撞见那黄皮子,仰面朝天,似被钉在地上一样,嗷嗷惨叫,却动弹不得。
大家无不啧啧称奇。
听纪应先生讲,他家和黄皮子已斗了几代,终结都不是很好,所谓医人难医己,几代人了,最后也都得疯病,迷迷终日,郁郁而亡。
“你不害怕吗?”我小声地问。
“哈哈哈。”得来的是纪应先生的大笑,他那么开心,那么畅然。
人是人,仙是仙,正是正,邪是邪。自古人仙之争、人鬼之争凡例很多,但邪不压正的故事也举不胜举。纪应先生离开我家的时候,轻轻抚摸我的头,意味深长地笑了,他这个笑很慈祥,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