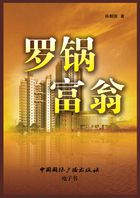教我们的班主任其实非常好。她的形象一直很高大、很完美,而且很有魅力。对于她说的话我们都无条件照做,心甘情愿。事实上,我们都抢着表现自己,讨好她。她的表扬可以影响到每个人的情绪和表现,甚至能影响到他们的一生。
在那个非黑即白的社会中,学生也被划分出非好即坏的两部分。从老师的眼神和口吻中我们能清晰地知道哪些人属于好学生,或坏学生,很自然的,会在心理上与之对比,或鄙夷、或羡慕。这种思维定势将维持数年,因为一个班主任带领一个班至少四年才放手。对于某些学生来说,无异于炼狱,尝尽教师的白眼和同学的孤立和歧视。一旦这些学生的自卑意识根深蒂固,无疑将“永世不得翻身”,即使有一天他们在社会上通过努力打拼超过了那些所谓的好学生,也只能赢得他们的略带诧异、嫉妒却仍然揶揄的笑容,仿佛这是个意外。
因此,我一直都在积极表现着,生怕被归类于坏学生的行列。争取最早到校,收拾卫生,抢答问题,专心听讲。从老师的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眼睛里,我隐隐觉得她其实很欣赏我。但一次迟到之后,我真正明白自己的直觉完全是幻觉。
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爷爷奶奶家醒来,睁眼一看,外面天光大亮了。我赶紧穿上衣服,一推房门,刚要迈步,猛然发现门口积了一小湾水,差点踩进去!昨夜一定下了大雨。院子里掉了一地树叶。看看爷爷的老怀表,我近乎绝望地发现自己肯定要上学迟到了。
我不乐意地向爷爷抱怨,“我不敢上学了,老师一定会骂我的。”
爷爷披着棉袄,端坐在桌前四平八稳地说,“没事,我送你去,不会有事。”
他还劝我吃点饭,我哪有心思吃饭?
等爷爷吃完饭,收拾停当,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急得像猴一样来回乱窜。爷爷还是不温不火地笑着说,“你急啥,一会儿就好。”
就这样爷爷拄着拐棍,领着我踏上了湿滑泥泞的上学之路。
路上,我总嫌他走得太慢,不停地在前面催促他快走。
好不容易我们上了山,走进了校园操场,我才缩头缩脑地跟在爷爷身后。
爷爷走到门口探头往教室里看。我忐忑不安地抓着爷爷后腰的衣襟,看见门开了。老师发现是我们俩后非常意外。爷爷说明了来意,老师当时笑盈盈地让我们进去。在同伴们的嬉笑声中,我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们齐刷刷的充满善意的注目礼将我的羞臊感一扫而光,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
还好,老师似乎并未生气,继续讲课。令我奇怪的是,爷爷没有立即告辞,反而留下来,拄着拐棍倚靠在教室的墙上看着我们上课。我觉得非常别扭,以至于回答问题都不好意思,总觉得像故意做表演似的。这与平时勇于表现的我大相径庭。直到爷爷移步走出教室,老师象征性地笑着送到门口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刚一放松,却见老师脸色铁青地走过来,眼睛里愤怒的火星子刺刺直冒,盯得我心脏都停止跳动了。她不耐烦地让我站起来,接着问我,“为什么迟到?!”
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了一会儿,后来想到门口那一小湾积水,就怯怯地说,“我家门口有湾水,我过不去。”
她马上翻着白眼严厉地说,“有多深,比鸭湾还深吗?!”
全班学生静下来,紧张地看着我们。我用近乎恳求的目光看着她,这种难堪不亚于大沙河溺水前窒息的无助的感觉。我费劲心机,甚至带着爷爷不辞劳苦地远远赶来,为的不就是要避免这种比灾难更可怕的尴尬局面吗?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逃不掉。
我面红耳赤地承受着她接下来的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挖苦,“——起来晚了自己承认个错误不就没事了嘛?脚尖那么深的水,哎呦!我过不去呀!哪里学来的那身讨厌的娇气!还领着家里人到学校来,你也不想想他那么大年龄走那么远的路,刚下完雨的道那么滑,他欠你的吗?亏你想得出!谁惯得你这身臭毛病!以后不要带家长来了!我一天教学已经够累的,还得迎来送往的,这是学校,不是你家!……”
我一直硬着头皮挨下去,像一个落败的拳击手毫无招架之力,只是无奈地等待着比赛的结束。我没有说话,心里忐忑不安,唯恐这一次会影响到我在她心目中的“好学生”的地位。
我的脸在燃烧,豆大的油脂顺着我的脸蛋向下淌。
那次“堂训”尤为漫长。她尽情地发泄着,不遗余力地展示她的良好口才,这是我们这些小学生们所公认的事实,“老师们词儿多”。这次和以往所不同的是,字字句句都像匕首一样刺痛着我那砰砰直跳的小心脏。这无异于对我那可怜的自尊心的强力摧残,我感到受伤,以至于至今我还能记得她踱来踱去声情并茂地对我冷嘲热讽的情景。那阵势极像骑马在秧苗田里肆意驰骋一样。不过谁都知道,不是骑马的有多厉害,而是秧苗根本不会反抗。
从那以后,我总觉得别人不会再尊重我。
在思维定势上,我或多或少地已经把自己归类于“坏学生”。
我发现做坏学生的世界也很精彩,因为他们享有很多优厚的待遇,他们可以无视学校的一切条条框框,而没人觉得奇怪,当然也不会有人骚扰他们。上课不听讲,作业不用做,坐在最后一排,自己忙自己的。上课时老师为了杀鸡骇猴,警示那些表现不大好的学生,偶尔故意提问一下这些“坏学生”,让他们出出洋相,由于出乎意料而惊慌失措,继而懒懒散散地站起来,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眨呀眨,一脸茫然地望着老师。通常老师十分鄙夷地说,“大傻个子长得挺高,学习大泥包,坐下吧你!”
原先听到这些话,我觉得好笑,内心里充满了对坏学生的鄙夷。后来听到这种话,我觉得刺耳。
中午放学回到家,我看见爷爷坐在炕上的小桌前正要吃饭呢。我一肚子的沮丧想跟他说说,又怕他再去找我们班主任,搞不好她又会把我骂个狗血喷头,以后还有好日子过?这样一想,我便把所有的委屈都咽了下去。
谁知爷爷一见到我,便笑着责备我说,“你上课时举手发言怎么总用手挡着眼睛?有啥不好意思啊?上课时应该龙头虎眼、大大方方的。你看人家别的孩子,哪个像你那样?以后要改啊!”他又转过头对忙里忙外的奶奶说,“这孩子上课举手老是挡着自己的脸,老师都看不清他是谁!还得上下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