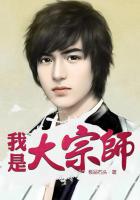二年级的一个上午,学校要求买田字格练习本。我家附近没有卖本的商店。黄屯和洼店的合作社有卖的。
我不想去那么远,就让家住黄屯的同学孙秋萝帮我捎一本。
孙秋萝身材瘦弱,细脚伶仃,眼睛不大,但是很有神,言笑间表情丰富而单纯,非常可爱。她也不大清楚本子的价格,说不是七分钱就是八分钱。我告诉她我会给她八分钱。
如果我说我从一年级就一直暗恋她,你们信不信呢?什么暗恋,开玩笑,有强烈的好感倒是真的。
那时候我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常常拖着两管鼻涕。但是这些都不妨碍我憧憬着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想法。
有些人觉得小学生不会或者不懂谈恋爱,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我很早就有浪漫的想法,只不过当年的条件不成熟。
你还别笑,这算啥,有个小孩三岁时就看好邻居家小女孩漂亮,抱着家里的猫崽子找她妈交换。和他比起来,我就是个小鬼见阎王。
中午回家吃饭时,我把要买本儿的事跟妈妈说了,妈妈马上开始凑钱。她翻箱倒柜地寻找了半天,凑齐了七分钱。我说不够。妈妈就出去借了一圈,才借到了一分钱。后来她解释说,“在街头转来转去,遇到王庭鹰家的老太太,把缺钱的事儿说了,老太太二话没说,回家取来一分钱。”
下午,我把这八分钱交给孙秋萝,让她第二天把本儿买了捎来。
可是,第二天,我跟她要本儿时,她说忘了,并一口应承明天给我。
我没办法,只好说没什么,明天取来就是了。
中午下课时,老师留作业正好要用到这个田字格本儿。而下午学校放假,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这个本,就完不成作业。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自己到她家去取。
下午我没有回家,在学校玩了一会儿直接奔黄屯而去。
我先找到同学孙强,他大体给我指了个方向。
在嘈杂的狗叫声中,我好容易才打听到她家在哪儿。
我走到门口时,院里的大黄狗嗷嗷狂吠。我站在铁门外等着,院子对面的房门开了,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皱着眉头的妇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远远向我张望着,表情非常疑惑,继而有些不耐烦地问道,“你要找谁啊?”
我揣摩她的年龄,断定这是孙秋萝的妈妈,赶紧说明了来意。
她转头向里屋喊了一嗓子,说了句什么,我透过没打开的半扇门玻璃依稀看见孙秋萝瘦削的面孔一闪,却随即又离开了。她们之间的对话声极小,我根本听不清,只看到她妈妈的脸上越发难看,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令人诧异的一幕发生了!她妈妈在门口操起笤帚追着她一顿劈头盖脸地暴打。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异常焦躁,恨不能冲进去夺下笤帚去打她妈妈一顿。或者,跟她妈妈问明原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
可又一想,我能帮人家什么呢?
我觉得喉咙里一阵干渴,简直要冒出烟来!人生中的无奈和绝望瞬间掠过我小小的心灵。那种强烈的欲望和无法实现的压抑感之间的交锋对峙残忍地折磨着我这小小的男子汉。多年以后,我仍然没有走出这种难以名状却又实实在在的困境。
稚嫩的我只看到孙秋萝在学校里乖巧活泼,却没想到在家中会受到如此虐待,心里的各种幻想都迅速破裂了,随之而来的是怜悯和同情。九岁的我虽然个子很小,却百感交集,颇觉自己单薄脆弱,如此卑微,空有慷慨激昂的骨气,仍然无法改变现实。
所以,我只能在院门外空等,痛苦地看着她们此刻都在里屋骂的骂,哭的哭。
折腾了半天,她妈妈才步履蹒跚地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几个钢镚,骂骂咧咧地走到我面前。“俺家丫头张罗张罗把你钱丢了,我好容易才凑够了钱还给你。”说罢,随手把钱递给我,转身回去了。
我数了数手中的硬币,怎么数都只有七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