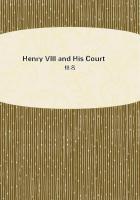贡布扎布是那顺乌日塔的大仇人。贡布城这块宝地原是那顺乌日塔家的,被贡布扎布看中了,公然要那顺乌日塔让给他,那顺乌日塔死也不从,说是祖宗留下的宝地岂能在我手中失掉!但贡布扎布发誓要拿到手,说什么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早让比晚让好,主动让比被动让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信走着瞧!从此,那顺乌日塔家的畜群,常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杀死或强行赶走,后来连房子也被烧了,不仅没有安身之地,真的连性命也难保了。那顺乌日塔虽然也是贵族,但那时还不是王爷的岳父,无力与贡布扎布抗衡,为了全家的生存,只好忍气吞声搬到大山坳,过着隐居式的生活。即使这样,他也从未表示过把宝地让给贡布扎布,那是贡布扎布强行霸占的。经过多年的再创业,他又把大山坳培植成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这样上对祖宗、下对子孙也好有个交代了。不料又埋下了祸根,贡布扎布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又对大山坳垂涎三尺了,只因那顺乌日塔成了王爷的岳父,一时不好公开下手。另一方面,贡布扎布企图夺取王位是人人皆知的,他把敖拉扎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并曾派杀手暗中杀过敖拉扎布,但没有得逞。暗箭难防,不知哪一天就会死在他的暗箭之下。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敖拉扎布和那顺乌日塔都是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日本投降后,贡布扎布在观察形势,霸气暂时有所收敛,敖拉扎布和那顺乌日塔也松了口气。
哪知好景不长,在巴音等三人离开山坳的第二天,那顺乌日塔突然听到一条重要消息:国民党已派要员秘密潜入贡布城,并任命贡布扎布为反共救国军司令和旗长,还可能升为将军和盟长。这一消息仿佛晴天霹雳,他立即派人探实后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敖拉扎布,敖拉扎布惊得目瞪口呆,果真如此,哪里还有我们的活路!
惊魂稍定,两人赶忙商议对付办法。由于贡布扎布成了国民党的人,对过去向往的国民党也就转眼变了样。在苦无良策的痛苦中,想起了巴音三人,从他们那种豁达大度、虚心诚恳、有理有礼、与人为善、不强加于人的态度看,共产党不像传说的那样可怕,倒是很友善的,他们所说的共产党的主张也是好的。再说,乌力吉这个人正派忠诚,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他的话也是可信的。
这时,敖拉扎布忽然想起在长春上大学时,曾偶尔风闻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的事,可惜没有细打听。可话又说回来,当时也不敢打听,就是打听,也没有人敢讲,这是过去的事,想也没有用了。
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只有受请出山任旗长为上策,所以盼望巴音他们再来,而且越快越好。议到这里,他俩的心情舒畅了许多,觉得有出路了。
再说孔冬,一收到盟政府给敖拉扎布的信,就同尤才、巴音等人商议还等不等省政府的委任状。大家认为,如果敖拉扎布愿意出山,有盟政府的邀请信就可以了;如果他不愿意出山,就是有了委任状也可以用种种借口推辞掉。于是决定孔冬和乌力吉、刘龙立即带上盟政府的信再度到大山坳。他们是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上路的,心中嘀咕,如果这一次再请不出来,工作就难了,新旗政府的成立将要推迟,这对开展工作是不利的。因此,必须耐心地、千方百计地说服敖拉扎布出山。
敖拉扎布和那顺乌日塔听说孔冬亲自来了,喜出望外,两人急令大开寨门,带人到寨门迎接,并献上哈达,连声表示欢迎。孔冬接过哈达,仔细打量敖拉扎布。他二十四五岁,个子稍高,胖瘦适中,面若冠玉,挺拔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一双大眼睛如一泓泉水,清澈深邃、炯炯有神,“眸正则心正”,整个人的形象是英俊潇洒,俊伟不凡。与其说是个王爷,不如说是个风华正茂的学子。孔冬顿时对敖拉扎布产生了好感,觉得乌力吉所说的他是个思想进步、正直善良的王爷,与贡布扎布有天壤之别的话绝非虚言。
孔冬紧紧握住敖拉扎布的手热情地说:“敖拉扎布先生,见到你非常高兴,相见恨晚啊!”敖拉扎布惊奇地看着与自己握手的这个共产党员竟是一个热情、和蔼、英俊的青年,丝毫没有盛气凌人的味道,顿生亲切之感,连声说:“真是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呀!”初次见面未曾交谈,彼此就都给了对方一个好印象。
这一次的热情和上一次的冷落对比鲜明,乌力吉感到大惑不解,猜不透是吉是凶。这时孔冬谦虚地说:“王爷,老先生,我等再次登门打扰,望请多多谅解!”
那顺乌日塔满脸喜色地说:“何言打扰,贵客光临,欢迎都来不及哩,快请进。”
进入大厅后,分主宾坐下。孔冬首先表明了来意:“上次因为有急事处理,未能亲自来请敖拉扎布先生出山,还望见谅。今日我们再次登门拜访,有效仿刘备三顾茅庐之意,恳请敖拉扎布先生念及全旗苍生,出山主持旗政。倘若这次达不到目的,那我们也只好三顾贵府了。此次来,不仅是我们的意思,更是受盟政府的派遣,现将盟政府的信呈上,请您收阅。”
那顺乌日塔一听是来“请王爷的”,又见女婿阅信后喜形于色,就放心了。
敖拉扎布高兴地说:“孔先生,劳驾你们两次来请,实在是感激不尽,我何才何能,怎敢与诸葛亮相比,哪敢劳驾你们再来一次呢?我对新政府还没有尽一点义务,就受到这样的信任和重视,实在惭愧,还有什么理由不听盟政府的吩咐,令你和尤才先生失望呢?再说,正需要我效劳时我不去,以后有何面目见全旗父老?我从现在起完全听从盟政府和你们的安排。”
孔冬三人这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请敖拉扎布出山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令人纳闷儿的是,怎么完成得这么顺利?乌力吉高兴地说:“王爷出山主持旗政,大家都高兴,全旗人民也高兴!”
那顺乌日塔笑呵呵地说:“老夫已摆好家宴,一来为三位洗尘,二是祝贺王爷出山,请诸位赏光!”
众人皆大欢喜,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那顺乌日塔所说的“家宴”一点也没错,大家都无拘无束,轻松自如,仿佛一家人一样。敖拉扎布席间向孔冬敬酒时感慨地说:“看你貌不惊人,文质彬彬,怎么能在一招之间能打倒一个彪形大汉呢?未见你之前,白音草原已将此事传得沸沸扬扬,说你像天神一般,膀大腰圆,威武有力,以致我与你刚见面时,想象中你的形象与现实中的你怎么也对不上号。”
孔冬微笑着说:“哪里有那么神,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是那个打手他太轻视我,他出拳完全是漫不经心,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二是我是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否则他不至于那么狼狈。听乌力吉先生说,你在外地读大学时,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继承王位后很有正义感,能同情贫苦牧民,待人接物十分随和,没有一点架子,所以人望很高。这次出任旗长,确实是名至实归呀。”接着孔冬又向他讲述了共产党的有关政策。
“过誉了,过誉了,我一定不让盟政府和你们失望,要认真地把工作做好。”敖拉扎布高兴地说,两人把酒言欢,好像是多年未见的朋友,谈得十分投缘。
刘龙坐在那顺乌日塔身边,显得十分文静,那顺乌日塔怜爱地劝他不要拘束,要多吃点。刘龙腼腆地直点头。乌力吉笑着说:“别看他现在害羞得像个大姑娘,打起仗来像只小老虎,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刘龙说:“那次战斗我犯了错误,挨了孔政委的批评。”那顺乌日塔笑眯眯地说:“你是个小英雄,打了胜仗,不应该受批评,而是要得表扬。听说袭击王府的是‘天下好’那帮土匪?那帮土匪可厉害啦,结果被你们打败了,了不起,了不起!”
乌力吉说:“据孔政委分析,不会是土匪,极有可能是某人的家丁。”
“那可能是色日因楞的家丁吧,他挟愤报复的可能性很大。”敖拉扎布插嘴说。
“没有证据,不能凭想当然就断定是色日因楞所为。”孔冬接着说。
这句话使敖拉扎布感触良深,孔冬开阔的胸襟,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他感动,他觉得投靠共产党是走对了路,与孔冬这种人共事一定会很愉快。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仍于夜间秘密出发,除了那顺乌日塔、王爷的福晋和贴身随从外,其他家人都不知王爷要外出。孔冬与敖拉扎布轻车简从悄悄地出发了,他们没有走上一次来回的路,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回旗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