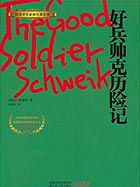吕老太太的厉害是出了名的。她原是富人家的女子,加上精明能干、容颜姣好,本是该享几十年清福的。然而,不知是应验了“红颜命薄”的老话,还是她鼻梁右侧的“接泪痣”克福,总之,她一岁上殁了生母,父亲为图家计顾不上管她。后母对她样样苛刻,唯独不勒令她缠脚,更不像其他母亲那样将撕扯成几寸宽的新布绺子一层层硬性箍在女儿的脚上,还用棍子赶着让下地走动。也正因为这件事,她便觉得后母是疼爱自己的,甚至为自己内心曾经生出过对她的恨而忏悔。及至后母把视如掌上明珠的亲生女儿也不依不饶地拉到炕旮旯往脚上勒布绺子时,她才幡然悟到些什么,继而也明白了自己这双大脚是如何的逆情悖理。她开始全力对付自己的两只脚,纵然是脸上泪汗淋漓,脚上浓血四溢也咬紧牙关绝不松绑。从此,她的厉害便颇有些名气了。
然而,长长了的脚板是不能缩短的,任凭她使出浑身解数竭力惩治,那双脚终难称得起是三寸金莲。也正是这双脚的缘故,她十九岁了尚待字闺中。“花儿能开几日红,女儿家能耍几天人,你家养老姑娘搁不着咱管,可不吃凉粉得让开凉板,我女儿可是到寻主的时候了。”后母对父亲阴阳怪气地撤开了腔。
与大户人家结不成亲,又担心小女先嫁落下个“大麦抽穗小麦杨花”的笑柄,父亲便不得不抛开富人家男娶女嫁时门当户对的讲究,将女儿屈嫁生活拮据的吕家。可终究是自个儿身上跌下的一疙瘩肉,就把自家的土地分出一些让吕家种,顺便也薄息给左邻右舍租种些,算是给女儿结了人缘,那陪嫁在当地也是前无尽有的丰厚,吕家的日子一下子起色了不少。
后来,吕老太太寡居了,大户出身的女子压根儿不该想到改嫁,何况她还有个儿子。再后来,吕老太太与众不同的便是她是地主的女儿。解放了,穷人们有了觉悟,懂得了应该当家做主的道理,地主老财罪恶滔天,得彻底打倒,地主的女儿自然就让人觉着碍眼了。于是,吕老太太被冷落了,昔日里亲哥热妹的乡邻见她如瘟疫般唯恐躲之不及,一个个扬头晃脑高傲得不愿正眼看她。吕老太太哪里受得了这个,她强压着火气忍了些日子,还是气不过,管它三七二十一,豁出去骂了一次庄。
“黄鹂子担不起三分膘,穷诈唬个啥呀?这世事咋转是大世里的事,那日能样子就像是自个儿有能耐!我家没像刘文彩一样欺男霸女吃人奶,地主是好当的么?得苦死累活地做,省吃俭用地攒。穷了还是个啥德行,谁偷你抢你啦,还不是懒的……”众怒难犯,终于有村长出面干涉。
吕老太太可不吃那一套,她似乎找到了发泄对象,说话刀剁一般更厉害了。这是村长所始料不及的,当着众人这样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让他的面子往哪里搁?他恼羞成怒,撵上去推搡开了,不知咋的,吕老太太的一只鞋被摔出去老远,那只棒棒脚恓恓惶惶地露了出来。
“嘻嘻,棒槌。”
“哈哈哈哈……”
看热闹的人抽筋似的笑起来,分明是向着村长的,吕老太太嘴唇打战,鼻侧的接泪痣充了血,突突直跳。她靠着身旁的土墙,将掉了鞋的脚奓在空中,如咆哮的母獅般指着村长吼道。“把鞋给老娘拾过来!”那声音让人联想起静夜里一声重重的镲响。不知是她的气势逼人,还是村长记起了“好男不跟女斗”的古训,反正,他悄没生气地把鞋拿到她脚底下了。吕老太太坐下来一边穿鞋一边撒泼。
“舔肥勾子咬瘦毬的些货色,打问一下这一村的土地原本姓啥,沾老娘的光白种了这些年,现在换过气了,却像狗一样翻脸不认人,常舌头往当官的裤裆里蹭,对着老娘龇牙咧嘴……”她的嗓门子大得山响,把在场的骂了个狗血喷头,直到村长打头,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灰眉土眼地回了家,才觉着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吕老太太这一泼,人们公认她是个不要命的,加之大骂村长,这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的竟有些玄乎,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对她刮目相看。至此,她的厉害可以说是威名大振了。
然而,也有吕老太太对付不了的人,这就是她的婆婆。老人家整天跪在炕头边,时不时伸出头一觑一探的让人觉着不自在,更要命的是只要身边有人,她就唧唧哝哝个没完没了。吕老太太知道她在诉说自己对她的诸多不恭不孝。“家丑不可外扬”嘛,她因此很气愤,每每听到她声泪俱下时,便猛不丁闯进去。老人家却像无意识似地展开双掌在泪脸上踏踏实实地一抹,就抹出一个笑模样来。“我家媳妇一天到晚不停地忙”,差不多每次她都能听到婆婆这像是说给别人听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话,“娃娃,歇缓一阵阵吧,家里的轮圈圈活哪能指望做完,操心把人累过火了。”满有疼惜之意的。唉,真拿她奈何不得。
好在婆婆不久就过世了。
吕老太太当婆婆之初,可是蛮乐乎的。儿媳妇莲花念过完小,这在同龄女子中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刚进门那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娇嫩得像她的名字一样。俗话说一分脾气一分本事,吕老太太人厉害,本事也厉害,收割打碾针线茶饭粗的细的都拿得起放得下,加之莲花面热嘴甜,她心里髙兴,人就更勤苦,很多事上都替换着莲花。
莲花生养稠,刚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时就做了节育手术,还是生下了七个儿女。吕老太太心性强,打灯熬油地给孙子孙女们缝新的,补烂的,让个个穿戴得有模有样,莲花也就更巴结她了。当然,也有因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使吕老太太发火的,那时她便做出十分气愤的样子骂叨起来。“不是我老婆子抖亏欠,一天到晚脚后跟打着尻蛋子跑,挣死挣活的为了谁唦?难道我把啥能背到墓坑里去……”每到这时,儿子就磕头下跪表示愧疚并求母亲宽恕,莲花也温顺地点根烟双手递上。“妈,消消气吧,别伤了您老的身子,我们改了就是。”于是,一场风波便平息了。吕老太太是不是想借此来重新体验自己的威势不得而知,但她因了这一头一跪一支烟而更加勤快却是肯定的。
年老人最疼爱小儿大孙子,吕老太太也没例外。大孙子悦悦除吃了母亲十个月奶外,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她用身子焐了他两三年的尿巴,更没少给他偏吃另喝过。悦悦回报奶奶的是其他人难以给予的快乐,一副鬼脸一个响屁都能使老人家笑出泪来,那颗被人们赋以悲意的“按泪痣”也喜滋滋地颤动。
悦悦最初离开奶奶是到离家几十里的地方上中学的时候。这可难为了吕老太太,一开始她曾掉了魂似的不自在,一个人偷偷地抹过眼泪,即便后来,她也是整天价扳着指头算日子,朝思暮想地等孙子回来。“过了星期三,除过两头剩一天,快了,悦悦快回来了。”她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并不断准备孙子下一个礼拜的吃食,油泼辣子咸韭菜锅盔馒头油花卷……食柜里的东西渐天增多,生怕忘了什么。
孙子孙女们一个个长大,像引窝的鸟雀有了自己的营生,莲花的细皮嫩肉早被风吹日晒得粗粗拉拉的,脾性儿也像遭风吹日晒过一样远没过去绵软了。吕老太太有种失落感,从灵魂深处感到孤独和寂寞,她觉得应该争竞一下让儿孙们正视她的存在,就发起了脾气。
“妈,闹伙啥哩,我得了关节炎,再是跪不得了。”儿子说。
“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你就别自个儿寻不开心,打问一下,有像你这样当老人的吗?”莲花说。
吕老太太被呛得心口子疼,她翻过来倒过去也解不开心里的疙瘩。于是,每当有亲戚邻里看望她时,就深有感触地感叹:“唉,猫老不逼鼠了!”接着便是听不清字语的絮叨,嘟嘟囔囔,像她婆婆当年一样没完没了。日积月累,她与晚辈的矛盾不断加深。
悦悦娶进了海棠。人们都艳羡说吕家的风水好,反正,又一个窈窕俊秀的娘儿们。